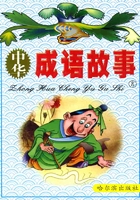§§§第一節文才:一種重要的社會認同標準
文才,作為一種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是文人之所以成為“文人”的內在規定性之一,其在社會上被認同的程度和範圍,充分地反映着其時文學在社會文化結構之中以及文人在社會知識群體之中所處的地位及所具有的影響,也折射着處在變革期的文學發展所處的階段和深度。對“文才”的認同略可分為兩個層面來認識,從外在角度講,需考察社會對文人之“文才”持一種什麽態度;從內在角度講,是文人個體怎樣認識與對待自己之“文才”。從上述兩個角度來審視漢末魏晉人們對文人之“文才”的態度和看法,就會發現,此時期的不同階段,人們對文人之“文才”的認識是有極大的差異和變化的。
一定程度上說,兩漢時期社會對文人之“文才”也是很重視的,有很多的歷史片段在文學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如漢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甚至發出“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的感歎,狗監蜀人楊得意告訴漢武帝此乃其邑人司馬相如之作,“上驚”,相如奏《上林賦》,“天子大說”,“以為郎”(《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第2533-2575頁。),漢武帝身邊的東方朔、枚皋、吾丘壽王、嚴助、朱買臣等都有因“文才”得幸的經歷;如宣帝為賦辯護;如班固說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班固《兩都賦序》,見《班蘭臺集》,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一冊,第308頁。另《文心雕龍·詮賦》也說:“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其源或出於班氏。);如揚雄心壯司馬相如賦,“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漢書》卷八七上《揚雄傳》,第3515、3522頁。);東漢時如“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杜)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美帝之,賜帛免刑”(《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杜篤傳》,第2595頁。);如肅宗向竇憲推薦崔駰說“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第1719頁。),後竇憲把班固、傅毅、崔駰等搜羅到帳下,使得“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傅毅傳》,第2613頁。);另東漢有“東觀”,東漢一世的許多著名文人都有著作東觀的經歷(詳情可參閱劉躍進《東觀著作的學術活動及其文學影響研究》,《文學遺產》2004年第一期。)。綜合來看,兩漢社會似乎形成了一種重“文才”的發展軌跡,但事實情況應做具體分析。就兩漢四百多年的時段衡量,重“文才”事例的絕對量並不算多,更重要的是社會上並没有形成對“文才”接受與認可的整體形勢,有的衹是“文學”、“文士”社會地位很低的事實。所以文人是不大以多“文才”、擅文事自詡的,他們更深的感觸、感歎是“為賦乃俳,見視如倡”,這纔是漢文人對自身所從事之“文事”一直以來的內心感受與認識。以文才顯者,他們可能實現的文化追求大概就是著史,卻很少以“文事”為榮。這種局面的實質改觀發生在曹魏。曹氏“尚文辭”,尤其是以“七子”為中心的建安諸子,以“文才”為世所重,這在曹丕、曹植、楊修等的相關文論中有直接的反映,曹植以“才捷愛幸”,明帝曹叡“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等等,都顯示了當時重“文才”的軌跡。但概觀言之,曹氏的重“文才”、“尚文辭”整體顯現着這樣的特點:事例基本圍繞着曹魏王室展開,曹氏政權的“尚文辭”帶有提升、推廣“文學”的政治意味,作者個體以“文才”為能事的例子還並不是很普遍(曹植送楊修、陳琳自己的作品以耀才,陳琳“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作論盛道僕(曹植)贊其文”,曹丕送作品給孫權等等,是較為明顯的例子,不過這樣的例子並不集中。)。兩晉時期對文人之“文才”的認識和接受比曹魏又有了深入發展。如果說曹氏“尚文辭”更多帶有提升、推廣“文學”的意味,晉時期的“文學”狀貌則表現出“普及”的傾向,社會及文人自身對“文學”表現了更為自覺的認同,“文才”已變成了文人顯示才華、獲得社會認可的重要文化行為,而且這一傾向已經具有了社會普遍性。
一、西晉時期人們對“文才”的認同
西晉社會對“文才”的認同,可從幾個方面來認識。一是“文學集團”。與曹魏以王室為中心大力延用文人的情形類似,西晉也存在着某政治勢力集團延用文人的情況。西晉權勢攬集文人的事例,最著名的當屬前引賈謐的“二十四友”。
這個“集團”或有政治意圖,賈謐“權過人主”,其招攬諸人於自己的身邊,似乎帶有壯大自己勢力的意味,不過這不大像一個嚴格的政治集團,“二十四友”並不是賈謐的政治親信(《晉書》卷四《惠帝紀》載“(永康元年)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第96頁),“黨與”中並不包括“二十四友”,連為“二十四友”之首的潘岳,即使“每候其(賈謐)出,與(石)崇輒望塵而拜”(《晉書》卷五五《潘岳傳》,第1504頁),也並没有被當作“黨與”一併處死,可見,“二十四友”並不是賈謐的政治親信集團。),比如陸機就因“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晉書》卷五四《陸機傳》,第1473頁。),從“其餘不得預”的情況看,也不像是在招攬政治勢力,而明顯地是在邀名。賈謐用以邀名的這“二十四友”是以“文才”集結到一塊的,《晉書·劉琨傳》記載:“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晉書》卷六二《劉琨傳》,第1679頁。)可見其實。也就是說,其時“文才”是頗被社會認可的,因“文才”可以顯名,集結“文人”賦作唱和可邀得名譽。從“其餘不得預焉”的說法看,“二十四友”集團是頗注意以聲名相高、自增身價的,當然他們藉以耀世的是他們的“文才”或文學活動。
另外,西晉權勢吸納文人的情形還可以從“八王之亂”這個歷史過程中窺得一些信息,具體論述可參見本章附錄《“八王”幕府佐僚“文學”背景述略》。總的說來,作為當時社會的主要政治勢力,“八王”中的一些藩王很注意收取時望、擴大影響,在其招納的俊士賢才當中,具有“文才”的一些社會名士佔了一定的比例,雖没有直接的證據顯示他們是以“文才”突出被吸納的,但“文才”顯然是他們成為社會名士的文化素質之一。從“二十四友”及著名的金谷園活動等情形來看,以“文才”獲譽在當時的社會是很普遍的事情,那麽這些具有“文學”背景的人士在他們居身的幕府之中帶動相應的“文學活動”或“文學氛圍”應當是很正常的,這樣背景的人員佔相當比例,反映了府主和幕府群體對“文學”一定程度的認同。
以上是西晉政治勢力集團延用文人的情況,但其與曹魏以王室為中心大力延用文人的情形、旨意已有所不同。如果曹魏王室集團吸納文人、文學文化特徵突出或不突出,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不同階層、有差異文化群體之間的鬥爭的意味,那麽西晉政治勢力集團所帶有的文化背景則顯然要單純得多,這些集團的文化差異已不顯示為階層鬥爭。某集團文學背景或特徵的有無,往往衹與府主的文化層次與政治識見有關,而不體現階層的變動。即使是對立的集團,也無妨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徵,如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東海王司馬越的幕府群體,都顯示着一定的文學文化特徵。此時,“文學”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共性的文化樣式為社會所接受,“文才”高低顯示的是才華的大小,而不是社會身份的差異,“文才”已經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才能為社會所認可。“二十四友”與“八王”的某些幕府群體對有“文才”之士的重視,顯示的正是社會較為普遍地接受“文學”的發展事實。
西晉社會對“文才”的認同,除了可從“文學集團”方面來認識外,還可從當時社會對“文才”的“肯定”中得到反映。
如左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左思,武帝聞而納之。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武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晉書》卷三一《后妃上·左貴嬪傳》,第957-962頁。)。姿陋而以文才獲幸,這在此前的歷史上尚不見反映。另從“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的話中,可見當時社會對“文名”是有一定的認同因而加以傳播的。這與陸機入洛之前張華就已經“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所反映的社會事實相同。
又如前引《世說新語》“樂令善於清言”條、“太叔廣甚辯給”條反映的情況,“長於手筆”、“長於翰墨”等“文才”,能與“善清言”、“甚辯給”等清談本領一併為社會所許,頗能反映出社會對“文才”的好尚。如此說並不突兀,社會對“文才”認同的例子還有如劉琨“文詠頗為當時所許”、潘尼叔侄“俱以文章見知”(《晉書》卷五五《潘岳傳附從子尼傳》載:“尼少有清才,與(潘)岳俱以文章見知。”(第1507頁))、王鑒“少以文筆著稱”(《晉書》卷七一《王鑒傳》載:“鑒少以文筆著稱”(第1889頁)。)、應貞于華林園宴射“賦詩最美”、鄒湛所著詩“為時所重”(《晉書》卷九二《文苑·鄒湛傳》載:“(湛)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第2380頁))、司馬保“少有文義”(《晉書》卷三七《宗室·高密文獻王泰傳附孫保傳》載:“(保)少有文義,好述作。”(第1098頁))等,都可反映“文才”為社會稱許之一面(另外《晉書》中其他的說法像“善屬文”(如第1013頁卷三四《羊祜傳》載祜“博學能屬文”、第1317頁卷四七《傅玄傳》載玄“博學善屬文”等)、“有文才”(如第1635頁卷六〇《牽秀傳》載秀“博辯有文才”等)、“有文藻”(如第1499頁卷五五《夏侯湛傳附弟淳傳》載淳“有文藻,與湛俱知名”等)、“善文辭”(如第2380頁卷九二《文苑·棗據傳》載“據美容貌,善文辭”等)、“以文章顯”(如第2381頁卷九二《文苑·棗據傳》載“子腆,亦以文章顯”等)等,因《晉書》為唐人所作,僅據這些說辭不好判斷這些斷語是晉世當時人所稱還是唐人根據後世資料所評,故不用作資料依據。正文中所用之事例,蓋可判為晉世時事,“為時所許(重)”顯然是為當時人所許,而不是為後世所重,“俱以文章見知”、“少以文筆著稱”、“少有文義”中的“見知”、“少以(有)”也都應該是當時的事實而不是後世的追認,故用作反映事實之實例。)。
除了對作者“文才”的直接稱許,此時還出現了為“文人”延譽的事例(《晋书》卷五一《挚虞传》载虞:“性爱士人,有表荐者,恒为其辞。”(第1427页)挚虞是著名的文士,其舉薦人士“恒为其辞”,也是一種延譽的舉動,不過已不可考知其舉薦了哪些人士。),史載:
(張載)為《蒙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晉書》卷五五《張載傳》,第1518頁。)。
及(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核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余思為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引》也。”陳留衛權又為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瑰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為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為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為之《略解》,衹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于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卷九二《文苑·左思傳》,第2376頁。《世說新語·文學》記載此事有所不同:“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贊述焉。”(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246頁)張華、皇甫謐的順序和說法有所不同。)。
“延譽”情況的發生,前提是延譽者對所延譽之對象應有相當的認同,社會也存在相應的心理期待,否則也不會有“延譽”之舉。張載、左思之人之文經過名士為他們延譽而聲名大振的情況說明,社會對特異之“文才”、“文事”的關注與認同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左思的情況,有劉逵、衛權、皇甫謐為之作序,劉逵、衛權、張載為之作注,又經張華的贊評,這種“盛況”在此前的文學史上是没有的(司馬相如等所造《郊祀歌》十九章文字華美而古奧,《史記》說“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卷二四《樂書》,第1177頁)《後漢書》卷四二《東平憲王劉蒼傳》載:“……(劉)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明)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第1436頁)這些情況的發生,基本是奉帝王詔命而行,其主要意圖也不並是為了推介作品,其實質與眾人推介《三都賦》不類。),諸人同時為左思的這一長篇巨製進行鼓吹,甚至出現了“洛陽紙貴”的奇觀,顯示了其時社會認同“文才”的極大熱情。社會對“文才”的這種熱情還可以從當時的一些說法中得到印證,《晉書》張亢本傳載:“時人謂(張)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史臣曰:‘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核遺文,非徒語也。’”(《晉書》卷五五《張載傳附弟亢傳》,第1524、1525頁。)“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並不是史臣的創新之詞,而應是晉世當時之語,“二陸”、“三張”、“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等說法的概括與比較,顯示着人們對文壇人、事的熱衷和極大的興趣。
西晉與延譽情形類似的重“文才”舉動,還有對“文士”的舉薦,較為典型的事例是張華對“文士”的舉薦。《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這樣概括張華:“華位崇望高,為晉初文壇祭酒。喜獎掖文士,即窮賤之士亦為之延譽。其所稱引、交接者,有陸機兄弟、左思、成公綏、陳壽、褚陶、張軌、劉聰等,皆一時之選。”(曹道衡、沈玉成編撰《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33頁。)翻檢《三國志》、《世說新語》及《晉書》,張華舉薦之人物約略有二十七人,這些人當中,明確具有“文學”背景的有十六人,可以進一步佐證《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所說不誤。張華“喜獎掖文士”並形成一定的局面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此舉所顯示出的對“文才”的認同,比此前的“文學集團”又深入了一步,它已經超越了“文學集團”吸納“文士”通常所具有的政治意味,而更多地指向了重視“文才”、推廣“文才”的文學發展本身。以政治領袖與文學翹楚的身份對“文士”進行較大規模的援引、推介而不帶政治意味,這在文學史上還得首推張華,所以在文學發展由魏向晉推進的過程中,張華是有特殊貢獻的。張華能較為集中地獎掖、推介文士,顯示出文士之“文才”作為一種文化能力,在社會舉薦人才的文化標準中,已經佔有了一定的位置。
因“文才”而舉人,除了張華做得比較集中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事例,如:
杜預將之鎮,復薦之(陳壽)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晉書》卷八二《陳壽傳》,第2138頁。)。
國子祭酒鄒湛以(閻)纘才堪佐著作,薦于秘書監華嶠(《晉書》卷四八《閻纘傳》,第1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