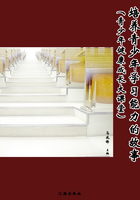另曹節、王甫“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讓、忠……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賤,為人蠹害。”說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並不誇張。當然,即使如上“黨人”遭到打擊、宦官的勢力得到很大發展,但並不是說宦官鬥爭的對手——士大夫階級就銷聲匿跡了,無論在階級勢力還是思想文化方面,經過从前漢到後漢的深入發展,士大夫都已經確立了他們在社會上根深蒂固的主導地位,單憑宦官一己一時之力是難以徹底撼動士大夫的主導統治地位的,所以即使是宦官最得意、最得勢的時候,他們與士大夫的鬥爭也是一直存在的,不過没有體現得如“黨錮”之禍那麽激烈罷了。宦官能獲得這樣的發展機會,當然是藉助於皇權,即“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代表的是以皇帝為首的整個內廷系統,至少在靈帝的時候,皇帝和宦官是緊密結合、一致對外的。漢靈帝常常“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後漢書》卷五七《劉瑜傳》,第1856頁。),“聚為私臧,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張讓傳》,第2536頁。)宦官是皇帝藉助的近侍,皇帝是宦官獲得權力的後臺,他們維護內廷權力、利益的目的是一致的,靈帝責備張讓的一段話頗能道出其中實質:“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可見他們一致對外的一貫事實。
但無論宦官的勢力怎樣膨脹,其弟子如何布列州郡,相對於傳統的士大夫勢力而言,都是單薄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也絕不衹是簡單的一時一事的勝利可以解決,鬥爭是在各個方面進行的,除了布列子弟,扶持相關勢力是他們壯大勢力的一條必然途徑,“鴻都門學”的興起正是藉助了這一歷史契機。
(二)“鴻都門學”的建立
于史可輯的“鴻都門學”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势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1991-1992頁。)“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1998頁。)《後漢書·孝靈帝紀》李賢注云:“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光和元年十二月,靈帝“敕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後漢書》卷七七《酷吏·陽球傳》,第2499頁。)。由“待制”到“遂置”到“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再到立像“以勸學者”,形勢逐步升級,且這一過程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的,說明靈帝對之是極度重視的。
不同尋常的是,靈帝的這次舉動遭到了士大夫的強烈反對。早在“鴻都門學”正式建制的前一年(熹平六年),蔡邕就上書靈帝: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反對不但無效,而且在反對聲中,靈帝還加大了步伐——“鴻都門學”正式建制。對此,乘對策之機蔡邕又予以發難: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1999頁。)。
大臣楊賜也上疏批評:
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日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附孫賜傳》,第1780頁。)。
反對越激烈,靈帝扶持得越見力度——年底更為樂松、江覽等圖像立贊,“以勸學者”。但“鴻都門學”發展的每一步都會招致抨擊,尚書令陽球上書曰:
(樂)松、(江)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後漢書》卷七七《酷吏·陽球傳》,第2499頁。)。
“鴻都門學”現象當然不能僅從靈帝個人喜好的角度理解,而顯然屬於政治事件。靈帝的其他舉動如“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第346頁。),顯然荒唐、淫靡之極,已嚴重違反儒家對帝王的要求和規範,且引起了“京師轉相放效”的不良社會效果。但並不見士大夫反應得如此敏感和強烈,原因無他,因為這還尚算是“個人”、“小範圍”的事情,類似現象在宮廷中多有,不過這裏更顯荒唐一些而已,但尚在能够容忍之列,而“鴻都門學”事件顯然觸及了階層利益集團的根本對立。
關於“鴻都門學”士人的文化、階級特性,王永平在《漢靈帝之置“鴻都門學”及其原因考論》一文中有精審的考證和論述。這裏不再展開分析,而直接引用原文的結論:
從文化取向而言,“鴻都門學”主要是一個文學藝術群體,其中士子多以辭賦書畫等才藝作為進階之資,而與儒學士大夫以經術、德行為入仕之正途不同。……從社會階級而言,“鴻都門學”中人大多出自寒微,與儒學世族不同。
“鴻都門學”事件實際上反映的是出身低寒、從事嚮為正統所輕之“賤業”的人群與經術傳家之士大夫群體之間的衝突,以靈帝、宦官為代表的內廷挑起了這次矛盾,並藉助他們與外廷抗衡(關於宦官與“鴻都門”人士的同屬關係,陳寅恪所論實已啟其端:“然則當東漢之際,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頁)論述東漢末士大夫和閹宦兩大對立集團的鬥爭,概括閹宦的主體文化取向是“尚文辭”,實際已暗含了對宦官與“鴻都門”人士同屬關係的揭示。以後毛禮銳在《漢代太學考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2年第四期)、韓養民在《秦漢文化史》(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頁)、王永平在《漢靈帝之置“鴻都門學”及其原因考論》(《揚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五期)中直接揭示了“鴻都門學”的建立與宦官的密切關係,其中尤以王作後出轉精,論述縝密,可參看。以後孫明君《第三種勢力——政治視角中的鴻都門學》(《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五期)對上述觀點有所商榷,認為“鴻都門學”是由靈帝建立的針對清流士人和宦官的“第三種勢力”,虽從異處立說有積極意義,但論述邏輯及例證似不足影響前述論作的論證和結論。)。“文學”、術藝之需多為人情所不免,但儒家既要強調“節之以禮”,在統治的實際過程中又總不免執行重禮鄙情而對以“文學”、術藝為能之士加以輕視,所以靈帝搞出這種局面來,既可以滿足他和宦官們的實際愛好,又可以藉以打擊士大夫一貫自恃的驕傲和神聖。靈帝藉用“文學”、術藝之勢力與士大夫集團對抗,一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樣,“文人”與士大夫集團有對立、制衡的傳統,但靈帝捨棄傳統的“文人”群體,如蔡邕、酈炎、張超等音樂書法多能之士,而直接提拔底層“文人”上來,也正是因為如上文所述,傳統的“文人”早已“經學化”了,他們實際上已開始代儒家立言,這就是靈帝身邊搜羅大批“文人”卻還是要大興“鴻都門學”的原因。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鴻都門學”階層對立、鬥爭的實際性質。
二、文人群落的重組
“鴻都門學”的發生、發展,引發了這樣幾個重大變化:
首先,針對“太學”的“鴻都門學”的建立(范文瀾云:“一七八年,漢靈帝立鴻都門學。這個皇帝親自創辦的的太學裏,講究辭賦、小說、繪畫、書法,意在用文學藝術來對抗太學的腐朽經學。”(《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三章第二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50頁))使經學的獨尊地位受到衝擊。
太學之名,西周已有,當時天子與諸侯均設,但封建社會意義上的太學的建立,是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天人三策》曰: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03-2504、2512頁。)。
太學有兩個主要作用,一是教化天下之民,二是養天下之士,當然以資教化的是儒術,養成之士是儒士,建立太學是董仲舒推行“獨尊儒術”的一個主要步驟。元朔五年(前124),“興太學”,設五經博士,弟子員五十人,以後多有增補,成為常制。太學成為官方確認的權威經學學府,同時也成為國家培養官員的最高場所。可以說,太學是儒學成為統治話語、儒士成為統治階層的象徵,其特殊的社會功能隨着經學從西漢到東漢的深入發展而日益得到強化和確認。
但在東漢末的時候,經學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突出事例之一就是針對“太學”的“鴻都門學”的建立。陽球抨擊“鴻都門學”所說的“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就揭示了“鴻都門學”與“太學”的差别和對立。它們的對立所揭示的不僅僅是兩個機關之間的問題,而是兩個機關各自代表的文化、階層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鴻都門”人士擅長的“書畫辭賦”等被士大夫群體稱為“小文”、“蟲篆小技”、“工技之作”,屬於“小能小善”、“才之小者”,而“匡國理政,未有其能”;他們的身份,大抵是“無行趣勢之徒”、“有類俳優”、“群小”、“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豎子小人”。“鴻都門”人士的文化趣向、階層屬性與經學士大夫完全不同,這種對立在蔡邕、楊賜、陽球的抨擊中也可以看出,與“鴻都門”人士的文化趣向和階層屬性所對比論述的正是“口誦堯舜之言”的“搢紳之徒”,他們強調“通經釋義,其事優大”,君子“當志其大者”。
“鴻都門”之學與“鴻都門”之士的狀況當然一直在社會上存在,但在儒術獨尊、儒士獨尊的狀態下,他們一直是以卑微的、被人輕視的狀態和方式存在的,儒家出於建構禮樂的需要、出於維護自身權威性與神聖性的目的,在現實生活和國家政治管理中是排斥他們的,翻檢《漢書》、《後漢書》,對比“文人”與經學士人的地位和命運,二者的差别一目瞭然。無論是官方的確認還是社會的接受,經學和儒家士人在人們的意識中都是唯一尊貴與合理的存在,此外無他。而以官方的名義對被士大夫激烈反對的“鴻都門”之學與“鴻都門”之士進行確認,這在歷史上確實是破天荒的一次。“鴻都門學”代表了一種異質的聲音和狀況,從而對傳統統治話語和士大夫統治勢力構成了一定的衝擊。
其次,以利祿相招,“書畫辭賦”“作者鼎沸”。內廷不但仿效“太學”為“小能小善”者建立國家級最高學府——“鴻都門學”,而且還直接搬用太學諸生出入為官的套路,對“鴻都門”生許以官爵,“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並各拔擢”,“受豐爵不次之寵”,“使理人及仕州郡”,“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乃至“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帝既“待以不次之位”,又“立像以勸學者”。在以仕為體現人生價值之最尊貴方式的古代社會,被許以官爵更能顯示被確認的意味,所以這一打破傳統社會確認規則的舉動必在社會上引發巨大的回應。“鴻都門學”初起時尚衹有“數十人”,而前引《靈帝紀》李賢注曰“至千人焉”,又蔡邕說“諸生競利,作者鼎沸”,作者蓋又不止“千人焉”,基數迅速擴大。這是必然的,因為有利祿相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何況帝王勸以利祿,又為能者立像廣為宣招,其轟動效應決非一般的一時好尚可比,這也應該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苦心經營“鴻都門學”的靈帝所期望的社會效果。衛恒《四體書勢序》稱“(漢)靈帝好書,世多能者”(《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注引,第31頁。)。江式《論書表》:“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魏書》卷九一《術藝·江式傳》,第1962頁。)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本漢》:“靈帝好書,開鴻都之觀,善書之人鱗集,萬流仰風,爭工筆劄。”(崔爾平校注《廣藝舟雙楫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頁。)所描述之狀況,蓋可視為“鴻都門學”的後續效應。一種事物衹有逐漸取得社會的認可,逐漸被社會所接受,纔可能取得普遍發展之勢,由於史料的缺乏,不好概括“鴻都門學”對社會觀念的影響程度,但“鴻都門學”作為一級國家機構、“鴻都門”生曾普遍為官、“鴻都門學”曾引起社會反響,這些都實實在在地成為一種客觀事實留存於歷史當中,其必與後世相關社會現象的發展構成開啟、承遞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