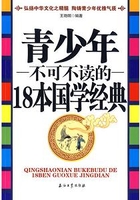一、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及其历史条件
早期道教大约形成于东汉中叶潮流,形成时即有二派:丹鼎派和符篆派,前者重清修炼养,后者多以符水治病、祈福禳灾为主要宗教活动内容。后者发展较快,多为民间组织,如:太平道,为张角所创,主要在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北部一带流传;五斗米道,为张陵、张鲁所创,主要在今四川一带流传。这两派在汉末均曾发动过农民起义,五斗米道还在汉中建立过政教合一的政权。魏晋时期道教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逐渐汲取佛教的宗教形式以提高宗教素质,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的水平。尔后,道教经过隋唐时期的国教化,同封建社会的国家上层建筑融为一体,再经过宋辽金元时期的革新,宗教伦理素质和修持方法进一步提高。明清时道教以正一道(修习符录、祭祀、斋醮的显教)和全真道(修习南北派内丹的密教)为主流,在教理上进一步与儒、释两教融合。
道教信仰内容蓄积了汉民族历史形成的感情、信仰和思辨的传统成果,包含了庞大而丰富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东方宗教的色彩,其产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交叉作用的结果。
第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为道教产生奠定了基础。道教不像三大世界宗教那样是由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起来的,而是有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长期孕育的过程,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古代先民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即萨满教一类的巫术宗教)。夏商周后,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举,原始宗教分化,对神祇和祖宗的祭祀纳入国家的礼乐教化,对“怪力”、“乱神”的崇拜流入巫祝和方士阶层。后世道教宫观中司香火者称庙祝,便是自此沿袭而来。周代鬼神崇拜更加系统,形成了“天命观”的神学理论,其崇拜的鬼神已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祇三个系统。周礼说:“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属于天神的有上帝及日、月、星、斗、风、云、雷、雨诸神;属于地祇的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式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这些也是后来道教成为多神教的来源。后世道教做法事、建醮坛、设斋供,即古人祭祀之礼;唱赞歌、诵宝诰,即含有言辞悦神之意;上表章、读疏文,是申诉和祈祷之用,故道教的产生承袭于古代巫祝遗风,所供奉的神也大多渊源于古人的信仰,因为这些神都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战国时期,追求长生成仙的方士们形成“方仙道”,成为后世上层神仙道教的源头。秦汉以来,由于儒学日益兴盛,加之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文化已无法形成战国时期那种和儒家平起平坐的自由发展的独立学派,被迫由世俗文化转向宗教文化中寻找出路,道家黄老之学逐渐由治国之术演化为治身养生之术,并与阴阳五行家、神仙家、方技术数家合流,和方仙道融为一体并在东汉转化为黄老道。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方仙道及其后身黄老道的方术化和宗教化进程加快,将春秋时期从原始宗教文化中分化出来的道家、墨家、神仙家、阴阳家、五行家、方技家、术数家乃至民间的巫术重新综合起来,加上儒家的伦理纲常,形成比原始宗教高一个文化层次的新宗教——道教。
第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政治需要是道教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地广人多,社会底层大多数劳动人民处于不识字的蒙昧状态,诸子百家学说只能在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中流传。儒家学说在汉代虽为皇帝推崇,但只能教五经博士诵习,平民百姓多看不懂。君主为在思想上控制不识字的广大劳动人民,使其安定顺服,必须依靠宗教,故汉代皇帝竭力神化“三纲五常”,将孔子奉为教主,建孔庙尊孔祭孔,使孔子偶像化,儒学宗教化。汉成帝、哀帝时期又兴起谶纬经学,谶纬渐成儒家正统,称为“内学”。儒学同传统礼教结合,在执行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方面甚至超过公开的宗教。但由于这二者都过分依赖国家政权和族权,没有单独的正式宗教组织,当国家政治统治发生危机时,其宗教作用自然会受限制。故此,统治阶级感到有必要建立一种独立的、不和国家机构重合、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生危机时仍能起教化作用,并且维护封建宗法制国家政体的宗教,以弥补礼教和儒家学说在宗教功能方面的不足。于是,在东汉社会危机加剧、儒家礼教失去维系社会人心的作用时,道教便应运而生,把儒家的伦理纲常信条接过去,当做成仙的必要条件,对人民实行宗教的麻醉作用,但因道教接受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注定其无法取代儒教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而只能在维护封建宗法秩序方面起辅助儒教的作用。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统治阶级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后期更是肆意压榨,如《资治通鉴》中所称:“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后,汉光武帝刘秀继位,虽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业的措施,但因豪强的兼并和割据,大大束缚了农业生产力,使民众的苦难更加深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濒临崩溃,持续地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对于解除生活苦难的强烈需要使人民转向宗教寻找精神寄托,为道教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
第四,佛教传入刺激了道教的产生。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东汉中后期得到较广泛的流传。佛教是一种在教理、教义、组织形式和修持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世界宗教,其传入给华夏文化以巨大刺激,激发起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迫使华夏文明以模仿和抵制的双重方式作出反应。道教在大力吸收佛教的宗教形式以提高自身的宗教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同佛教抗衡,其各种要素逐渐形成——神仙家的阴阳五行和谶讳学说同老庄哲学结合起来被固定在道教的道义中;中国古代宗教的天神、地祇和人鬼神系统和被神化了的黄帝、老子被固定在道教的偶像崇拜中;专职的神仙方士编造了神仙所降的经典并改称道士。于是,一种具有多元的宗教思想和多样的神仙方术以及多神为其特点的道教形成了。
二、道教的特点
道教文化兼收并蓄,庞杂多端,《道藏》中涉及易学、医学、术数、杂家、诸子、地理、天文等诸多方面,学术界一般认为其主要包含史学、神学、伦理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六大项内容。道家与道教,从外表看,似可分离,但在实质上却大相径庭,秦、汉以前,道儒不分,甚至诸子百家也统统渊源于道,这个“道”的观念,只是代表上古传统文化的统称。儒道分家及诸子百家分门别户,发生在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间。汉、魏、南北朝以后,道教改变道家的学术思想,以与佛教抗衡,乃使道家与道教泾渭难分。唐、宋以后,儒家排斥佛、老,使道家与道教的界限更加模糊。事实上,秦、汉以前道家的学术思想,是继承伏羲、黄帝的学术传统,属于《易经》原始思想的体系,也是中国原始理论科学的文化思想。汉、魏以后的道,是以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为核心,采集《书经》系统的天道观念,加入杂家学说与民间的传说信仰,构成神秘性的宗教思想。
道教认为万事万物由三清尊神——原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所创,他们分别传授“三洞”真经——洞真、洞玄、洞神,“三洞”真经又分七部,通称三洞尊文、七部玄教,这是道教不可动摇的信仰基础。道教有三十六天、三十六地说,认为三十六天由三清尊神辖众神仙统治,是超脱轮回的美妙仙境。三十六地由十殿阎罗统辖,人死后,经“五道转轮”,善者为神为仙,不善者灵魂入禽畜道、饿鬼道、地狱道。道教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认为人命不决于天,道和生相守,生和道相保,二者须臾不离。人只要修道养生,便可长生久视。道教还有“天道承负,因果报应”之说,认为因果报应,如影随形,积善者入仙境,作恶者有恶报。行善积德,可为子孙造福,虔斋修道可免自身厄运。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和儒教、佛教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同时也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特点。
第一,从道教的教旨看,它追求成仙,重视现世利益,同三大世界宗教追求灵魂的解脱,重视来世利益迥异。三大世界宗教都提倡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幸福,漠视现实生活。道教却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生宝贵,应该从速修炼、成仙得道,才能永享幸福快乐。道教修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体生命与“道”的一体化。
第二,从宗教类型上看,道教是原始社会自发的自然宗教和阶段社会人为的伦理宗教的结合体。在古代社会,人们首先受到死亡和灾病之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威胁,而后是封建社会中国家机器的巨大社会压力的威胁,故道教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灾病、逍遥自在为特征,这不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化,也是对超社会力量的神化,道士正是为超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争取自身理想的现世利益而修炼。
第三,从道教的风格看,以修习法术见长,对神秘的力量和圣物不像其他宗教采取屈服、恭顺和虔敬、祈祷的态度,而是尽力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和支配它们,使超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道教要靠修习内丹和各种法术夺天地造化之功同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使命运屈服于自己,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道教一反其他宗教包括道家哲学对待社会人生的消极态度,鼓励修道士将修习长生之道当做远超世俗政治功名利禄的一项大事业来做。张伯端提出只有修成大丹,“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悟真篇序》。)。这样,抛开世俗入道教,修成大丹做神仙,对于在人生观上追求建功立名、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有强大的诱惑力。
第四,从道教的内容看,它比三大世界宗教存留着较多的民间信仰和古代巫术,又夹杂中国儒、墨、医诸家和佛教的思想材料,在内容上有兼收并蓄、庞杂多端的特点,在结构上有明显的层次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外来的佛教文化外,道教几乎把正统的儒家礼教所不收的其他文化要素都收了进去,又汲取三教九流的精髓并将其融为一体。但道教仍有自身众多的类别和系统,且随着道教发展阶段的不同、宗派的变化,崇拜的神仙也各有不同,不同宗派间既有信仰上的共通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刘勰在《灭惑论》中阐述了道教文化在结构上的层次性:“道家立法,厥有三品,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道安《二教论》亦说:“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录禁厌。”这些都说明道教神学大致是由宗教化的道家学说、生长术和仙学理论、各种斋醮符录杂术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化层次组成的。道教在教团组织和布道活动上一般也分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较大的层次。知识水平较高的上层神仙道士多诵老庄、修长生、炼大丹,下层民间道士多在乡村为民众疗病去灾、祭神驱鬼、画符施术。道教的这些特点是同中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的。
§§§第三节佛教在中国的流变
佛教产生于印度,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北天竺迦毗逻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其属释加族,创教后被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前三世纪发展并开始外传,一世纪传入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势力的强大,也由于佛教本身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在二者的碰撞中,经过相互妥协、吸收、排斥、融合而在唐代形成宗派。各宗派中,禅宗立足于佛教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的最佳契合点,而成为中国佛教。
一、佛教的传入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不管其宗教观念如何光怪陆离、荒诞无稽,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找到根源。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而得到发展,这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汉末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为缓和矛盾,统治者需要寻找更为有效的精神武器,而广大劳动人民也需要宗教的麻醉,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是中土社会所不具备的精神鸦片,满足了中土社会的需求。正如吴康僧所说:“佛教省欲云奢,恶杀非争斗,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法之良药,安心之要求,佛教始盛于汉末,殆亦因此节制欤?”(《法竞经序》。)同时佛教理论本身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使佛教得以传播。两汉神学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能直接赏善罚恶的粗俗说教,经不住实践;魏晋玄学偏于抽象化的论证,不适于群众中流传。佛教承认和强调社会现实社会充满苦难,并加以扩大,整个客观世界成为“苦滩”。困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中的众生,“生、老、病、死、怨憎会、受别离、求不得……”一切皆苦。作为佛教教义总纲的“四谛”,以苦为大。由此出发,按佛教唯心主义的思路,通过繁琐、复杂的论证,要人们相信:现实世界的一切苦难都是虚幻的,只要按照佛的指引,都可解脱,进入“涅槃”。这既容易渗入群众,也易于被统治阶级所接受。
佛教初入中国,上层统治者完全以固有的神灵和方术看待释迦牟尼和佛教。由于老子恬淡无为的思想与佛教涅槃寂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故佛教教理被理解为黄老之学。“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把道的清虚无为与佛的戒杀、禁欲等同,而佛的戒杀、禁欲是作为清除人生痛苦的修炼手段,与道家顺应自然的无为毫无关联。牟子《理惑论》中对佛的描述,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土社会对佛的理解。“佛之吾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方能圆,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把佛描述成一个法术多端、神通广大、变化莫测的神仙。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亦被视做祠祀相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