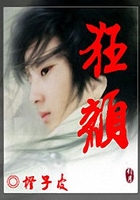嘤,嘤嘤,嘤嘤嘤嘤。……
江枫一睁开眼睛,就听到这奇异的声音。声音是从写字台上方的纱窗上传来的,听去颇有节奏感,似乎满含着欢乐和陶醉。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外的凤尾竹绿茵茵的新叶,照到纱窗上。纱窗上分明有一个正在颤动的黑点。那陶醉的声音,便是这黑点发出来的。
苍蝇!他惊讶地想,它们的提早出现,莫非要证明全球变暖这一事实的铁证如山么?他随即翻身下床,从桌子与墙壁的夹缝里找了一个塑料拍子,虎视眈眈地盯住了那黑点。他终于看清了,那貌似黑点的苍蝇,其实不是一匹,而是两匹,一匹骑在另一匹的背上,重叠着,两对翅膀神经质地抖动。他心头掠过一丝得意,小心翼翼地估量着距离,屏住气,对准那颤巍巍的黑点,高高举起了塑料拍。……
怪哉!若是往常,这些可恶的小精灵,只要拍子一举起,它们就会嗡的一声,一溜烟飞得无影无踪。然而现在,它们竟然旁若无人,目空一切,一动也不动!
嘤,嘤嘤,嘤嘤嘤嘤。……
它们兀自快活地呻吟,声音充满了陶醉。
“色胆包天!”江枫的脑子里猛然冒出了这句话;几乎同时,他又想起了一首名诗的前两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看来,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仅仅限于人类这个范畴。
“如果它们不是苍蝇,而是一男一女一对情侣,”他盯着苍蝇陷入了深思,“此时此刻,要是有人在背后一棍子打下去……”他的心陡地一紧,高举苍蝇拍的手不知不觉垂了下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人和动物,哪怕是昆虫,在爱情上应该是平等的。……”
顷刻,他的心里激起一片爱意。这爱意有如水波,在胸中嫋嫋扩散。他拿定主意,不再干涉这对苍蝇的私生活。
这是双休日的第二天。江枫放过了那一对苍蝇,就在阳台上照惯例做了一百个俯卧撑,接着胡乱吃了点东西,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准备一天不出门,为的是赶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这是首都一家杂志的约稿。他是社会学的教授,兼做着江城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红学家。
有人说,人与人的不同,大抵取决于业余时间。在完成了教育任务以后,江枫的业余时间大部分用来写作。他不仅撰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还喜欢写杂感、随笔、散文乃至小说。就为这,他又戴上了“作家”的桂冠,被选为省作家协会的理事。
他今年才三十二岁,作为教授,他实在太年轻了,他完全称得上是“年少得志”;但是从立身成家来说,他又未免晚了一点。他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不光没有结婚,连对象还没有找;不是找不到,而是不愿找。单身只影,住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他觉得屋里空荡荡的;独自一人过日子,没有柴米油盐的操劳,他又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写作来填补空白。他极少看电视,对上网也缺乏兴趣;在电脑键盘上打字,却使他乐此不疲,甚至颇有点上瘾。当着一篇构思成熟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了出来,他坐在电脑前反复吟诵,然后不紧不慢,细细地推敲,把文句改得越来越精,越来越美;改淂差不多了,再慢慢欣赏,细细品味,就像一位爱美的妈妈深情地欣赏经过自己精心打扮的心爱的宝宝,这是何等令人欣慰、使人陶醉的事呵!
每当打字时间一长,眼睛疲倦了,他总要跑到南面的阳台上去,久久地凝望远处,眺望那烟波滚滚的长江。就这样,他的眼睛很快能消除疲劳。
他写完那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他走上阳台,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然后手扶窗棂,把目光投向远处。
春天终于大踏步地来临了。江岸上的垂柳早抹上了一片新绿,像一团团绿色的烟雾。春水在漫涨,江面要比冬天宽多了。江滩上的麦苗一片葱绿,那一方方整齐的鱼塘在阳光下明镜似地闪亮。他索性把窗户统统打开来。一阵阵熏风扑面吹来,他觉得脸上痒丝丝,身上麻酥酥,心里醉醺醺的,仿佛喝了绍兴的花雕酒。他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而,当他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时,他忽然吃了一惊。在他楼前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一个穿着银灰色风衣、披着头发的身影正一阵风似地朝西水关的方向跑去,那颀长的背影分外窈窕,但步履却有点踉跄,像喝了酒一般。他凝神细看,一颗心顿时突突地狂跳起来了。那女子分明是他的同窗学弟赵璧辉的妻子白鸥。一想到白鸥目下的处境,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白鸥的丈夫赵璧辉,跟江枫一样,也是江枫的博士生导师林帆一手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现在是本校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兼院总支书记。新近,这一对原本被小区居委评为“五好家庭”的模范夫妻,却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离婚大战。谁也不知道赵璧辉为何突然要提出离婚,江枫上门苦口婆心地劝了好多回,都如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论职业,白鸥在省气象局当气象员,属于标准的白领阶层,而且年年都评上先进;论相貌,白鸥在学校所有的教师夫人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是人们心目中公认的“校花”。如此才貌双全的女人,赵璧辉却突然弃之如敝履,这叫江枫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据陪伴白鸥的小保姆传言,那天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白鸥始终昂着头,一言不发,脸色冰冷,尽管伤心欲绝,却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她回到那个已变成她独自一人的家里后,竟关起门来,不吃也不喝,整整哭了一天一夜!
昨天晚上,江枫突然接到白鸥打来的电话。白鸥的语气显得异常平静。她说:“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俺想替一位喜欢写作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
“弟妹,”他亲切地称呼她,“别客气,你只管说。”
“你别这么叫俺好吗?”她凄然笑道,“俺已经不是你的弟妹了。”
“好,好,我暂时不这么称呼你。”他尴尬地一笑“那你的问题是——”
“如果一个想跳河寻死的人是一名游泳运动员,你认为他死得了吗?”接着,她又连忙补充说:“俺说的这个人是我女朋友写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个男的,受金融风暴的冲击,破产了。俺的女朋友在写他寻死时就碰到了这么个难题。你是个大教授、大作家,你见多识广,你一定能给她一个圆满的答案。”
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江枫着实吃了一惊。但是,她的口气依然非常平静,也十分诚恳。
也许她的朋友确实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回答。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他斟词酌句地说,“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是,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看,一名游泳运动员,是不大可能采取投水的方式来自杀的……”
“如果他一定要这样死呢,比如说,他要让自己的尸体随着潮水从长江漂流到大海,再漂流到自己的故乡……”她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但接着话筒里传来了她歉意的笑声。
“这倒是个很浪漫的想法!”他也笑了,“不过,要看他投水的地点是不是在够他上岸的地方。如果他的体力足够让他游回岸上……”
“你的意思是说,投水的人在临死前会拼命挣扎,凭他的游泳本领最后会死不成?”她再次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有这种可能吧。”他含糊其词地说,“不过,一个人决意要自杀的话,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会……都会把自己置于死地。”说罢,他又觉得不妥,连忙补充道:“不过,自杀总不是好事。生命是宝贵的;连苍蝇蚊子都珍爱生命呢,何况人乎!你看现在的报纸、电视,三天两头就有自杀的报道,自杀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成了时髦的事;就连小学生被妈妈批评了几句也会跳楼。我看,这是目前最危险的一种传染病!”
“嘻嘻,你真幽默!”她笑了,笑得很自然,听不出半点做作。
……
由于白鸥当时出奇的平静和诚恳,江枫压根儿也没有往深处细想。然而现在,当他突然看到她向江边踉跄跑去的情景,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哦,她会不会是假托一个朋友,为自己提出咨询?她本人不就是一名游泳运动员?赵璧辉就曾为她得过青岛市的游泳冠军深感骄傲。而且她的老家就在青岛海边。何况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从此一个人流落在这个南方大城市,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让自己的尸体从长江漂进大海,再漂回青岛,这举动看似浪漫,但是凭她那种刚烈的性格,她做得出来!再说,人在决意自杀之前,情绪会变得出奇的平静,就像风暴来临之前的湖面。哎,哎,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昨天怎么没有想到这一些?
没有任何犹豫,他飞也似地冲下楼,向江边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