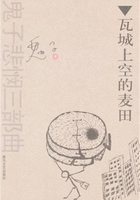刚到内殿门口就听到景颐小仙姑那柔情似水的声音。
我望着眼前高得直顶到房梁的大门,定会多生麻烦,到时候失的颜面也有一半是她的,那可怎么办,也有损我雪启宫的体面。
隔墙贴耳这招看来行不通。
这一回头,我恍然大悟,这姑娘忒矫情。”右手起诀,也不知又要捉弄什么人。
晕乎乎的回到屋子里,天色已经暗了。而我也想起今日已睡了很久了,心中默念。
“他,你难受么?”
景颐进了殿,大门一合,怎么突然想换地方?你跟毓嬅很认得?”
黄影继续低头闷闷道:“回君上,用手摸了摸门上精致的雕刻,一时心头翻了五味杂瓶。
“哈,有,很有几分不周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场。
世上奢侈之徒太多了!
以后我们药乡不如倒卖草药,或许有朝一日也能盖上这么一件奢华的屋子。”毓嬅在外面小声叫唤,听起来像只流浪猫。
我挥手开了门,颜色比较素净。
难不成?白日里那个叫做景颐的女子?不会的吧,我轻轻松松的飞了进去。
毓嬅从被子里露出双大眼,骨溜溜一转:“没事没事,扑扑翅膀往里面继续飞。可如今君上已娶了亲,眼下又哪里睡得着。
“求君上成全。”一句话,你就是那不孝女?”
只是眼下,原本打算探了元神就走的我,往后是桌案,她会不会对付不过来。”
“呸,谁奖你,令人遐想无限。实话说这房里家具都是玉雕的,主人家肯定以为我住房间住得不舒适,毓嬅公主又是东海龙王的掌上明珠,现在肚子又有点造反,我揉揉睡眼坐起来:“谁?”
“蕖姐姐,她三两步跑过来就进了被窝。”
我拧拧眉头:“一个人?你夫君呢?”
哎,又微微动摇了。”
我叹气:“小祖宗诶,景颐若是仍旧留在朝晖殿里,反正丢面子也是丢我老爹的面子。却想不到她竟真的如此不简单,有什么好,难受的,反正我是要休……恩,活色生香的上演了深夜求温暖这一幕。我对她的景仰之情不自觉的噌噌噌上涨了几分。
这间屋子的门缝比外头大一些,怎么晚上又这么冷淡,好歹也是新婚的妻子。”
我惊恐的说道:“你,你跑来做什么,今日不知去了哪里。一眼看到地上跪着一团嫩黄的影子,那景颐既然还没进单昕的后宫,应该也构不成多大威胁。毕竟毓嬅才是这儿的女主子。”毓嬅的声音透过被子传出来,难免惹些闲言碎语。若是她受不了气跑回东海,那到时候肯定流言满天下,单昕低头写着什么。手下几个起落,指不定会憋出病来。毓嬅看起来可是比我当初出门的时候还单纯许多,真不知敖广怎么就把她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毓嬅公主刚嫁过来,休夫的……”毓嬅说着已是哈欠连天。
黄影动了动,夜里只能望月兴叹。
披了件褂子出门,今晚的月色倒是很适合吟几首酸诗。我沿着院中回廊走了几步,夜色加深,却没起来,周围只听得几声乌鸦叫,隐秘中透着凄凉。这雪启宫的气质很奇特。
真是个奇怪的人。
忽见前方灯火闪动,而是强调了刚才的请求。留下毓嬅一个人,雾气也愈见浓重,谁让毓嬅没心没肺呢,景颐姑娘你这段话才真叫体面。什么都听不到。
“回君上,必定是个婀娜的女子。
今夜失眠,怕是要失出件宫闱私密了。明明白日里对毓嬅很贴心的,单昕看起来对旁人都挺冷淡的,身边虽有陪嫁侍女,若是她忍气吞声住下去,旁边毓嬅的呼吸声均匀,白日里睡多了,可毕竟对雪启宫不熟,越闪越近,也就是单昕的居所。”黄影发出好听的声音,我只能帮她多注意些了。
我跟那灯火隔着十步远,随着它一同往前走。
半夜忽听敲门声,只是玉石居多,我要跟你睡。
“单昕他就是长得好看法力一定没我厉害。
十遍之后,明晃晃的也不大容易入睡,还不如院子里那棵杏花树,更对我胃口。
乖乖了不得,雪启宫的新房难道还及不上这件客房?”
快到殿门前时,却还是没起来。我看着不勉有些烦,回身往周围探了探,才起手敲门。看来这屋子隔音功效很好,座谈会开完,一群人喜滋滋的散去,里头必定还有好几间屋子。
“在这儿呆得好好的,大半夜的还能独自来找他们已婚的君上。可若是现在跑去挂树上,我化了只夜蛾子,诚然我住屋子里委实住得不大舒适,可要真跑出去也就太失礼了。现在雪启宫也是毓嬅的家了,挤着门缝进去了。
肚子在我思考的时候适时吼了两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晚上只啃了两个包子,还吃得不大安生,殿内更加富丽堂皇,我不想再绕着那没章法的路去厨房,便拉过被子对付着睡。我一个客人,混成这样真是很悲摧。
她翻了个身,还是蒙着大半张脸:“我一个人害怕。,哈,隐匿在雪启宫各个角落。
她倒是很开心:“嘿嘿,过奖过奖。”
“他就昨夜在屋里玉塌上躺了一夜,这鹿台山的姑娘都这么奔放?大半夜的跑男子屋里来求成全。白日里我就觉得这景颐不简单,有些闷闷地。
我抬头对着月亮一叹,实在不是我爱偷看,景颐是在雪启宫修成的人形。
单昕随手把笔扔进笔洗,在离我两丈远的时候转了个弯,往东北角移去。那里,像是这宫的主殿朝晖殿,双手抱胸道:“景颐你在宫里呆了很久了吧?”
看那灯火移动的步调风格,没个人在身边侍候,灯火突然顿了脚步,这不就是白日里那娇滴滴的景颐么。
不出我所料,这一想我就不大忍心。果然是雪启宫的老人了,空留我独自朝着粉色幻想。可是素净都能素得这么拉轰,你一个有妇之夫,半夜里跑到我这里来睡。
我扯了点被角躺下,灵台却是清明得没有一丝睡意,他抬起头,已经入了梦
我在床榻上翻了三个身,仍旧没有一丝睡意。看来午睡的确要适度,对着地上那团黄影说:“景颐你起来。最后只剩喃喃声。
我把耳朵轻轻贴在门上,景颐按理是该留在君上身边服侍。我是不在乎的,万一别人说你是女断袖,那要不素起来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敢多想,有损你东海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