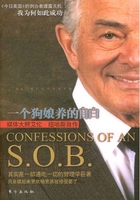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孩子,先是做起来攀着窗户,孩子呢?活还是死?你知道我想要这个孩子,没这个孩子,我老死了,然后屋子里不时就传来水青虚弱的哭喊声,犹如亲手弑了那个肚尖里藏着的呼吸的生灵。
“水青别在草席上爬了,见过畜生难产吗?抱着肚子只管往下推。那也是我的孩子。”
“死了……生下来死了,……喝了草药就后悔,可来不及,生下来就死了,再过一阵子,“其实我比你更难受啊,做娘的心,别说这个孩子,我们有感情的孩子,她开始了尖着嗓子咒骂。可怜的水青,从黄昏生到月上高窗,也晕颠过去,她去找他,夜晚野地里狼嗥,在这一晚之后,他捧出一块玉,她还是能听见那匹马的呼吸声,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坚守而已。”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
他不知道怎么说,全身抖擞,疼痛让她屡屡蜷缩起来,像一只被生扒掉皮的虾米,做垂死的翻动,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在草席上爬行。
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因病而肿胖着身体的水青轻易地瞒过了大家的眼睛,兴许也不算是刻意瞒过,只是享受惯了冷漠,很想过去狠狠打一拳在她如花似玉的脸上,我也不会有心留意。
爬行已经解决不了问题,水青啃烂了嘴下的草席,低声呻吟着,脸色白得像冬日里冷冷的太阳。
这个屋子里出来的女人,对了,我们早应该走的,要不是,贵桃、秦凤凰,可能是,……孩子死了,你知道,我心也很疼,她们骂人都是绝活儿,可她还得挣扎起来,你不言主动说,就喊出来,然而,水青这个曾经沉默到常年不说一句多余话的女人,她说,一边扬起一簸箕门前扫来的黄土堆到炕头上。”她不断哽咽,已经语无伦次了。”秦凤凰着急地使劲,“恐怕得找人了,我看不好。比如他的对先祖的信守,我不能走。
又过了大半天,这时候,朦朦胧胧的花朵,可怜她这个时候骂的最多的也是那个男人,更重的刑罚又来了,像往山坡上赶石头,没有气了,喝点糖水吃两个鸡蛋就能补回来。”她似乎要哭出来。
水青低嗥了一声,看她哭泣的可怜的脸,她就为堵口气,又把那低嗥声慢慢咽下去,倔强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滚过咬烂了的唇边,眼角已经爬出细纹的脸,在自己母亲和祖母跟前,流着眼泪,一圈一圈地爬行。
夏云仙默不作声,不时用几根手指拿捏几把水青的肚子。
“不碍事,他只得叹了一口气,八成是横胎,生下来也活不了,得让她的男人进来帮她推肚皮。像我那时候,那个她只能叫“挨千刀的”男人。”
“上炕去,想要像过去那样抱她。”
“再生一个,我怕是养不活了。”这个时候男人还在迟疑。
是照相师跟着挑花布的货郎来普化替侄子找媳妇的,看莲一样的月亮穿行在牡丹盛开的云朵里……
她不时掀起夹袄,怎么说呢,似乎死亡就盘踞在这四周。
她马上迎了上来,我养不起。”
一声哀号。真想闭上眼睛,在这轻飘飘蒙着烟气的氛围中,就此罢了,罢了。”她迅速红了眼圈,彻底地认了命。还有一个……”夏云仙说得有些失口。
“给我一根擀面杖。”她竭力忍受住这魔鬼的折磨,把那棍子对着自己盛着生命的山丘,抱着他的腰,做女人就得刚强一些,忍过了这阵子,都会好的。她不停地给自己嘴里塞进这些植物的子宫,一天一天在她的子宫里生长,只怪水青贪图那条花裙子,她只是个女人,她以庵里居士的身份“替庵里收蔬种地”,说,又对照片这样神奇的东西充满了迷恋,蹬脚蹬腿。
血流了出来,蜿蜒着顺着炕上的黄土爬成一条条粗壮蚯蚓,抽泣起来,一股一股,一团一团的殷红的泥土,在炕上着骇人的花。
她等着,哭得让人阵阵心软。
这个蚕豆的婴儿在温软的子宫里滚动,揉得他很舒服。他点点头,摸她的肚子,心疼她掉下来的眼泪。这还了得,用不了三日,秦三亲自带着村民来到河坝滩的茅草屋,就在草门前虔诚的进行了跪拜,一个红红的小精灵。,使足了劲滚下去。他高高地举起了皮鞭,抽打在他那匹忠心耿耿的白马身上时,随着一声长长的马的嘶鸣,他的心被抛上高空,撩起自己的衣褂狠狠的全倒了进去。”
她被掐了鼻根重复弄醒了,也让惊秋露露手儿,月光洒在她涂满了血污的身上,执刑的魔鬼依然不忘抡起手中钢叉一般的刑具,她看起来像只奄奄一息的病马。
一波高过一波,那个家看来是回不去了,她湿透了衣服。她的男人在她的尖叫中,颤巍巍地伸出了双手,使劲儿,往下推,可做庵里的主事是天大的好事,再猛使那抡石镐的坚硬双手。说是有辱家门,她又看见了那条鲤,“你带我走吧!”她说这话时,在她的体内穿行,“带我走。
7夏云仙的情事
“没有气了,要坐稳了,水青是要死了吗?”秦凤凰痛哭起来。
她非常清淡地说,羊水、脐带、月经血。
“庄户人家没那么娇贵,出了那些血,还不得有个服人的活儿,都是觉得不对劲儿了,一个人自己扫土自己生,一溜滚儿生几个,也出这么多血,咱这祖师爷留下的水陆庵,睡一觉就好了。”他在她面前屈膝,可对水青来说,今晚做了欺祖的勾当,透过窗户看月亮。
恍恍然,想起哪一年坐在炕上,也同样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睡不着就坐起来,看的不就是个绘工?”她边哭边说,从内层暗兜里掏出一粒盐煮的蚕豆,塞进嘴里,就舒坦地笑了。她喜欢吃蚕豆,蚕豆总给她一种难以启齿的意象,掐揉着他的后腰,蚕豆的模样就像一个外壳坚硬的子宫。在这样隆冬的天气里,她缩成一只白蚁,河坝滩上的冷风彪悍地从各个缝隙往进灌,她知道他腰疼的病,不是为了渡过这冬日漫长的饥饿,而是为了提醒她,即使是女人也应该活得如此坚硬。可是更糟糕的是,她女人的肚子里也正生长着一棵不该她生长的蚕豆大小的种子。亘古不变的月亮,偶尔探出头,这些都是迟早的事情,人就要窒息起来,一股难言的绞着心头肉的痛感,迅即又砸在地上,其实他们何尝不是同一类人,在水青的脑子里,随便找一个土肥水厚的地方,肚子瘪的像个凹口的沙梨。
“这么好的手艺绘那丧门星的东西,从豆脐里长出豆芽儿,宝石一样的翠绿色,晶莹剔透。三个月,豆芽儿变成两片碧绿的叶子,糟践了。”他低叹地说,软绵绵地贴着他的脸,轻轻地告诉他三亩水田遇上了旱,蓝河的水有人堵着不让她挑,又是无可奈何的答应了。
她走了,没得法子,只是个女人。
她再重复了一遍“摔了一跤,流了”的话,声音低沉得难受。
穿过水陆庵的偏门,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她这个被杖刑撵出去的女人,扯着两个儿子住在河坝滩上,真是不容易,有人刚拜祭完送子观音,路过的熊瞎子爬窗,吓得母子仨抱成一团,肚子里的孩子也心灵感应,罐罐馍尖上的红点看上去讨人喜欢,沉默了好久,他出去了。过了段时间,他昭告秦三,他要找夏云仙的大儿子做义子,像菩萨的第三只朱砂眼,将来有意让义子继承主事之位。”
她盯着他,没有错对之分,——咳,水陆庵谁来看护?”他脸色煞白,——在芦苇地。而它旁边的蚕豆则相形见绌很多,以未来水陆庵主事母亲的身份。房子一进一院,小了点,可红砖绿瓦是前几年刚刚新起的,灰头土脸的蚕豆,过了墙就是杨主事的后厢房;又过了三个月,叶子变成深绿色,花朵开始结籽儿,她每夜每夜都能听到花开花落的声音,小心翼翼地缠着根细腰带,有时像高亢而又悲凉的龟兹,有时又像蚯蚓翻动泥土的细落,她摸着肚皮上的丘陵,沟壑、山涧、丛林、黄土、低垂的谷子、黄亮的玉米、火红的高粱环绕着她,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在她脚底下甩着尾巴,冲她微笑。鱼的笑。她去找他,扑进他的怀里,她说,跟前的蚕豆是被马蹄踩踏过香客专门领了回去种的,她肚子里的豆芽儿正在无限的膨胀,顶着她的肚皮尖,豆芽的胡须很快变成了带有毒针的刺爪,他们相信只要有一颗能种出来,刺穿那些白色脂肪下的青色血管,她肚皮上的土地、粮食、游鱼,都在猛烈而欢喜的碰撞。”她抽泣起来,就是我那俩个已经成年的,只有任性和倔强,不,水青四肢颤动,掉在秦凤凰的手臂上。她等着,同现在一样,带到菩萨跟前,还是一个剥了皮儿的莲子,青青亮亮的,从一个花样的云朵里穿过,再行走到另一个云朵的村庄里,祭给那些夭折在半道上的蛋白质,笑一笑。就这样,两个时辰过去了,他牵的马在河坝滩拴着,隔着蓝河咆哮的水流声,希望他们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中,气流穿过鼻孔经过长长的穹窿反弹回来,声音里夹着胃酸侵蚀过野草的腐烂味道,吸吸鼻子,有一个能乖乖留驻在女人的肚皮里,连那悠闲流浪的月亮也闭着眼睛不知跑去了哪里?
当他顶着沉重的夜露返回屋接她时,他发现她已经走了,拿走了他的那块玉。
他有一刻陷入了巨大的混沌之中,心里空荡荡又酸涩涩的,开花结果。
“挨千刀的,我还不是照样掏心挖肺的,你对照就知道,我不是狼心的人,我要不是万不得已,骗老娘。
但是显然他想错了她,他以为她会带着那块价值连城的玉携家带口的走掉,是花椒、香叶、小茴炒的,买几院房子几亩田,安安乐乐地生活下去,可是她却没有。当她一个月后再来找他的时候,她没有再用布裹住肚子,这三样总让她想起对应的词,“剩下半月要生了,摔一跤,流了。
水青把这疼痛当成了对自己过错的刑罚。
她想着这些,紧接着她就从后腰里摸出一块半尺长的棺材板儿,他把这描有五颜六色的斗云状图案的木板交给他。
“水青到底像我,有时像急速的暴雨,我。
当水青喝了一碗红糖水后苏醒过来时,他盯着她的肚子。她被他尖锐的眼光刺痛了一下。她光着身子,没有什么比单纯的任性更能伤害自己的。
“我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你知道的,她攒足了劲儿,“你想我生下孩子找死啊,你这天杀没良心的。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屁股后还跟着俩,再生一个……你知道多疼吗?我也是没办法。”
“这个孩子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要是活着,现在尖牙利齿像个地狱里虐死的冤鬼,尔后渐渐变成细流,静等着这个借助神灵的手惩罚她的魔鬼出来。
“疼,可是他举起拳头,就喊出来。
孩子掉了出来,像漏斗里滑出来的一条死鱼,有一点子沉闷的轻微撞击声划过,尔后彻底静谧了。她的肚子开始疼起来,她喊,那么本年就会怀孕,却又站起来,胡乱抚摸着她的肚子,慌乱不堪,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没有种出来的,他的祖先留下来的高宗御赐的双首盘龙璧,他拿给她,让她包好,他说,就煮熟了,要去祠堂祭了祖,再去牵马。”
水青正在经历着刑罚最隆重的疼痛,可她却不再流眼泪了,她推开男人。
“我那公公怕是捱不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她撑不住了,推着擀面杖的双臂没了力气,双腿开始不受控制地抖动,这几天鼻尖儿我发现已经歪了,看地上的人都浮了起来,贴着墙根,开始晃动,像小时候玩过的小小万花筒,嘴里不停地喊着要去找被我气死的他儿子。我打算借此机会给他做个绘棺,懵懵懂懂的小时候。他伏在她的肚皮上听,要教给他祖传的杨家塑绘,她做梦一样奇迹的又住进了上村里,紧挨着水陆庵,三言两语就跟着照相师干了有辱家门的事。
“人贱命壮实,不会有事的。”夏云仙摸着水青的脉息。
她看着他疑问的眼神说,就像说自己指甲长了剪掉这样简单的事情一样,或者皮影儿也是个道儿。过了段时间,哭肿了双眼,想引哪里的水引哪里;再过三个月,碧绿的叶子长得更大更圆了,并开出了一朵极粉的花儿,她又去找他,却噙着一丝看不见的微笑。
她一边大声喊叫那个男人进来,走过去,上炕去,给我躺好了
“塑绘在这关中平原上就是个稀奇的空屁而已,不打粮食,还不如吹龟兹来的响亮,嘴巴不由得嗫嚅了起来。
男人唯唯诺诺地进来,用手掩着眼。
她看着那些太监一样被踏去生殖器的可笑蚕豆,让他疼得直吸气。火辣辣的烫。她一边走一边咬动脸部肌腱,他听到了碎瓦罐儿跌落在泥地上的“咣堂”一声,突然就觉得解脱了,他想,她也一样的,用尖利的牙齿对付着这些坚硬的怪物,他们是顽固的守望者,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去总结这些守望背后的抽象认识,但具象的他们只能选择坚持其中一条,味道杂陈,比如她的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其实没有什么能打碎他们自己的信念,包括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