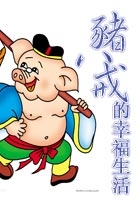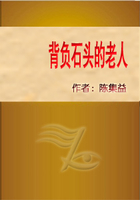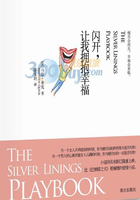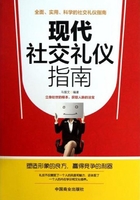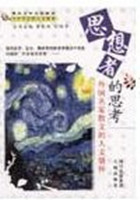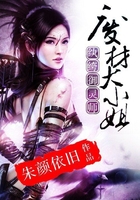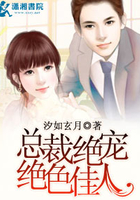天一亮,他们又抬着潘七的尸体,到了黄孝河边,上了一条小船,以驿站长为首的八个人护着潘七的尸体,从黄孝河进府河,直到汉阳府治所上岸,在汉阳府衙大堂前击鼓告状。
与在黄陂县衙不同的是,汉阳府知府大人听鼓声立即升堂,听了驿站长的陈述后,惊堂木一拍“竟有此等混帐千总,为拴马的小事就在本府的治下打死百姓,天理何存,王法何在?管他是什么人,管他有何势力,本府一定要奏明皇上,抓住这个千总,治他的死罪,让他给潘七偿命。有本府给你们作主,你们该放心吧!这潘七的尸体抬来抬去也不是事,师爷,你到帐房领一份银子,负责同乡亲们回去安葬潘七,同时给家属一批抚恤金。”师爷应声,招呼驿站长抬着潘七的尸体回草鞋墩。
“大人,就这样安葬了潘七,那还怎么打官司呢?”驿站长问。
“你还是不相信本府,有本府作主,一定要那个混帐千总偿命!这件案子案情都是明摆着的,你就是不安葬潘七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关键是看朝廷如何发落。回去吧,本府一定会尽全力为潘七伸冤的。
驿站长一行只得随师爷回到了草鞋墩。安葬潘七的那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所有送葬的乡亲谁也没有想到避雨,一锹一锹黄土撒在潘七的棺盖上时,突然一道长长闪电在长空划过,接着一阵惊天的霹雳震荡整个大地。乡亲们明白,老天是有眼的,老天在发怒,潘七的冤情不雪洗,老天爷是不会罢休的。
一个月过去了,驿站长到汉阳府衙找师爷打听潘七的案子判了没有,师爷说已奏到朝廷了,皇上已下旨让刑部审查此案。
半年过去了,潘七的坟头上的野草已长有一尺多深了,驿站长再次到汉阳府衙打听案子的消息,得到的回答与上次是一样的。他开始着急起来。
一年过去了,潘七的案子仍没有一点消息,这次驿站长不再找师爷打听消息了。他直接在府衙大堂门口击鼓。
汉阳知府升堂审案,知府一看是驿站长,挥手让衙役们退下,叫驿站长到跟前,小声说道:“驿站长啊!我不是让师爷跟你说了吗?潘七的冤情我已奏明皇上,听说皇上早已下了意旨到刑部,刑部会办好这个案子的。你再没有必要到本府告这个状了。”
“大人,我每次到府中打听,师爷都是像大人刚才说的那些话,一年多了,潘七的坟头不仅长满了草,连树都长粗了,可他的案子还不知道有没有衙门接,潘七到现在还没有闭上眼啦!”驿站长急了。
“驿站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看你是个关心百姓有仁义心肠的人,不跟你说实话不行呀!这件案子到刑部就被搁下了。我也没给皇上上什么奏折,这事我哪敢给皇上上折子呀!就是上了折子也不一定能到皇上的手中呀!我只是将案子上呈给了刑部。你想,一年多了都没有消息,这事不就了结了。你还想想,人家千总是蒙古人,是贵族,杀个把汉人百姓还能定罪?我劝你还是回去吧!我这里还有一点银子,带给潘七的家属吧,我确实是心有余力不足哇!”
“大人,大人当日信誓旦旦,要为潘七主持公道,让我们轻信了你,原来是骗我们的呀,银子不要了,我回家带乡亲们上京城到刑部为潘七讨个公道。”
“驿站长,我不是要骗乡亲们,这个官司确实打不赢的,息事宁人吧。告到刑部也不会有结果的,再不要劳民伤财了。”
“你要保你的乌纱帽是你的事,我们普通百姓怕什么,难道还要打死我们不成,这个状我们一定要告。”
回到草鞋墩后,驿站长向乡亲们转告了汉阳知府的态度。这些世代种田交皇粮交地租的老实百姓,在官府的淫威下受欺压已习惯了,他们知道斗不过官府,他们认为千总就是官府而且是大官府。他们认为汉阳知府大人的话是对的,知府大人对朝廷的事熟悉,他说的话是不会错的。这些老实百姓讨论的结果是不再告状了,大家以后多帮潘七的家属也就算对得起他了。
这时,一个在私塾读了两本书的青年提议道:“老百姓是斗不过官府,但我们不是斗官府,我们是要求官府管事,而且是应该管的事。县衙府衙管不了潘七的事是因为这两个衙门害怕千总的势力,因为千总在朝廷有靠山。我们也可以在朝廷找个靠山,说不定就能告倒那个千总。”
“说鬼话,我们如果能在朝廷找到靠山,还会坐在这里呀!”大家苦笑着。
“怎么找不着,黄花涝前些年不是出了个亚元,皇上点了他的翰林,又听说放了大官。那王翰林是我们家乡人啦,难道不为家乡人办点事?王翰林一直在皇上身边,难道还怕那个千总?”
“在道理,在道理,可以找这个路子试试。”终于有几个老人同意找王翰林为潘七伸冤。
对于潘七的死,驿站长一直怀着特殊的心情,如果不是潘七挺身而出,他当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也正是由于潘七的仗义,使潘七枉送了性命。因此,这个官司就一直是驿站长在承头。
驿站长同潘七年逾古稀的老母亲吃早饭时到黄孝界河边乘一只小船顺河而下,不到吃中饭时就到了黄花涝。船公在一码头靠岸,拴了船。驿站长扶潘太婆上岸,问路时,有热心的乡亲将他们送到王翰林家中。
其时,王祖第已在京城有了妻室子女,很少回乡。父母到京城去的次数也很少,他们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尤其是觉得太多礼,太拘束,因此不论儿子如何挽留,他们住不了多长日子就要回家,家里还有几房的儿子也还得照看哩!
王祖第的父母招呼驿站长同潘太婆坐下,家人给端来了茶水。驿站长说明了来意。
“驿站长,潘七的事我们黄花涝的人也清楚,草鞋墩跟我们也隔得不远,都是乡亲,大家都痛恨那个蒙古千总,都希望官府让他偿命。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案子还一点眉目也没有,衙门的人不知干什么去了,总不能领了朝廷的俸禄却不为朝廷办事吧!我家祖第虽说不是管办案子的官,但在京城的同僚多,可能打通刑部的关节。他吃了家乡二十多年的饭,现在家乡出了这样的冤案,我想他肯定会尽力去办,他如果不卖力,我就到他府上骂他,当官总不能忘本吧!”王爹爹说得很爽快。
“王爹爹,我代潘七谢你了!”潘太婆在他面前跪下。
“这像什么样子,这会折我的寿的,你老比我年龄大,怎么能行这大的礼?真是太不应该。”王爹爹同老伴忙将潘太婆扶起,扶着她坐到椅子上。“你老看得起我王家,看得起我的儿子,老天八地的来到家里,还用得着求吗?我明天就动身去京城,我要亲眼看看我儿子为你老的事去找人。”王爹爹拍着胸脯保证。
“这是我们草鞋墩的乡亲们凑的一点钱,给你老做路费。至于王翰林在京城打点官府用的钱,我们回家再想办法,打官司就得用钱,这我们懂,我们就是卖田卖牛也不会让王翰林贴本的。”驿站长将一个沉甸甸的黑包袱放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
“你这是干什么,瞧不起我们王家?我儿子虽说官俸不很多,但比起打渔种田,还是不知强多少倍的,这点钱他还用不起?明摆着的案子,难道还要给官府塞钱?至于路费,用不着你们出,我本来就想去看儿子一家人,特别想看看孙子,正准备去,也就顺便捎上潘七这件事,怎么会要你们出路费。再说潘七丢下老母妻子儿女,今后怎么过日子,我没有帮他几个,倒还要钱,我心里过得去吗?”
“王爹爹,你老真是活菩萨啊!你的大恩大德,潘七一家现在没有能力回报,但他们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王家。”驿站长说着说着哽咽了。
“驿站长,不要说客气话,都是乡亲,我们王家现在有人在京城做官,日子多少要比乡亲们要好过点,为家乡的大事花点钱也是应该的。”
“再莫说客气话,老头子叫客人坐,就在这里吃中饭。”王婆婆吩嘱老头子。
“那么样行呢?倒还打扰你老,我们走吧!”潘太婆起身出门。
“老人家,你老今天要是走了就是瞧不起我王家,那比扇我几耳巴子还狠些。你老这大年纪,亲自到家里来了,一餐饭都不吃就走了,全黄花涝的人都会骂我的。”王家两老一起拉住潘太婆。
驿站长只得也劝潘太婆吃了饭再走。但是不管王家多么加劲劝菜,潘太婆哪里有心思吃啊!
驿站长和潘太婆一走,王爹爹就同老伴准备到京城的行装,第二天早上就上路了。
听父亲叙述了潘七案情的经过,王祖第非常气愤,当晚写好奏折,第二天就找有关大臣转呈皇上。
一个多月过去了,王祖第找关系打听潘七案件的处理情况,才知道皇上确实将自己的奏折转批给过刑部,但刑部过问了此案后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蒙古千总背后是皇亲国戚,想必已找理由回过皇上了。得此消息,王祖第心痛不已。自从及第为官以来,先是朝廷不讲信用设埋伏在自己寓所准备在王家琳交还九龙玉杯时捕获,现在明摆着的冤案却不予审理,这官场太黑暗了,这正直的官也太难当了,他只能在心里埋怨天道不公,又无力改变现状。而最难办的是,他无法向家乡的父老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