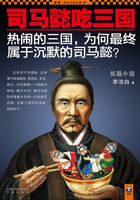王启梦还是在家乡结婚了。
婚礼举行得非常隆重。披红戴绿,坐八抬大轿,吹吹打打,拜天地、入洞房,热闹了一整天。洞房也裱糊一新,宽大的里面还可摆放衣服的架子床,嵌象牙花的大衣柜,箱柜桌椅摆设齐全。当牵亲婆走出房门,告诉王启梦去揭新娘的盖头时,他才清醒过来,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刚才不是在梦境。
他在洞房徘徊,清理着自己的思绪,想让自己静下心来,想想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些是自己主动做的,哪些是被人牵着做的。以前他厌恶这些繁琐的礼节,乡村中有婚丧嫁娶的大事从不去看,就是听别人谈到这些细节也觉得可笑,他是受鲁迅影响过的现代大学生,应该是反封建的斗士。但是,刚才自己怎么啦!自己干的事不正是封建礼仪吗?
中国大概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路。
他现在头脑真的清醒了,完整地记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改革,谈何容易,你想前进一步,就有人要拉退你三步。这样想着,他又烦恼起来,由于走来走去累了,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你在搞么事啊!懂不懂规矩哟,还不来揭盖头,未必还要等我自己揭。”盖头下传出一口没碟子即汉口方言,那声音既响亮又有一股傲气和泼辣。
王启梦一惊,不自觉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原来房里还有一个人,原来他还有揭盖头的任务没有完成。他立定在房中间,不知所措。
“我说的话听见没有?”语调中有一股威严。
王启梦被这股威严震慑住了,他像被逼进山间小路上一样,后有追兵,只能向前,别无选择。他伸手揭开了红盖头。
“你是个苕吧,大学生的名声是花钱买来的,怎么在房里一会儿走,一会儿坐,该做的事都不晓得做。”新娘露出了真容,脸相还不错,只是擦抹粉太多,穿金戴银,珠光宝气,时髦裙衣,这些只在北平富贵女人身上所有的东西她都有了。
这一夜,在这个女人的威逼和诱惑下王启梦没能坚守住自己所设下的防线,他屈服了,不但屈服于家庭,也屈服于这个女人。他记起了魏国生引用的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气太重,如此社会,如此家庭,就不是书生又能怎么样呢?
新娘对王启梦颐指气使,对下人指手划脚,也少不了骂几句。王启梦真是难堪极了,他常想,怪不得在汉口嫁不出去愿意嫁给乡下人,原来是头河东吼狮,我这辈子算彻底完了。
新娘在黄花涝住了一个多月后,对全家人都不客气起来,动不动就发脾气,咒骂乡下太小太不热闹,闹着要搬到汉口住。王启梦的父亲也被吵怕了,吩咐人将汉正街商铺的货房收拾两间出来,又重新买了新家俱,择日供了祖宗,让一对新婚夫妇搬到汉口去住。
新娘住到了汉正街,对她来说才真是如鱼得水,她开始只是逛商店,今天买这,明天买那,后来商店逛烦了,在家里也觉得无聊,就邀一些原来的朋友来家打麻将,王启梦又不会搓麻将,除了受人奚落外,还得对这些人装笑脸,因为只要新娘输了钱,就会找他的岔子吵闹,他的心因滴血太多而麻木了。
是啊!谁叫他百无一用,摆脱不了这个家庭呢?当柳若梅随魏国生走后,他跑遍了武汉三镇,没有他能做的工作,他就要流落街头与乞丐为伍,而那些乞丐也是不好缠的,少不了你的苦头吃,他尝够了挨饿的滋味,尝够了被人嗤之以鼻的滋味,遭人白眼还算是礼遇。一个少爷沦落到这种境遇,已经够他受的了。这时他投江的心都有,但又怕世人嘲笑,担心柳若梅为他痛苦,真是走投无路啊!鲁迅先生说走的人多了就是路,如果大家都走这条路还算路吗?世界如此之大,芸芸众生都在忙碌着,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生机呢?
眼看真的要倒毙街头了,王财记的伙计找到了他,好像是伙计们硬逼他回店铺的,其实他也有这意思了,不说是回心转意,至少是想先保住性命再说。
一个月后,他接到了柳若梅的信,信是以徐志摩的两首诗连在一起开头的。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信的正文很简单,仅有几句话:
王启梦同学,社会这所大学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一切都该重新开始了,希望你能坚强些,努力前行。我会记住我们以前的快乐日子的。
新的路靠自己去走,一路保重。
柳若梅
柳若梅这几行文字,似乎含有绝交的意思,难道她已看出我没有摆脱封建家庭的本事,没有带着她在社会上独立前行的能力吗?太让人伤心了,我太无能了,找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作,竟一事无成,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带着她争取自由!以前的理想,全是空中楼阁,现在再想起这些话全是对自己的嘲讽。不行,我们不能就此结束,我要去找她,哪怕是在江边扛码头,也要争取带她过上自由独立的生活。对,好多话对面不好说或会忘了说,先写一封信再说,也像她那样引用徐志摩的诗。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若梅,接到你的信我痛苦极了,我恨我的家庭,但我更恨我自己!我为什么这么无能,找一份工作的能力都没有,我不光养不活你,也养不活自己,像这样的无能之辈,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
但是,我舍不得你,没有你,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请你相信,我一定会改变自己,就是当一个码头工人,也要养活你,实现我们自由的理想。
见面后,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现在我急着想见你,想不出要写的话。
王启梦
第二天一大早,他偷偷溜出商铺,他知道伙计们这几天一直在盯着他,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吩咐,不然怎么会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碰上他们呢?
他来到江岸火车站附近,找到那晚魏国生领他们来的一间旅店,向伙计打听,说是只住了一晚就搬走了,问走到哪里,伙计说不知道,他拿出柳若梅的信,才知道因自己接信后太激动,竟没发现信上没有详细的寄信人地址。他这时真的恨起自己来了,那晚他们约定由魏国生帮她找工作,他自己找好工作后再来找她,谁知一找就是几天,什么工作也没找到,他哪有脸面来见她。再后来,回到了商店,更没脸来见她。在她看来,是我不顾她了,主动疏远了她。我真该死,连向她说明实情的勇气也没有,百无一用是书生嘛!现在怎么办?她肯定不愿再见到我了,到哪里去找她,再拖延时间,误会只会更深。今天我得勇敢点,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向她说明实情,明天我就到码头上去扛包,不相信我就锻炼不出来,会连一个女人都养不活。
他来到岱家山军营,向卫兵打听魏国生的营房,根据指点,他来到营房,熟悉情况的士兵说魏排长已调了部队,不在了。他心中一急,也忘了问魏国生调到哪个部队,回头跑到江岸车站附近在各棚户间打听,但一无所获。
夜幕沉重的时候,江岸车站附近的棚户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疲倦的人们陆续进了棚内,他也不再问人了,站在大路口张望,行人走过他身边有的绕了过去。
“少爷,太晚了,回店去吧。”一个伙计过来喊道,他吓了一跳。
“你们是我的魂吧!怎么我不论走到哪里你们都知道,像尾巴一样。”他发火了。
“少爷,怎么骂自己呢?是又累又饿吧!”
“滚,我不回去。”
“那我就陪着你。”
王启梦只得回到商铺。他太饿太累了,只有圣贤才不在乎肚子的感觉。他是普通人,为了肚皮放下个人尊严是常有的事。
第二天,他去了码头,工头认识是王财记的大少爷,客气地说只要他上船背一包盐上岸就留下干活。好心的工人们说没试过他的力气,第一包就从船上背上岸,如果走那窄窄的跳板走不稳,栽到江里去了就救不起来了,不如就在仓库里先背一包走几步试试。他让工人抬一包上肩,就在盐包落肩之时,他感觉是一堵墙砸下来了,退了一步,盐包砸到后背,他爬在地上,盐包压在腿上,用力抽都不出来。好心的工人推开了盐包,问砸伤没有,好在他能站起来,说明没事。工人教他,盐包来了不用肩去接着,只会越让越吃亏的,要是在船上就掉到江里喂鱼了。工头笑着说大少爷是劳心者,这扛码头的事,如果想干下辈子吧!
他又愧又恨,又找了很多地方,仍是没有能干的事。他彻底气馁了,向命运屈服了,就住在商店的客房里不再出门,吃了睡,睡了吃。等到父亲安排的人来跟他谈婚事时,他赌气地同意了。
现在一切都越来越难堪,那个女人跟他没有共同语言,还是一个典型的泼妇。据说她父亲还是汉口商会的头面人物,她动不动抬出父亲笑骂他家。
他现在清醒了,明白了。与柳若梅是不可能重圆旧梦了,与这个泼妇也难于过下去的。他又记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他采取了逃避的方法,每天吃完早饭,带一把油纸伞,怀里揣两本书,溜出住处,乘渡船过汉江来到龟山上。找一处树荫下的大石块,坐观江汉合流,千帆竞发,心情开朗多了。
他翻开书,是鲁迅的《伤逝》,这些日子,他完全沉浸在这篇文章之中,他自比文中的涓生,当然只是涓生的不幸,他知道自己比涓生差远了。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若梅,为自己。这是他读开头一段时从头脑中闪现出来的。他知道自己的文笔不行,而且现在的中国是无写处,所以只能在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文字。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多么有力的豪言壮语,我们也说过这样的话,但现在呢?别人不干涉能行吗?不受别人的干涉能生存下去吗?活着是多么不容易啊!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啊!”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过去得太快,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情景。
“然而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若梅现在怎么样了,她为什么不给我来信,为什么躲着我,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一个外地女孩,受到这样的打击承受得起吗?如果她有事,我这一辈子是不得安宁的。”
“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无能,我有罪,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被一个泼妇奴役,我不能算一个男人,我该进地狱,只有这样才没有悔恨和悲哀。
“我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前行,但到哪里去呢?
哎,这个社会呀!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晚霞映树,飞鸟投林,轻风拂动,江水波光泛金。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家,我们家在哪里,能回到那个泼妇的房子里吗?如果她今天运气不好输了钱,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乱子来。但是,不进那个房子,又能到哪里去呢?
当他回到住处时,今天却异常的安静,住房里一个人也没有,问了商店的人,说是新太太到外面打牌去了。
直到半夜新太太才敲门,王启梦打开门后问她怎么这晚才回。
“你嫌我回晚了,我明天还要回晚,我或许就在外面过夜。”太太恶狠狠地吼道。
“又是谁惹你了?”
“谁惹我了,我也不知道谁惹我了,别人能一天都就离家不回,我就不会也离家不回吗?你嫌我,我还嫌你哩!你有狗屁用,工作工作找不到,生意又不会做,如果不是我娘家的名望,你家的生意又维持得了几天。”
“照你的意思,你没嫁到我家时我家就不做生意了,难道我家的店是你家帮助开的?”
“你家会做生意吗?你家的生意现在还有钱赚吗?你们家现在有一个上得了场面的人吗?”太太更凶了。
“我就不信,我们家这么大的产业会靠你家支持,明天我就去做生意,我想这总不会是天大的难事。”
“你去呀!为什么天天跑出去躲着我,老爷早就逼着你做生意,你就是不干,有什么本事你就显出来。”
“我现在不要老爷逼,我自愿去。”
“看你这熊样子,也难于上台面。”
“有言在先,我做生意,你不要去干扰,你要呈能,你就去做,我不去。”
“我才不会去你们家那破店哩!我们家的店比你们气派得多。”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王启梦打算过几天到店里做生意,通过繁杂的日常事务慢慢忘掉失去柳若梅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