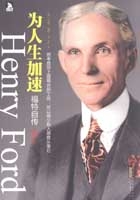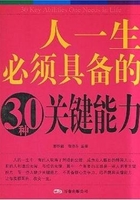清脆的,是杯盘落地的声,接着是男人失去理智地咆哮着。他说:“最烦你这个样子了,你知不知道这样的你很让我烦?桥桥就不会像你这样。有趣吗?逼迫我,你觉得有趣吗?”
小乔穿上衣服。在客厅里,看见一地碎了的玻璃杯片——刘莫一直用它给水仙花浇水。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小乔,让她去XX地把刘莫接走。那是个陌生人的声音。
她找到刘莫时,她正坐在路边的台阶上,表情很麻木,整个人苍白的像张白纸。不知道她已经在那里坐了多久,像是已经进入了幻觉。她正在发烧,身体哆嗦的像只筛子。即使这样,她依旧拒绝去医院。
晚上,她给她煮了皮蛋瘦肉粥,买了褪热的药拿给她吃。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黑暗里我清楚地感觉到她抖动着肩膀。小乔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忽然她大声地哭了起来。自始至终她什么都不肯说什么,只是哭。边哭,边抓起一旁Alawn留下的剃须刀,握在手里疯狂地割着左手的肌肤。
她抢下她手里的刀片时,被划伤了手。血流如注。
烧退下来。刘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三天三夜。小乔请假,照顾了她三天。
Alawn走了之后,就再没出现过。他就像是天空里飘过的一团烟雾,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去了哪里,再没有人知道,像是整个人被凭空抹去了。而桥桥是谁,她也没有问过刘莫。
刘莫愈加的憔悴。她不再背单词,不再环游世界,而是夜夜流浪在外,每天喝的醉汹汹的回来,甩到脚上10CM高的细高跟鞋,妆也不卸便倒头睡在楼下的沙发上。有时候醉的厉害,会敲开小乔的门,抱着她,把头压在她的肩上,边哭泣,边含糊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她放开她,她就扑到在地上。脆弱和绝望清晰可见。偶尔一两次清醒着回来,也会再从冰箱里拿出酒喝到醉倒。
后来的某一天,她忽然把头发剃光了回来。整个人好象坚强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脂粉的痕迹。利落,干脆。她让小乔摸了她剃光了的头。脸上浮起的笑容像一朵枯萎了的花。
她问她:“要去哪里?”
她说:“她想去西藏,想看看虔诚朝拜的信徒,想被圣地洁净一下空乏的心。“
果然,第二天她就出发了。小乔起床的时候发现她已不在。只是留了字条:不日归来。
在她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她经常会做些古怪的梦,梦见她穿着七彩的霓裳从云的那边飞来又飞去,手里舞动着粉红色的丝带,宛如仙子。她对着她温和地笑,灿如繁花。
小乔依旧忙而有序地生活着。在小店里等待着购买它的人。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人。但是生活充满了期待。
在她快要上学的时候,刘莫降临在小店的门外。原本苍白的脸晒成了抢眼的高原红,气色也好了许多,新长出的头发倔强地矗立着脑袋上。她穿一条黑色大花的长裙,很醒目,也很漂亮。站门外对着她微笑,就像梦里见过的一样。
她开始忙碌起来,因为有个人说要购买下店里的大部分的东西。
等到事情完结之后,才发觉刘莫早已悄然离开。她给她留了封电子邮件,说她不再想去环游世界,她选择了做一名山村女教师,说那边已有八个可爱的学生。她还说,那边没有电话。如果想她,就写信。
她开始羡慕刘莫,她给刘莫写信将她的生活,她的爱情,半个月后,收到了刘莫的回信。她说:小乔,我们都生活我现在生活的很好。我喜欢这里的高海拔,这里的阳光很清透,可以洞穿所有……
她们常常通信,讨论爱情、宿命、未知、所有。
九月下旬,小乔离开了A城,她在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独自坐在铁轨边,看着乌沉沉的天空和呼啸而来的火车发呆。她想起,扶着肖楠生的手在晚风中微笑地走,她记得他的手掌很厚实很温暖,就像一剂镇定剂,时刻给她以平静,可是……她不在想下去,用力地闭上眼,又睁开眼,将他的身影去眼前抹去。
她躺在草地上把身子尽量放平,伸展,她的身体里有太多的回忆和希望。那些都是莫飞留下的。身体记得他的激情,耳朵记得他的声音,手指记得他的温度,乃至每一寸肌肤毛孔都清晰地记得他。
她思念他。
记得他。
要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