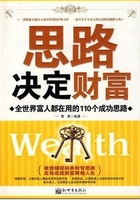而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综上所述,以中庸和谐为指归,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一体,这对于克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有着矫正的作用。但是,中国人的和谐观念确实也有追求大团圆与虚幻境界的缺弊。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满足)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更是尖锐地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传统的和谐观念,客观上对于国民性的怯懦与保守,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作用,这是不用讳言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大门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随着封建自然经济形态的更替,专制制度的解体,以及一浪高过一浪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包括“中和”在内的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也受到挑战和批判。五四之后,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地吸收西方文明过程中,痛苦地寻觅着、探索着,尽管它可能会遭受种种曲折,但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交流中,中华文明中和谐理想的重建却是势所必然的。中国当今的和谐之道,在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之中,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与现代性的建立,必然会获得重新建构,再续辉煌
这将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世纪工程。而国学的意义将通过此而得到彰显与激活。,在古代哲人看来,和谐之道归根结底是一种有关人生幸福的境界。天地自然的和谐之美,不仅体现了自身的秩序性和规律性,而且这种“和”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即自然向人生成的伦理意义,这是古人论“中和”的基本看法。《周易》中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赋予云行雨施、品物流行的天地以生养万物、惠泽人类的人情味道。春秋战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以人为本思想的活跃,主体论的美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孔孟、老庄那里都有不同的表现。《吕氏春秋》作为一本兼容并包的杂家著作,糅合儒道两家的主体论人学,在美学中倡论以心为本的思想。作者提出:
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人从生理常规来说,都是贪图美声、美味、美色等等的,但是人的生理欲求毕竟不等于人性的最高境界,所谓“心”也就是主体的思想与情感,决定了人对外界事物刺激的接受与感应的态度。当人心处于忧愁或烦闷时,外界的事物就不可能对人构成审美对象。要使审美的主客体和谐一致,必须使主体处于一种和谐快乐的地步,这样才能使主体得到快乐,同时也使审美对象的价值得以实现。
国学的和谐天地,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中,达到了极致。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但注重从不同中求匀称,更推崇从均衡中求变化,在审美境界上更是以天工自然、和谐平淡为圭臬。在中国古代,美的和谐往往用“文”来表示,它包含自然界、社会生活领域一切色彩绚丽、富有藻饰的事物,而“文”的组成则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意即文是由不同的线条交错而成的一种美的视觉形象。《易传·系辞》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而成天下之文。”《楚辞·橘颂》说:“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王充《论衡》也说:“学士文章,其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功。”到了六朝的刘勰著《文心雕龙·情采》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把杂多因素的组合视为和谐之美的根源:“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所谓“神理之数”,也就是自然之道。类似这样的观点在古希腊美学中也普遍存在,如赫拉克利特就指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和谐,艺术也是这样。如绘画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音乐混合着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不过西方人强调和谐中的对立,而中国古代文人更注重对立面和谐的转化,追求总体和谐之美。
与书画相通的诗文声律对偶之美,也体现着“和而不同”的创造原则。诗歌的声解不仅是有助于讽诵,更主要是便于吟咏情志,抒写性灵。西晋陆机《文赋》谈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锖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而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洪涩而不鲜”。陆机认为音声的迭变是逝止无常的,作文需掌握音韵的自然变化,作有机的组织和安排。而音律由不同的音节迭变构成,“若五色之相宣”。
在小说美学领域,古人也强调“和而不同”。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以来的章回小说,注重叙事性,情节以单线条为主,通过情节的铺叙展现人物的性格。由于小说故事情节的繁多,难免会出现“似曾相识”的现象。像《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主要叙述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及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单独成篇又互相连贯,其间免不了要产生“犯”即雷同的现象。为了求得故事的生动活泼、吸引读者,一方面,必须使情节故事互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如果在相同的故事中写出不同的人物性格,达到“和而不同”的效果,则更为高明。因为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金圣叹在批《水浒传》第十一回时提出“将欲避之,必先犯之”,也就是说,要避免雷同,就先要写相同的事件,在同中求异,从而既互相应和又各不相同,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读者的美感。如《水浒传》中,同是打虎,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不同;同是杀嫂,武松杀嫂与石秀杀嫂不同;同是劫法场,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不同;同是因宝刀生事,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不同,等等。都是相同的事件却写出不同的人物个性,衍变出不同的意味情思,都是“犯”而后避、“和而不同”。清代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也谈道:“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毛宗岗总结了《三国演义》叙事与塑造人物的技巧与方法,指出《三国演义》善于写出相同事件中的不同特点来。比如对火的描写,是写兵家常用的攻战方式,“吕布有濮阳之火,曹操有乌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陆逊有猇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盘蛇谷、上方谷之火”,但它的写法却情态各异,意趣盎然,在应和中又各具特色,没有雷同重复的感觉。所以《三国演义》一书,“譬如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
当然,中国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文艺家,在特定情境下,往往打破中和,以狂怪冲突之美获得独立价值。明代李贽就大声呼吁:“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说》)李贽认为真正的文章,决不拘守于“首尾相应,虚实相生”之类的法度,而是天工自然,臻于“化境”,一切形式上的“和”都融入自然之道,“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汤显祖也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合奇序》)清代石涛更是提出:“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画语录》)他们都反对因袭前人之法而不知有我。总之,中国古代有成就的文艺家认为,达到艺术创作的和谐需要一定的法度,但是这种法度应以自然为准则,并发挥艺术家的独特个性,这样才能创造出气韵天成、和谐完美的作品来。
二、对和谐之道的重新反思
当然,古代社会已经过去,毕竟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之中,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对于传统的和谐之道当然必须进行全面的反思。如果没有认真的反思,重建和谐文化便无从谈起。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走着不同的道路。欧洲文明起源于古希腊雅典城邦之中。古希腊的雅典从地理环境上来说,与大陆型的农业生产环境不同。这个半岛周围有良好的港湾,可以通向爱琴海的群岛,甚至直达小亚细亚。从公元前12世纪到8世纪,古希腊的雅典一直处于贵族统治下,其后经过各部落的不断联系,尤其是一系列政治改革后,逐渐确立了按阶级和财产关系划分人口的社会形态,开始取代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而此时的中国周朝,正演出一幕制礼作乐,按血缘宗法关系封邦建国的活剧。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氏族统治的削弱,带来的是古希腊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移民的兴起,其范围已波及周围的邻国。在奴隶制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雅典的公民民主制度也发展成熟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法律的契约关系,它无须温情脉脉的亲族关系来“和同”,人与自然也无须通过群体来契合天道,实现天人合一。《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在与大海等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中,历尽艰辛,回到家乡,依靠的是个体的力量;普罗米修斯敢于触犯天条,表现了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
古希腊的悲剧精神,是在个体自由发展,同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尖锐对立中展开的。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摆脱了氏族社会血缘和等级制度的束缚,固然取得了个体自由发展的机缘,但同时也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失去了群体的依托,受到无数不可捉摸的偶然性的支配,由此滋生了头脑中的命运观念。古希腊著名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有一段歌词道出了人们对无情世界的困惑不解:“朋友呵,看天意是多么无情!哪有天恩扶助蜉蝣般的世人?君不见孱弱无助的人类,虚度着如梦的浮生,因为不见光明而伤悲?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论古希腊悲剧精神时说:“从整个希腊悲剧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它们反映了一种相当阴郁的人生观。生来孱弱而无知的人类注定了要永远进行战斗。而战斗中的对手不仅有严酷的众神,而且有无情而变化莫测的命运。他的头上随时有无可抗拒的力量在威胁着他的生存,像悬岩巨石,随时可能倒塌下来把他压为齑粉。他既没有力量抗拒这种状态,也没有智慧理解它。他的头脑中无疑常常会思索恶的根源和正义的观念等等,但是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个体孤独感与命运感,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不和,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底蕴。中世纪希伯来文明的输入,也没有消融与取代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悲剧精神,而是使这种悲剧意识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将灵与肉、个体与宇宙的裂变变得更为严重,虽然在虚幻的宗教天国中,一切变得至美至善,因而中世纪美学以和谐完善为美。但宗教以人生苦难换取天堂的慰藉,本身就是一种悲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归根结底,它是极度的人世不和谐与悲剧所造成的精神异化现象,这正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之于当时的人生苦难一样。
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悲剧人生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那里得到了充分表现。随着启蒙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逝去,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代表的悲剧人生观弥漫西方世界。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看来,古希腊是一个阳光灿烂、海风拂煦的和谐社会,法国艺术史论家泰纳的《艺术哲学》就说:“希腊是一个美丽的乡土,使居民的心情愉快,以人生为节日。”他在书中所描绘的古希腊时期的文艺状况与人生情景经过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优美畅达的文笔的译述,曾经为中国许多读者为之心驰神往。但尼采却独具只眼地看到了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其日神说与酒神说对现代西方的美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西方人始终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存在什么天人合一、人人和一的可能性,贯穿于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是冲突不和的悲剧人生观。西方文化过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冲突,造成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实与这种文化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