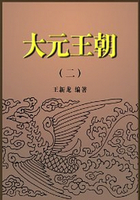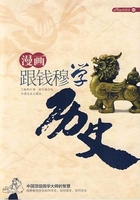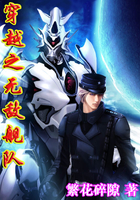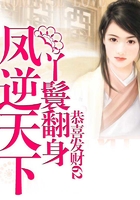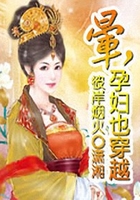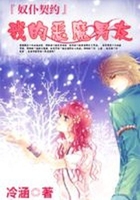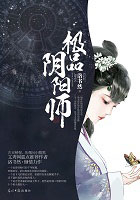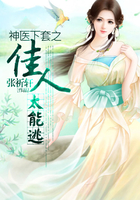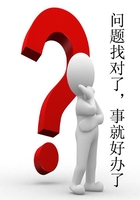王国斌和彭慕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比弗兰克更为广泛地考察了各种要素,他们在清代发现,中国的某些核心区域,与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可供比较的地区一起,一直是最成功地将人类活动前工业方式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地区。考虑到中国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具有大得多的规模,人们可以推断说,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成功的政权。但无论是在王国斌还是在彭慕兰的概念中,清的秩序都不是有重大意义的新秩序。特别是王国斌强调了中国周而复始的“农业国家的再生产”,及其在回应经济扩展与经济收缩周期时的变迁,在长时段中,这些周期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经济,这个类型在经历了公元1100年的唐宋变革期之后,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规律性。他承认,与明相比,清具有更大的军事扩张性(1997,95~96页),而彭慕兰则沿着他的分析思路,引证了某些影响中国表现的清的政策和取向,比如政府更大规模地卷入和拓展到中亚、而非海上贸易的范围(2000,173、203页)。但是,和弗兰克一样(而与本书的几个作者形成对比),在王国斌和彭慕兰的大历史研究中,无论明还是清,的确,无论17世纪是否发生过王朝更迭,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从16—19世纪的整个时代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时代,甚至在更狭小的意义上,中国还在旧大陆的“原发型工业化的死胡同”中保持着生存能力,而欧洲,这个“幸运的畸形儿”,偶然发展起了一些先决条件,杀出一条血路(彭慕兰,2000,207页)。尽管王国斌和彭慕兰对于世界体系图景都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的作品都强化了弗兰克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长期的、正常的、相对的实力的观点,而这一实力在19世纪为大西洋带上非正常的支流所干扰。
彭慕兰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查尔斯·蒂利所倡导的全面比较(encompassingcomparison)的工作,此项工作从一个大结构或大过程起步,然后在这个大结构或大过程中挑选一些区位,再去解释那些区位的异同,作为它们与整体之关系的结果(蒂利,1984,125页)。但依我之见,由于无法对全面的结构或过程进行界定,他和王国斌所进行的工程就更为接近蒂利的发现多样性的比较,这“有助于理解那些从未以同样的形式重现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还表达了关于因果关系的共同原则”(146页)。蒂利的另一个范畴,工业化过程比较,有时、特别是在这一经历被看做与更大的问题相关时,“对于我们理解一个特定历史经历的单一性来说非常需要”(145页),穆素洁(SuchetaMazumdar)的《糖与中国社会》(1998)一书可以作为这一范畴的实例,并由此浮现出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在数量和价值上仅次于茶叶和丝绸的最重要的中国出口产品是糖,由于集中注意糖的生产、消费和国内外贸易,穆素洁探讨了中英之间在糖的国内消费方面的巨大分异,这一分异也出现在华南各地区与沦为帝国主义强权殖民地的世界其他糖产地之间的甘蔗栽培与加工上。她将比较的参数公平地设置在农业财产关系和社会阶级中,发现最有效的比较参数在明清变迁的过程中必然变化。然后就是,作为广泛扩展的社会政治断裂的一个后果,大多数农业“直接生产者”设法成为“拥有永佃权的小农,以便再分和继承他们的土地”,尽管在同时,地主—商人精英强化着他们的凝聚力和权力。按照穆素洁的说法,支配着这一小农经济堡垒的精英,其最为主要的利益并非是为市场所驱动的,所以在整个19世纪末,中国城市人口比例的缩小和产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微弱,这个堡垒的因素是基本的(1998,52、387~388页)。为中华帝国的最后550年安排的因果连续性,把明的开端(1368)与20世纪初连接起来,模糊了清代、而且是在中华帝国间第一次发生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就是,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获得了完整的财产权……大土地和直接生产者的不断农奴化过程在晚明时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清代,它在全国范围内急剧缩减,在华南则彻底消除。总而言之,我以为,这些新的农民权利在农业的层面上逐渐构成了资金与生产之间的主要障碍,而且就长远来看,为清代的经济发展设下了限制。(穆素洁,405~406页,1998,引证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德怀特·珀金斯著《中国的农业发展》,作为“表明了1368年与20世纪之间连续无间”的作品。)
因此,中国也具有偶然性。尽管偶然性把欧洲放在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个新的轨道上,这个轨道可能或者不可能通往工业化,但从明到清统治的变化也偶然地导致了一种社会—财产关系的体系,这个体系把中国放在了另一个命运攸关的轨道上。这样,穆素洁的著作完成了一件由彭慕兰提倡的(2000,8页)、关于欧亚大陆两端之间殊途异轨的双折画。清初所呈现出来的重要性并不是作为一个这样的时代,即中国正肩负着置办家庭所需的压力,而别人则偶然地重新创造了世界,而是作为这样一个时代,即中国走上了一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崭新的却前途未卜的道路,别人则走上了另一条这样的道路。如果那另一条道路不曾迂回而至现代性的话,这一条也不会引人注目。鉴于不规则的周期是王国斌总体概念的组成部分,而穆素洁又否认生产结构中的变化是线性的,如果我们比较他们和彭慕兰的作品对于弗兰克和盖尔斯的理论中500年周期之压倒性决定论的时限性抨击,“时间之箭”成为比“时间之环”更清晰的焦点。(关于这些隐喻和周期性概念如何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朝向宇宙运动、离开特殊的、独特的、连续的事件和寻常的历史事物的距离,见高尔德,特别是10~16页,1987。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学者把中国看做可以概括为历史停滞的概念,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学家的一种观念,见布鲁,7~12页,2000。)这个时间之箭直指19世纪,其他一切的时间节点被排列起来加以解释:在一个缓慢的、衰落的、或最好地说来是持续不断的“东方”与一个加速的、上升的、其原动力是扩展性的“西方”之间的差别。(关于战后西方研究中国的学术的说明,包括现代化理论,把非西化中国的观念永久化为步履蹒跚的、保守的和被官僚制传统所拖累的,见布鲁,22~26页,2000。)发现是新的,但困扰是旧的,而且在整个20世纪都给清画上了一张两面神的脸孔。正如何炳棣在数十年前写到的:清代的一般意义在于,从年代上说,它崩溃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无论新中国在未来的变化有多大,清作为中国古代统治的最后阶段,还是留下了重要的遗产。
清代将继续作为一个基准面,由此既可研究更早的时期,也可分析当今中国之遗产(1967,189页)。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分依赖于两个同源共进(bivalent)的时空之箭,后者一方面从晚清向前指向现代性,而且通过推论指向西方,另一方面则从清的大部分时间向后指着被汉文明所支配的次大陆的远古历史,是个非限定性的“pre”(“前”),就像在pre-这个同源共进的特点构成了困惑混乱的基础,在处理揭示了重大变化并因此不支持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材料的过程中,清史学者感受到了这种困惑和混乱,但也并不如此看待现代。同时,它也展示了构建任何一种关于双向时间之箭的叙事的困难。结果,把19世纪的中国既当做传统的也当做现代的两难困境,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至少对于汉学家来说,这个术语明白无误地指称20世纪以前的中国,却淡化了传统/现代的反差,这就是“帝国晚期”。孔飞力在一部关于清代的书名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796—1864》,声称他的选择是受到下列问题的启示,即19世纪的中国是否只是处于又一次王朝衰落中,或是否在西方的外力下遭遇了它的破坏者(1970,1~3页)。显然,孔飞力希望他意欲提出的问题不与一个特定的王朝——清——相关,也没有关于衰落这个总是与历代王朝牵连的传统观念,他选择一个术语,是以最宽泛的视野,把19世纪的中国置于整个中华文明历史晚期的点上,这部历史始自公元前3世纪最早的帝国,由皇帝和官僚统治。但在一个两千年的时间期里,“晚期”究竟有多久?在孔飞力的心里可能是指清代的后半期,但在几年内,魏斐德在其会议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的导论中,指出了这个范围,即学者“考察了跨越中国历史最后400年、一直延伸到民国时期的那些过程”;“社会史学者开始意识到,从16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整个时期,构成了一个一贯的整体”(魏斐德与格兰特主编,1975,2页)。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日本汉学对美国学者产生影响过程中的一个二三十年的时间差(下文详论)。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历史学家很快就稳步发展起了一套对16世纪中叶直至19世纪中叶的理解,即将其理解为一个衰落期,并非一个停滞期,而是一个“变迁”期。(森正夫,4~5页,1997。关于日本学者对前现代中国的理解在20世纪发展状况的全面说明,见万志英,2003。)无论如何,在美国汉学中,“帝国晚期”变得流行起来,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对于非汉学家来说,则是听起来怪怪的)方式,来指代晚明到清的时期,大略从6世纪下半叶到整个19世纪。标志性的年代是1985年,其时,《清史问题》杂志的主编把刊名改为《中华帝国晚期研究》,他们希望“扩大读者群,包括一些非清史研究的专家,并表明一种更有机的分期,而不是一个王朝的框架可以轻易涵盖的”(作为《中华帝国晚期研究》第6卷第1期前言的“新主编的信”,1985(6)。)。
如此,现在是什么导致了对帝国晚期表示不满的嘀嘀咕咕呢?它只是成了语言学转向的术语学最新成果吗?也许是吧,但争论是无法挥之即去的。正如乔迅在本书中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帝国晚期表明了一种文化迟滞。因此它便支持了一种旧的观念,即中国,特别是清代,在历史的重压下步履蹒跚,当然是靠“现代的变迁”才把它解放出来。这一线性时间的想象似乎是缓慢的下落、到清末达到谷底的状态,就像热气球在它强行着陆并重新设计之后才能重新注入动力的轨迹一样。较少负面但也许会诱人上当的是盛期(culmination)这个词的意思,这是由我们关于清是帝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认识所导致的。其所深藏的隐喻是一支箭,它在一个漫长的、的确是几千年的飞行轨迹中呈上升状态,然后在19世纪陡然下落。我们对此下落的预料不可避免地是会以对整个飞行的观察为条件的。但是关于清的“晚”的观念却几乎不能只归咎于“帝国晚期”这个术语,因为它们在不用这个术语的中国史话语中甚至是更为清晰可辨的。实际上,清的迟滞的意思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特别是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日本史学中是最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清总是被概括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个“完整的封建社会”,或者是“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样的表述是非常普遍的。关于中国一个著名史学家体现在一个基本文本中的最近的例子,见郑天挺,1页,1999。)——当然,延续了两千、也许甚至是三千年的中国“封建”阶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被资本主义阶段所取代。从特别强调文明的退化、气息奄奄、衰老,通过描述旧体系内尚存的最后的可能性与新因素的内发萌芽之间的辩证法,直到对一个使被人普遍接受的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加以臆想的赞美,所有这些都把清描绘为天鹅之死。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意识到,清前期的中国还可以相当不错地与西方抗衡,但到王朝之末,这一切就灾难性地改变了。以下文字集中代表了目前中国占主要地位的观点:西方的发展犹如脱缰之马,腾跃飞驰,一日千里,迅速地脱离传统社会,相形之下,中国如龙钟老人,步履蹒跚,缓慢迟滞。
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而中国的18世纪,也存在着近代因素,但幼嫩稚弱,阻碍重重,不能够加快积累与汇聚,还远远不能够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的桎梏。(译自戴逸,18~19页,1999。也许没有比金观涛和刘青峰在1984年的著作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史学的困惑,前者把宋以后的中国解释为“僵化”、“停滞”、“超稳定”和“老化”。)而在日本史学界,从晚明直到清中叶被称为“近世”,即比“近代”多少早一些,而“近代”开始于晚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外,把清代中国定性为衰老是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原因的,即把中国从在“旧东方”(theOrient)发展中长期领跑角色的衰落,看成日本作为“新东方”(theEast)领袖崛起的结果。在一本关于明清史的书中,作者表明了主要是战前日本对于中国历史学术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持续影响,该书针对的是一般读者,书名为《传统中国的完成》,其中用下面的话来介绍该书:由现代回顾明、清两朝,其在中国史上所处的地位,无疑是进入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之前的最后阶段,这两朝可以说是由中国的理想和传统构成的最后的帝国。到清末,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拖入近代国际社会,但不能说被迫走上资本主义轨道的是一个还并不完全成熟的中国,中国自己很久以前就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实际上,说它过于成熟也不为过(岩见宏和谷口规矩雄,1977,6页)。于是,晚明就被描述为一个“中国社会臻于极盛”的时代,清前期则被描绘为一个什么时代呢?那就是,特别是在清的异族统治下,王朝更迭带来了一个混合物,它既是一时的新鲜活力,又是限制发展的新来源。无论如何,该书告诉我们,由于已知晚明的先进成果,我们几乎不应期望清代是一个重要的全面发展的时代(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