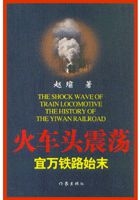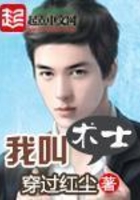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杜牧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南齐建武年间,谢朓任宣城太守,他用绮丽而柔媚的笔调涂抹了宣州的山水。从此,宣州就成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杜牧称之为“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题宣州开元寺》)。在唐人看来,宣州就是南朝,是江南。
晋朝东渡之初,中原仕宦有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言语》)的感叹,既表达了强烈的异乡感受,又为人们从山水风景中认同江南指示了路径。而真正揭示出江南山水的独特魅力,就要等到谢灵运、谢朓等因政治失意,而踏入江南更深处之时。江南以自己的美丽和温柔,收容了士人骚动而忧伤的心,维持了无根士人最后的矜持和优雅。南朝梁时,丘迟随太尉临川王北伐,作书劝北魏大将陈伯之来降,其中有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陈伯之读罢,遂率八千人归降。此时,人们已经沉醉在江南,而淡忘了自己真正的故乡。
这是个浪漫的奇迹。正是江南的山水,使得流放成为一种流连,逃亡成为一种徜徉。江南,是诗人的他乡,也是一个精神的故乡,它从此让士人们魂牵梦绕。唐人孟浩然说:“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送袁太祝尉豫章》)刘禹锡说:“斜日渐移影,落英纷委尘。一吟相思曲,惆怅江南春。”(《酬令狐相公亲仁郭家花下即事见寄》)白居易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蒙眬的春雨、缥缈的烟树、清澈的倒影、婉约的歌声,还有总也摆不脱的痴迷和怅惘,它们还是谢灵运和谢朓们的江南吗?
唐朝人有着更为个性化的精神世界,因此,江南的意义也是多样的。“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是孟浩然的愤懑,“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山中问答》)是李白的飘逸,而“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菩萨蛮》)则是韦庄的温情……那么,杜牧的江南又有着怎样的风景呢?在这首诗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那秋风衰草中的“六朝文物”了。注者常引王通的话解释“文物”云:“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中说·述史篇》)他们把体认南朝的理由归结于礼乐文化的传承,这显然是儒家华夷观念作怪,实际上,北方儒学之盛过于南朝。南朝于礼乐传统无所成就,却在浪漫而有个性的人格精神方面独有建树,深受后人推崇。杜牧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二首》)这其中就包括谢灵运、谢朓们在江南山水中所呈现出的优美、自由、深情,甚至是放纵的性情。所谓“旷达”和“风流”,指的就是那份无奈而又无根的矜持和优雅,是苦难世界中高贵而又纯粹的人格气质。唐人往往将这份苦难中的从容、绝望中的洒脱,与兴盛于六朝时的佛教相提并论,用那山光水影中寂立的塔寺和悠然的梵音,悄然替代了“衣冠礼乐”,所以,所谓“六朝文物”又指烟雨之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江南春绝句》)。显然,“六朝文物草连空”正表现了诗人对那种孤独缥缈的精神气质的怀念,而怀念,使得江南而再度成为诗人孜孜以求的他乡。
但是,杜牧还能像南朝文人一样,再次体验江南的优雅和柔情吗?连天的草、淡淡的云、潺潺的水,还有寺庙、飞鸟、阴雨、秋风、笛声和参差的烟树,这些都是典型的江南景色。但在这首诗中,这些景色又都显得遥远而且蒙眬:寺庙是前朝故物自不用说,那些朝朝暮暮随意飘过的云,从古老的楼台上拂过的风,你又能分得清它们的朝代吗?在这些景物中,诗人被一种顽固的历史意识所纠缠着,他所看到的只是风雨侵蚀中的六朝,因此,这个江南就显得不那么真实。杜牧似乎只能徘徊在这片景致之外,徒劳地遥想着六朝文人的优美和伤感,并由此而看到了自己和历史之间无可跨越的距离。我们能从诗中嗅出被历史抛弃的感伤和追之莫及的惆怅。
中国古代山水诗中乐观精神很少,它的感情倾向甚至比田园诗更缠绵,就是因为山水在诗人眼里并不仅仅是实在的景色,在它的花开叶落、春风秋雨中,总是暗示着某种神秘的命定性,暗示着现实那无可超越的窘境。而在杜牧的这首诗里,我们又看到了历史的无从超越性。“天澹云闲今古同”这样的诗句,既表达了追随历史的渴望,也散发出历史映照下现实个体的哀伤。那曾经存在着的依然存在,云、山寺、江南,它们使诗人怀想,但是,也正是它们指示了历史的存在,并因此区分出古和今,使得现实变成一种有差距的存在,一种令人忧伤的非存在。
历史延续了江南,历史也改变了江南。当王羲之在会稽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一觞一咏”时,他已经感受到了“俯仰之间,已为成迹”的悲伤(《兰亭集序》)。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宋书·谢灵运列传》),风华绝世,而江南却无力挽留他的生命。谢朓称宣城为“山水都”,他的国度被如此精心地封闭着:“凌厓必千仞,寻溪将万转,坚崿既崚嶒,回流复宛澶。”(《游山》)但无论怎样封闭着的山水都无力阻隔他内心的“怀禄情”,眼看着他断送了自己三十五岁的人生。美丽的山水成就了南朝人的人格,但却难以消释人生的悲凉,也难以承载生命的沉重。一味地沉湎、放纵,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沉沦和堕落,如石崇在金谷涧中筑庐纵饮(《水经注》卷16)等。
这一切,都在流逝的时光中变得清晰起来,就在中晚唐人的蓦然回首中,山水中的优雅,就如同华丽的衣冠大族,其实也只如舞动在秋风中的枯叶,随着风起云散,在历史中陨落。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这种沧桑的悲凉写照。面对着美丽的江南,谢灵运和谢朓们只有深情的沉醉,但历史却在他们身后留下了死亡、堕落和江山沦落的痕迹。江南,正因为背负了这种沉重的历史,而难以承载杜牧的希望。“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江山不改,一切如旧,但那些曾经的梦想和喧哗,那些传奇而令人羡慕的故事,都被年复一年的细雨所冲刷,都被淹没在潺潺不断的流水里,只留下呜咽的声音,伴随着古寺里的晨钟暮鼓,不断在山涧回响。古人的歌大多数是悲哀的,所谓长歌当哭、且歌且哭吧。南朝文人发现了江南,并且托身于它的清纯秀丽,而同时也用自己的哀伤浸染了江南,一代又一代的赞美,一代又一代的浸染,留给杜牧的就只能是走不出的潇潇秋雨,拂不去的瑟瑟晚风。
虽然如此,杜牧还是深爱着江南。不久之前,杜牧因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而侥幸逃过甘露之乱;又因为弟弟眼疾求医而超假丢官,幸得他人援引,这才带着身患重病的弟弟往宣州任团练判官。因此,无论家国前程,还是倜傥畴昔,都一时变得渺茫起来。杜牧喜欢春天的江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江南春绝句》)但晚秋风雨中的江南,更令他心动:雨幕中静谧着的人家,晚风里飘扬着的笛声,还有迷离在烟雨中的古刹老树,即使不能托身,但至少还残留着一个关于他乡的梦想。立在这同一个江南,怀乡之情油然而生:从闲云和飞鸟的身影里,从依稀的歌声、哭声里,从迷失在五湖深处的古老的传说里,我们能听到那些卓越的精神个体的深情召唤,感受到曾经有过的自由和超逸,还能感受到历史自身的悲凉。
这是一个只能凭吊的江南,不能久留,但却可以触摸和重温那依稀的梦想,可以深情地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