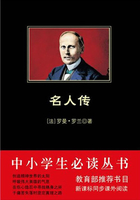范元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范元实(原作宝,当误)《诗眼》曰:必言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为传诵其诗也。”《登岳阳楼》(卷三五):“范元实《诗眼》云:《望岳》诗云:‘齐鲁青未了。’《洞庭》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语既高妙有力,而言东岳与洞庭之大无过于此。后来文士道之,终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孟浩然《岳阳楼》诗诗(衍一诗字)‘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楼’,然气蒸者云梦泽而已。杜云‘吴楚东南坼’,则《子虚赋》所谓‘吞云梦者八九而不芥蒂也’。且学者指为佳句者,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已,殊不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两句尤是含蓄有意之对。邵溥泽民侍郎云:晁以道以此为俯仰格,次公采其说,盖若桔槔之势相引也。其义以既在洞庭之际,亲朋相去之远,虽无一字见及,然于老病中,尚赖有孤舟可以浮泛,而生涯自知也。”
胡仔:《羌村三首》(卷三):“《渔隐丛话》载:《冷斋夜话》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相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当作‘更’,若使侧声字读,则失其意甚矣。”《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苕溪渔隐曰:待(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用时变如兵之出体(体宇当衍)奇,变化无穷。杜公此篇,即七言律诗之变体也。韦苏州诗:‘南望青山满禁围,晓陪鸳鸯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如《上严公寄题锦江亭》诗‘漫向江头把钓竿’,亦是变体。唐人如此甚多,学者不可不知。”
王彦辅:郭知达集注本:《义鹘》(卷三)题下注:“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黄鹤补注本:《义鹘》题下注:“彦辅曰: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又,郭知达集注本《溪》(卷二三)题下注:“《异物志》:溪,水鸟,毛有五色,食短菰,其在溪中无毒气。”黄鹤补注本:“补注:彦辅曰:《临海异物志》:溪,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当作孤,即菰),其在溪中无毒气。”将两种本子中两篇对应的诗注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是相同的。郭知达集注本两篇所集的注皆为王彦辅所注,不过未载王彦辅之名。而《溪》将《临海异物志》简称为《异物志》。
鲁訔:郭知达集注本:《游龙门奉先寺》(卷一)题下注:“龙门在西京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耳。”黄鹤补注本:《游龙门奉先寺》题下注:“鲁訔曰:龙门在京西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将两种本子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大致一样,可知郭知达集注本所集为鲁訔注,只是未标其名。
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可以看出,宋人所谓注家,就是其人有著述材料采入集注中,并非其人一定有杜诗注释之作。故有宋一代注杜者数十人,而号千家注杜。用此注家标准来衡量,我们完全可以说,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实际有注家20人左右。从现存材料看,王彦辅、王深父、吕本中、鲁訔四家皆有杜诗注释之作。而苏轼、胡仔、范元实皆有不少杜诗之论,蔡元度留下的材料少,八人皆足称杜诗注家。
事实说明,九家注之外,确实尚有至少八位注家的注存在。由于《杜工部诗集注》很多地方未标原注者姓名,准确统计具体的注家非常难,估计应在20家以上。当然,郭知达序中所说的九家仍是最主要的注家。
标名为“东坡”的伪东坡注,集中也有多条,今亦举两条:
《后出塞》其五(卷五):“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八阵图》(卷三一):“东坡先生云:仆尝梦见人云是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吞吴之意,以此为恨耳。此理甚长。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犹(衍一犹字)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其书生习气也。”
我们认定这两条为伪东坡注,根据有三。(一)两条注皆不见于苏轼全集中。(二)所注见识低下,立意与杜诗的本旨不合。杜甫《后出塞》并非如注所言,是咏安禄山的叛将脱身归国之事。而苏轼并不一定认为“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呑吴之意”。注所表现的是庸人的眼光和胸次,并非苏轼的见解。(三)文辞拙劣。“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谁“可恨”?为什么要出其将“姓名”?完全莫名其妙。“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书生习气耳。”有点令人不知所云。而杜甫死距苏轼在世,仅三百年多一点,谈不上四百年,有明显的破绽。全文皆小说家口吻,故可肯定为伪东坡注。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实际注家与郭知达所说的注家不符的矛盾?为什么序说删削尽伪注而实际未删尽呢?这自然引起我们对《杜工部诗集注》成书过程的探索。
《杜工部诗集注》署名为郭知达集注,其实他只是策划与组织者,而并非具体的集注者。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从序可以看出:(一)郭知达是集注的组织者与主编,没有具体参加集注;(二)集注是几个人共同完成的,成员殆即郭达达任职之郡的士人(包括郡的官吏)。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过程。它不是像一般的集注那样,先搜集各注家的注释材料,然后汇集材料,剪裁、组织加工而形成集注,而极有可能是利用含有九家注的多家集注本(近似黄希、黄鹤用以补注的《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删削、增补而成。说得详细一点,就是选一个含有九家注(含有其中一部分)的多家集注本作底本,把九家注保留下来,而将其余的删去。九位注家的注不全,再搜集材料,重新增删,组织安排,撰成集注。
知道了《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情况,也就找到了九家注为什么会实际是20家左右的注的答案。因为底本原本是多家注,在删削非九家注时,难免删削未尽。更有甚者,集注者是多人,各有所好,有意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加之有的注没有标明注家,无法判别是否为九家注,也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至于伪东坡注存留,主要是伪东坡注很容易迷惑人,不仔细辨别,往往误以为真。总之,九家注之外的十家左右的注和伪东坡注保留在《杜工部诗集注》中,是集注者对有多家集注的底本有意或无意删削未尽造成的。如果《杜工部诗集注》是按体例自行逐一搜集九家注的材料而整理、剪裁、撰集成书,是不会含有20家左右注和伪东坡《杜诗故事》的。从规范的角度说,利用多家集注而又删削未尽,破坏了《杜工部诗集注》自定的九家注体例,但从质量上看,保留非九家注,弥补了九家注的不足,更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注释成果,提高了《杜工部诗集注》的质量。
三
作为一个集注本,《杜工部诗集注》最大的学术特色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集注上。可以说,就注释的完全与准确而言,《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最好的。
首先,集注者富有卓见,精选注家。郭知达时代,杜诗注家已非常多。郭知达精选其中有创见的、注释较好的九家,既能集中宋代研究(注)杜甫的主要优秀成果,又防止集入平庸粗滥的注。这是保证集注质量高的根本。
其次,特重赵次公注。赵次公是比郭知达略早的注家,他的注代表了郭知达那个时期新近的杜诗注释水平。宋人很推崇赵次公注。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说:“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氏》、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郭知达本特重赵次公注,汇集了杜诗注释的新成果,富有时代气息。郭知达本所集赵次公注的分量,估计约占整个集注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比例甚大。《登岳阳楼》除题下注集《诗眼》外,其余所注皆集赵次公注。《送李煜卿》一首,所集更全是赵次公注,没有一条他人所注。大量集注水平高的赵次公注,可以将集注的质量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第三,注释比较准确,简明扼要。集注水平的高低与集注者的学识成正比。《杜工部诗集注》充分以众注(主要是九家注)为材料,根据注释的需要,精心裁剪,组织成精当的注本,真正集众家注之长,而避单家注之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将郭知达集注本与黄鹤本的《哀王孙》题下注加以比较。郭知达本注:“天宝十五载,明皇西狩,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诗此时作。《史记》:漂母饭韩信,信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王孙,如言公子。”黄鹤本注:“彦辅曰:韩信至城下钓,漂母哀之,饭信,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无补注。郭知达本注了三方面的内容:写作的时代背景;“哀王孙”的语典;王孙的语意。而黄鹤本只注了“哀王孙”的语典。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黄鹤本失之太简略,没有达到当注则注的要求。郭知达本则是该注的都注了,注得准确简洁。当然,这是黄鹤本与郭知达本注释局部比较,并非郭知达本的所有集注都优于黄鹤本。
第四,有集注者之注,纠正纰缪,救补阙失。集注也需要创造性的劳动,这集中体现在集注者的自注上。郭知达集注本的自注并不太多,但集注者之注往往高于所集注的注。从体例看,集注者自己的注一般用“新添”二字标出。《江畔寻花绝句》(卷二三)“诗酒尚堪驱使在”,没有现成的注可集,集注者新添:“王羲之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以王羲之之语注“驱使”二句的语典,甚确,对深入理解原诗有益。《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牙堂赀》(卷二一)“昔来寻一老,破愁是今朝”下集注:“杜补遗:汉初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曜即应劭八代祖也。又管宁书曰: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赵云:一老,公自谓也。祖出《右》(应为左,指《左传》):鲁哀公诛,孔子曰:天下不愸,遗一老。松(应为“杜”)所引是,又谓无祖也。”集注者认为杜田和赵次公次所注虽是,但并非“一老”的最早出处,故自己“新添”:“以今考之,《诗·十月之交》曰:‘不愸遗一老,俾守我王。’赵岂不见乎?”集注者所注《诗·十月之交》确实是“一老”的最早出处,比杜田、赵次公高明。这些集注者之注,提升了集注的质量,为集注生色不少。它表明,集注者不仅眼界很高,擅长集他人之注,而且学识渊博,自己注释也堪称行家里手。
当然,《杜工部诗集注》的注释也有缺陷。突出的有两点:(一)很大一部分集注没有标明原注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使用的集注的底本原就没有全标集注者。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对集注来说都是大缺陷。它不利于读者了解原注的注者,不利于阅读注文,降低了《杜工部诗集注》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二)有的注文不正确,有的集注抉择注文不精,有的集注注文失之冗长。如《不见》“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下集:“杜《补》:范传正李白新新(衍一新字)暮(墓)碑云:白厥先避仇,后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读诗(书)于大匡山,有读诗(书)台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号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所谓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庐山。”注匡山甚确,而前尚集有:“白始隐岷山,后客任居徂徕山山(衍一山字),而不载匡山。”这条注释水平低下,本不该取,集于此,画蛇添足,降低了集注的水平。《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卷一三)题下集注:“赵云:此篇极难解,姑以意逆之。似是公泊船处,一美士文采风流,有司马相如挑卓文君之作,公见其人,又见有搜求其人而去者,佳士岂薛文子弟亲戚乎?故及丈人安坐之语,且言国家轻刑以宽之,又言此士俊乂以勉之。尝观《太平广记》载严武一事云:武少时任侠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艳,武窥见乃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觉,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亦以上闻,有诏遣万年县官捕捉。乘递驿行数日随路,已得其迹。武自巩县方雇船下,闻制使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使至,搜武之船,无踪乃已。公诗意有类于此,当俟博闻。”所集赵注既言此篇难注,又引小说家言,不足征信,不仅于理解该篇主旨无补,反而添乱,治丝益棼。集注理应对赵注进行删削。不过这样的例证并不太多,可谓瑕不掩瑜。
除集注方面的价值外,《杜工部诗集注》在版本的选择及校刊方面也多有可取之处。郭知达非常重视版本,集注序说要辑“善本”,故集注本基本符合善本的条件。《杜工部诗集注》为三十六卷,底本与黄鹤补注本属同一系统。作为版本,郭知达本优点有四:(一)搜罗杜诗比较完备。杜甫集子经五代而散佚,至宋代编杜甫诗集,有一个逐渐辑佚的过程。郭知达本反映了北宋至南宋初杜诗辑佚的新成果。凡当时新搜集的杜诗,都用“新添”二字标注题下(所谓“新添”,当不是郭知达新添,而是底本的“新添”)。如《腊日》(卷一九)、《投简梓州幕府简韦十郎官》(《卷二四》)皆标“新添”。(二)杜诗文字比较好,错误比较少。(三)辑有杜甫友人的唱和诗。其中有的也是“新添”辑佚的。(四)杜诗中有杜甫自己的注文,有的用“公自注”标明。杜甫的自注和杜甫友人的唱和诗是重要的资料,对研究杜甫和杜诗皆有用处。与宋代其他版本相比,郭知达本也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值得重视。
在校刊方面,郭知达本也做得比较好。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精其仇校,正其讹舛”,大致符合实际。在校勘中,尽量罗列异文。如《龙门阁》:“高”校:“一作白。”“(危途)中萦盘”校:“一云萦盘道。”“吹过雨”校:“一云过飞雨。”在集注时,也集录注中有关校勘之语。《春夜》(卷二二)“风色萧萧暮”下集:“赵云: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则错字眼矣。又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却无义矣。师民瞻本作‘风色萧萧暮’,是。”其校勘材料丰富,有的还有断语,便于读者研读。
总的说来,《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一个质量很高的注本。在南宋时代即很受重视。淳熙八年,该本刻印后,宝庆元年曾噩又刻于广州漕司。陈振孙对其非常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该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其文云:“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九家之注,颇为简要。”“知其别裁有法矣。”隐然以其为宋代注杜善本许之,评价高而允当。郭知达集注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各有千秋,而总的价值大致相当。黄希黄鹤补注本有诗系年,为郭知达本所不及,而就注释的精要而论,郭知达集注本似乎要略胜黄希、黄鹤补注本一筹。
一二黄希、黄鹤
一
黄希,字梦得,宜黄(今江西宜黄)人。(《万姓统谱》谓临川人,亦谓其为宜黄人。因为临川即古抚州,宜黄隶抚州,即临川。)孝宗乾道二年进士(《万姓统谱》谓乾道三年进士)。官终永兴令。事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
黄鹤为黄希之子,字叔似,著《北窗寓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