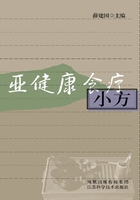出身小地主家庭的扬雄,人到中年才入仕途。官卑职小,薪俸自然也就很少;虽然晚年被封了个“大夫”,但却是个闲差事,仍然无职无权,莫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捞钱,即使他真想捞钱,也没有人会给他“进贡”;加上他嗜酒如命,哪怕是花生胡豆做下酒菜,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再加上他父母、妻儿先后去世,古代安葬死人是大事,花费自然也不少。扬雄长期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一辈子都过着紧紧巴巴的穷日子。他在《逐贫赋》中所描述的“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别人穿的都是绫罗绸缎,而我穿的全是麻布衣衫;别人吃的都是珍馐美味,而我吃的尽是野菜稀饭),仿佛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难怪他的“忘年交”朋友桓谭引用别人的话说:“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意思是说:道德文章如同孔子一样的扬子云,竟然贫穷到如此地步啊!)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从来不在意自己富贵贫贱的穷光蛋,却一直关注着天下百姓的疾苦,始终坚持用对待百姓态度的好坏来衡量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治人者”。
扬雄在《法言·先知》的序中强调:要建立和谐的社会风气,执政者必须真正了解民情(“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他在回答别人问他“何以治国”的时候,首先强调要确定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基本路线(“立政”),并且指出:“立政”的根本在于皇帝的自身修养和素质(“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接着,他告诉别人:落实大政方针的关键,是各级“从政者”必须了解老百姓最期盼什么、最厌恶什么(“从政者,审其思斁而已矣”)。最后,他直接告诉别人:老百姓期盼老人能受到尊重,孤儿能有人照管,病人能得到治疗,死人能有钱安葬,男子有田种,女子有布织;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老人被人侮辱,孤儿受人欺负,病人孤独无助,死人暴尸荒野,田地无人耕种,织机无人织布。扬雄希望统治者“审其思斁”的政治主张,完全是针对汉成帝以来的西汉末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说的。当时有官员上书朝廷,反映“民有七亡、七失”(七种使老百姓遭受死亡和重大损失的社会现象),如“水旱为灾”而“县官重责更赋租税”(水灾旱灾频繁发生,而地方官吏还要加重百姓的租税负担),“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地方豪强势力,无休止地侵占百姓的土地和利益),“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繁重的徭役,使农民失去耕种的时间),“酷吏殴杀,冤陷无辜”(酷吏残酷虐待百姓,昏官冤枉陷害无辜),“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以及“岁恶饥饿”而“时气疾疫”(收成很坏使百姓挨饿,瘟疫流行使百姓患病)鲍宣:《上时政疏》,《资治通》卷三十四“哀帝建平四年”。。这样的人祸与天灾,简直活脱脱的一座人间地狱的恐怖景象!
扬雄把符合老百姓的期盼和愿望作为检验“为政”措施的唯一标准,充分体现了“旧儒学”、“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扬雄最可贵最难得的地方还在于:他将这种政治主张用于衡量封建皇帝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措施,由此决定对这个皇帝是该拥护、还是该反对,并且将它作为评判所有帝王将相功过是非的重要标准。
扬雄为什么歌颂王莽?
朱熹等人认为,这是因为扬雄希望从王莽那里得到好处,或者已经得到了好处而给予王莽的回报,因此说扬雄“媚事王莽”。如果朱熹果真这样认为,那是他不了解扬雄,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让我们先看看扬雄都歌颂了王莽的哪些德政吧。《法言》全书末尾,在充分肯定王莽“勤劳”国事的基础上,扬雄对王莽“托古改制”的各种改革措施给予充分的肯定,主要有:发展教育以培养人才和推行儒家教化,演练礼乐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恢复井田制度以抑制豪强兼并土地,恢复肉刑以儆戒各种犯罪行为,鼓励耕种以发展农业生产。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完全是针对汉成帝以来的几代皇帝的弊政和严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
正是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和他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的巧妙“伪装”,完全赢得了扬雄对他的信赖,以至于使扬雄把实现自己儒家“圣王”政治的社会理想完全寄托在了王莽身上。这才是扬雄歌颂王莽的真正原因。
扬雄坚持旧儒学“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在《太玄》、《法言》中所阐述的“因循革化”的历史发展观,使他晚年选择了与刘氏政权决裂而支持拥护王莽政权的道路。应当说,扬雄的这种选择,其动机和目的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民众。因此,我们一再强调,扬雄的“事莽美新”不仅不是什么“败坏名节”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正好表现了扬雄高尚的人格和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对扬雄“事莽美新”作这样的评价,一是基于我们对扬雄“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的科学考察,二是基于我们所坚持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如果王莽确实“诈伪”,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伪装”,那也只能说扬雄缺乏政治远见而受到蒙骗,根本不存在什么“媚事王莽”、“败坏名节”的人格问题。
至于王莽是否“诈伪”,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它涉及的是对另外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自然不能妄下结论。只是因为与扬雄是否“缺乏政治远见”这个次要的问题有关,我们也不妨做一下简单的探讨以供读者参考。
考察王莽事迹的最权威资料是班固的《汉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中国的历史著作,以自《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为正史。“二十五史”中,绝大部分是后一个朝代的人为前朝修史,只有《史记》、《汉书》很少几部著作是当朝的人给本朝修史。诚如鲁迅所说,一部“二十五史”其实都是封建统治者的“家史”。撰写“家史”,本来就免不了许多忌讳,尤其是封建礼节中有“为尊者讳”的严格要求;何况《汉书》是汉朝人写汉朝皇帝的“家史”,其忌讳之多自然不难想象;再加上班固又是汉朝皇帝的亲戚(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是班固的姑曾祖母),于公于私,他都不得不对“汉贼”王莽有所挞伐。换句话说,班固所写的“王莽传”,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至少是在感情色彩方面。尽管如此,我们从《汉书》中读到的王莽,如果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感情色彩的字眼,仍然是一个既有“内圣”修养又有“外王”才德的大贤形象。请看《汉书·王莽传》中的这段话: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
将这段话译为现代汉语是:
王莽以皇帝亲戚的身份开始做官,对人谦卑有礼,遇事身体力行,从而取得美好的名誉,宗族中的人称道他孝敬长辈,老师和朋友都说他很有爱心。到他身居高位辅佐朝政以后,在成帝、哀帝时代,为国事竭尽辛劳,办事坚持原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信服和被人赞赏。何止是所谓“在家时家人一定听从,在国时国人一定听从”、“外表仁爱而言行不一”的人呢?
如果将这段话中明显带感情色彩的“色取仁而行违”去掉,班固笔下的王莽,不就是一位“内圣外王”的大贤臣吗?
由此看来,扬雄对王莽的信赖和歌颂,既不是为了“献谀邀功”,也算不得是“缺乏政治远见”。我们姑且做这样的假设:假如王莽像晋朝的司马氏、宋朝的赵匡胤那样政变成功,或者后来打败王莽的不是姓刘的汉光武帝,甚至《汉书》的作者不是汉朝人班固,那么,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王莽,还会是一个“大奸臣”形象吗?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身在官场却能一辈子淡泊名利、珍爱自己生命却能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而舍生取义、从不计较个人贫贱却始终为天下百姓疾苦担忧的人,他的人格绝对是高尚的!
那么,朱熹为什么要一再地贬损扬雄呢?
可以寻绎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是宋明理学建立“新儒学”的需要。新儒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只尊奉传统儒学中的孔子、孟子,以孔子、孟子为“先圣”,对汉、唐以来的大儒,甚至对孔子的嫡传弟子“七十子”的圣贤地位也一概予以否认;但是对两宋时期创立新儒学、发展新儒学有突出贡献的儒学大师则抬高其地位,奉为“新圣”。于是到了明朝,朱熹父亲朱松、程颢父亲程珦、周敦颐父亲周辅成、蔡沈父亲蔡元定等人,都被作为“圣人”的父亲,得到了在孔庙中被安排在孔子父亲“启圣王”身边配祀的崇高地位。而荀子则因为跟孟子唱反调提倡“性恶论”,扬雄则因为“事莽美新”而受到“罢祀”的处罚,两人的神主牌位从此被撤除。以扬雄在唐宋两代的巨大影响,要推行新儒学的那一套,自然是必须否定扬雄的地位了。子云学校的“识贤堂”第二,这是朱熹坚持新儒学道德观的必然结果。新儒学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是所谓“三纲五常”。连蔡文姬被迫嫁给匈奴单于尚且得不到朱熹的谅解,被朱熹指斥为“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何况扬雄身仕“贼莽”,不能为刘汉王朝殉节,还进而美化歌颂王莽这个“汉贼”呢?
第三,或许真的是因为朱熹没有“读懂扬雄”。朱熹说:“扬雄则全是黄老。吾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朱熹没有读懂《法言》,因为他没有像司马光那样,把扬雄的《太玄》、《法言》读了“数十过”。朱熹还说:“盖天地只有个奇偶,奇是阳,偶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朱熹竟然不知道,他直接采用邵雍《易》学研究成果所著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其实很多内容都是扬雄的《易》学思想,因为邵雍借鉴了《太玄》中很多精粹的东西,并且有诗赞扬扬雄说:“不究扬子天人学,安知庄生内外篇?”所以我们说,朱熹对扬雄的无情贬损,还有可能是由于他对扬雄的太不了解。
第四,贬损和否定扬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主张“以民为本”的旧儒学,毕竟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产物,是跟汉唐时期封建社会蓬勃向上发展的形势相适应的。南宋以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最高统治者需要一种能够维系这种摇摇欲坠的政治局面的文化思想,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南宋以后,儒学更加官方化、正统化,并且把“忠孝节义”之类的伦理道德称为“天理”。进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都完全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的需要。“事莽美新”的扬雄,被视为“逆子贰臣”而遭到挞伐,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由于“忠孝节义”是封建社会的“天理”,所以南宋以来,凡是尊崇扬雄的学者,都要在“事莽”和“美新”问题上为扬雄辩解。辩解的说法和理由主要有:(一)断然否定扬雄“事莽”,理由是扬雄死在王莽篡汉之前;(二)断然否定扬雄“美新”,理由是《汉书·扬雄传》不载《剧秦美新》之文;(三)承认扬雄“事莽”,但情有可原,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四)承认扬雄“美新”,但认为这是借歌颂之名行讽刺之实,或者认为扬雄称颂王莽的话,只是对王莽的一种期望;(五)承认有《剧秦美新》之文,但认为非扬雄所著,认为其作者是与扬子云同名的“谷子云”(谷永);(六)承认扬雄“事莽美新”,但情有可原,因为王莽太善于“伪装”,使扬雄受到了欺骗。
在众多为扬雄辩解的学者中,以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也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斗士之一的费密的辩解较为有力。
费密在他所著的《弘道书·从祀旧制议》中说:
莽之篡非忽起也,奉太后命居摄,已非一日,不过以哀章“金匮”之文即真耳。一切仍旧,校书天禄(阁),不与朝政也。必欲犯莽之怒,去位以干不测之祸,则“三家”执国命已久,先圣亦不当事之,而微服过宋矣……微子归周,圣人未尝不许以仁。子曰:“管仲相桓公,民到于今受其赐。”使先圣生宋元间,亦岂遂仰天绝吭哉?后世不以古经所载圣门旧法论人,而独取后儒偏私之说,此宋以来学者之通弊也……盖以圣人忠恕论人,则人无过者多;以后儒苛隘论之,则人皆有过而无可逃者矣。
费密这番话的大意是:如果扬雄“事莽”就是不忠不义的话,那么孔子“事鲁”也是不忠不义了,因为当时鲁国真正的执政者不是鲁定公,而是权臣季桓子。如果扬雄歌颂王莽(“美新”)就是歌颂叛臣的话,那么孔子歌颂管仲也是歌颂叛臣了,因为管仲背叛了他的主子公子纠,投靠了公子纠的敌人公子小白(齐桓公)。如果扬雄“事莽美新”就应当受到指责的话,为什么“微子归周”还会受到孔子等先圣的赞美?微子不是商朝的“叛臣”吗?
应当说,费密对朱熹等人的批判是有一定力量的。他不仅批判了朱熹等“后儒”对待汉唐诸儒的苛刻狭隘(“苛隘”)、对待宋儒的“偏私”,而且揭露了他们“苛隘”、“偏私”的目的——贬低汉唐诸儒是为了抬高宋儒。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扬雄的人格是高尚的,朱熹对扬雄人格的贬损是不足为训的。二、杰出成就
纵观先秦至两汉的学者,若论成果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之广、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之高,扬雄应当是首屈一指的。
扬雄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哲学研究领域,其代表性成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和《法言》使他赢得了“大儒”甚至“圣贤”(西道孔子)的美誉,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但是,由于这两部著作的语言过于简略,文义过于艰深,不仅现代人很难读懂,就连扬雄的同时代人也感到晦涩难懂。这不仅大大影响了《太玄》、《法言》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后世研究者众说纷纭,以至于出现了“真正读懂了扬雄的人,无不崇拜他;而没有读懂和根本读不懂扬雄的人,总是贬损他”的奇特现象。
有人说:“扬雄并非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例如他的《太玄》一书,不但在内容上是拾前人牙慧,毫无新见;即其全书的结构,也全然模拟《易经》而成。”
晋人范望的《太玄经注》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偏见甚至浅薄。可能因为论者根本不了解“《易》学”发展的历史,不了解扬雄写作《太玄》的背景和动机,更不了解《太玄》的特点和贡献。
扬雄生活的时代,为《易经》作注解的人很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京房、孟喜两家。京房、孟喜所传的《易经》,以“阴阳五行”之说为理论基础,将自然界的灾异现象,附会成人事变化祸福的征兆,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以至于极大地助长了社会上的谶纬迷信风气。受严君平影响,扬雄根本不相信“天人感应”那一套,更反感社会上遇事必筮卜的迷信风气,所以进京后不久,他就萌发了写一部科学地解释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著作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的《太玄》。
与《易经》相比较,《太玄》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
第一,创立了以“玄”为最高哲学范畴,以“首”、“赞”为经,以十一篇“玄文”为传,以逢三进一的“圜元模式”为数理逻辑的特殊结构模式。《太玄》的这种结构模式,与《易经》京房本以及其他《易经》传本按四季、六律、年轮,将卦、爻作牵强附会的排列完全不同。《太玄》的结构模式,成为宋代彭晓的《明镜图》、陈抟的《无极图》、邵雍的《方圆图》卦爻排列理论的基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