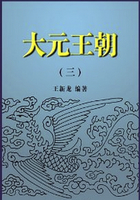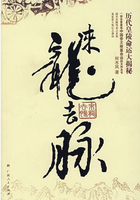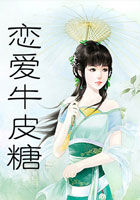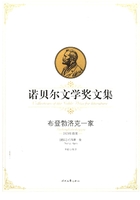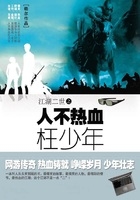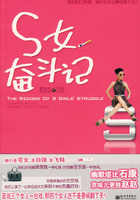今日论民族史者,若直接沿用上述旧称当然可以,然若(如我们习惯上的)改换成时下的称谓,则基本上是不准确的。据我们原有的民族学知识,民族、部落联盟、部落、胞族、氏族等都有它的特定内涵,氏族是指“原始社会以共同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种血族团体”,而部落是“原始时代的社会组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胞族组成,有些部落由几个氏族组成,中间缺胞族这一环节”。部落已不是氏族那样的严格的亲属群体,而民族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划分的人们共同体”《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397页“氏族”条、第62页“部落”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古代对族体的称谓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同一对象,称谓时可互换,率意性很强。如古代称某族,根据现代汉语双音词习惯,一般称为某民族,但古代某“族”与现今说的“民族”多半不相干。所记之“部”,有时也写作“部落”,它的对应词并不是现代民族学或人类学上所说的“部落”,它可能符合现今民族学上所界定的部落,但也可能全然不符。正如论者所言:“20世纪,随着民族志知识的深化,人类学者越来越发觉19世纪指代一个特定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原始部落’概念,其实包含着诸多不同的类型,如存在与部落不同的游群、乡民社会、种姓制度,部落这个范畴内部又可分为裂变型部落和酋邦型部落。”王铭铭:《他者的意义——现代人类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人类学本土化国际研讨会”,《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第51期,1999年。在藏彝走廊地区,各部之间差异之大是相当明显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中,大体在藏彝走廊区域的邛都、徙笮都、冉、白马均为“君长以什数”,而“地方可数千里”的巂昆明却“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我们习惯把他们都称之为部落或部落联盟,自然就不准确。很明显,他们的社会形态,从游群社会到酋邦型社会都是存在的。
我们谈“古代民族”时,一般是泛称各类人们共同体,但针对一定族体时,我自己的感觉是较为犯难。诸家论者颇不一致,择词时也因人而异,或氏族或部落,或某族某部,全凭自己的判断(有时并没有去判断)。如褚俊杰先生《吐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II解读》一文,揭示了藏彝走廊古代民族的一些重要问题,石硕先生《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褚俊杰文载《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石硕书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褚文内容转述自此。一书对此作了十分深入的阐述和论证,同时也沿用了褚文使用的“氏族”一词。问题是,褚文如何确定“恰”、“穆”是两支氏族呢?他们为何又不能说成是两支部落呢,抑或是两个“民族”呢?不能说两支人通婚,就一定是具有共同血缘的氏族。这在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注意到,石著中“嘉绒”用了族群这一概念,那么,它与“恰”、“穆”的相同性和相异性如何?我以为,如果把“恰”、“穆”二者同样称为两个族群也许更恰当一些。至于“恰”、“穆”两个族群的社会状况我们可以(如果可能的话)作进一步的研究。
有共同的特性才称得上族群,这种共性可能“是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这一点在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特别重要。古籍所载藏彝走廊地区族称,一般都十分简略。仅仅凭所载三言两语,难以给它们“定性”。如《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上记载的藏彝走廊地区的卷夷大牛种、三襄夷、白狼、楼薄、旄牛夷、青衣道夷等,除白狼夷的“文本”多一点外,余皆不过三言两语,它们应该都是东汉官员对“他者”的客观认定,我们现今无法判定是否符合其主观认同,不能因此否认他们是各种不同的族群。又如据今研究统计,彝族自称和他称有七八十种之多,属中国少数民族中称谓最为复杂的现象,大约自元代起,中原人即以“罗罗”一词来称呼彝族的众多先民参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虽然“绝大部分‘罗罗’并不知道自己被称为‘罗罗’”(美)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并不影响“我们”认定彝族先民“罗罗”是一个大的族群。正如今聚居于阿坝州的羌族,唐宋时甚至更早中原人就把他们称之为羌人,至元明清时期仍然如此。虽然“羌”的使用范围可能更加广泛,但却常常把居住在今汶理茂地区的羌民同与之相邻“夷”或“番”民区别开来,后者则主要是指嘉绒诸部。明代嘉绒之董卜韩胡(番蛮)常与杂谷(羌)相争杀,正是二者族类不同之故,汶理茂之“羌”是中原人对该族群的客观认定。同“罗罗”一样,许多羌民50年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羌族”,但并没有妨碍自唐至今对“羌”的客观认定。其实,50年前不知道自己所属族别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包括藏彝走廊在内的西南地区各族群众,据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三大民族调查所留下来的材料,许多群众都只知道一个较小范围的自我称谓。正是通过调查和识别,才最后确定了较大范围的统一族称。族称的确定并经过几十年的运用,许多本来只知道较小范围自我称谓的该族成员逐渐认同了较大范围本族族称。后来的情况证明,族称的统一强化了本“民族”的自我族群认同。在本次藏彝走廊会上,四川省民研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介绍说,他本人老家所在的乡亲1949年前被称为“西番”,20世纪50年代定为藏族,现在的研究表明,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羌语支。乡亲们问他:我们是藏族,怎么变成羌族了?袁先生告诉说:藏族还是藏族,只是原来使用的语言属于羌语支。这表明,这支“西番”被确定为藏族后,逐渐产生了新的民族认同。
在今日可见的民族史特别是古代民族史的汉文材料中,可以说基本上属于“被确定”的类型,一般情况下,人们是难以知道当时各族群的自我认同情况的。“被确认”不能等同于“想象的群体”,被确认的对象不应该全被虚化。古今之异,主要在于“确”与“不确”程度上的区别而已。所以我认为,“族群”这一概念在民族史研究中,可以得到也应该得到广泛的运用。
二、民族语言与支系
“藏彝走廊”民族自然不只是藏族和羌族,也不仅是指藏语支民族和彝语支民族,它主要是指藏缅语族民族而言。走廊地区中包括过去被认为“语支未定”的羌、普米、独龙、珞巴、怒等语,都属于藏缅语族语言,因此,把它理解为藏缅语族的民族走廊符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如马曜先生早年所称的“藏缅语族走廊”马曜:《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即是。
走廊地区藏缅语族的语言情况十分复杂,支系很多,其中一些至今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毫无疑问,族群的文化认同中,语言认同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民族而言,语言是民族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然而在现实中却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同一民族并不一定使用同一种语言,或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是否意味我们一般所言民族定义中的“共同的语言”已不适用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共同语言”应指该民族的主源,而不是说该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说一种语言,其内部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构成了该民族的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包括后来因各种原因“加入”进来的成员或群体。
第二,“共同的语言”应该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语言现象,彝语支的彝族、纳西族的方位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北方为水头,南方为水尾。白族中的“那马人”方位词,所谓“江上截”和“江下截”实际意义也是“北方”和“南方” 龚友德等《那马人的时空表述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但此三族现今居地,河水并不符合南北流向。也就是此三族在产生方位概念之时,应该居住在河水南北走向的区域,这一地区正是藏彝走廊地区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此亦可见语言特别是语源研究在民族或族群的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就现状而言,共同的语言并不是民族或族群认同的一个必要条件。包括藏彝走廊在内的西南民族中有许多人已基本上不用本民族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共同语言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自我民族认同。所以,“共同的语言”不一定是现实的反映,而是该民族主源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况。有的延续至今,有的发生了变异。王明珂先生以羌族为例说,当不同地方的羌族人在一起时,先问对方是哪里人,然后会问“你们那儿太阳怎么说”等一类的问题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第65页。,如果找到了“知音”,彼此就有更多的亲近感,这是语言发生了变异的例子。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当说某种语言的人们分成彼此不相接触或接解甚少的群体时,语言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F.Hockett)认为,分化百年左右,可能会产生属于一种语言的若干有差异的方言。分化千年左右,一种语言就可能分化成两种语言。因为它们有共同来源,所以这些语言有亲属关系(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第42章《种系发生学的变化》,索振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此而言,“共同的羌语”难以认为是想象或建构的结果,如果“想象”,也不是在“凭空”中建构。藏彝走廊地区自然环境复杂,交通和交往十分不便,即使是同一“民族”,土语方言的大量存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羌族地区就是如此,此山和彼山之间语言不一定完全相通。明代初期,茂州汶山县官员就说,“羌民二十八寨言语不通”《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三月辛巳。“羌语”可有方言土语甚至更细的区别,如各地汉语可能彼此也言语不通,但难以否认它是一种共同语言。20世纪90年代有过创造“羌族文字”的努力,当然是希望建立共同的羌语,就像政府提倡大家都说普通话一样,以减少彼此交往的困难。
与语言分类关系密切的是民族研究中的“支系”问题。有人认为,“支系是族群的一个对应范畴”王实在《“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持此观点的云南大学黄泽提供的《族群视角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研究》一文“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这值得商榷。族群的定义虽然现在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它是某一具有主观认同或客观认定的人们共同体则是大体成立的。语言系属分类自有本学科的标准,虽然有人质疑划分的“客观”标准不一定那么客观,但语言分类学的“科学性”却难以简单否定。语言学家根据语言的亲疏关系来确定系属,讲语言分支或支系(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等)这好理解。民族的划分虽然与语言相关,但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许多不同的民族,反之,同一民族的人,也可以包括不同的种族成分。所以,族群难以成为民族支系的对应范畴。
我国“民族”的划定,主要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等调查的结果,包括语言、文化、习俗、认同等的“客观”情况而确定的。民族识别政策固然出于政治的考量,但对族别的确定和识别却并不是泛政治化的,调查的结果——文化和历史因素是民族划定的主要依据。限于主观和客观的诸种条件,“调查”的结果本身不一定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与该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呈现“科学”的“对应和吻合”,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学术上的。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以致或有重新“识别”的要求。重新识别的要求当然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但将族群完全视为争取政治与经济资源分配以求得本族群的延续的“工具论”并不能解释要求重新“识别”的全部内涵,要求重新“识别”起码要有自认为有不同于他人的文化共性的基点,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和复杂化了。所以,我以为族群理论的工具论应该与根基论调合,从要求重新识别这一问题对此可以有充分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