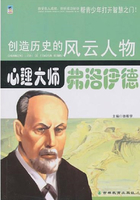“十二法印”中“十者是世间法及出世法,皆假施设,悉是因缘开方便道,为化众生,强立名字”,“十一者生死道场,等无所有,无得无舍,是名解脱”,吻合了佛教般若中观学派强调涅槃境界与世俗世界无本质区别的观念。“十二者正道真性,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名正中道”,显然又借鉴了《大般涅槃经》所谓:“中道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佛性常恒,无有变易。不得第一义空故,不行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大正藏》第12册,第523页。《大般涅槃经》强调世俗世界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涅槃境界“常乐我净”。这种对世俗世界否定、对涅槃境界肯定的观点,与“十二法印”一方面肯定道体“常乐我净”,另一方面认为有为之法无常、一切世法无我、有心之法苦恼、世间不净秽恶的思想如出一辙。第六法印又特别强调“出世升玄,至道常住,湛体自然,无生无灭,离有为相”。
“十二法印”的理论特质可以概括为:突出出世色彩的“升玄”解脱;道体兼具“常”、“本”、“源”、“根”的理论特征;道体是神格化的“道”在“事”的层面的呈现。
其实“法印”概念也源于佛教,吉藏在《法华义疏》卷六中说:“我此法印者,以理为印。谓文与理相应,则应信受;文乖此理,则不应信。理印有二:一体印……即是实相名之为印。……二者用印……通言印者,印定诸法不可移改。又释以文为印,将文定理,谓理与此文相应者,乃为实理,故名法印也。”《法华义疏》卷六,《大正藏》第34册,第541页。“印”乃印定诸法不可移改之义,故称法印。佛教有“一法印”、“三法印”、“四法印”诸说,大乘佛教仅有“诸法实相”一法印,即一实相印。如智所说“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即是法身。……我以相严身,光明照十方,为说实相印,实相印即法身。”《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五,《大正藏》第33册,第745页。“一切大乘经但有一法印,所谓诸法实相。……故《大智论》云:除诸法实相,其余一切皆是魔事。诸法实相即是真性解脱之异名也。问曰:声闻经何故但用三法印,摩诃衍教何故但用一实相印?答曰:声闻根钝著重,故须说三法印,令厌生死苦、欣涅槃乐。菩萨大悲、根利、易悟,生死即涅槃相,能不舍生死、不取涅槃、入不二法门,故佛但说诸法实相印也。”《维摩诘玄疏》卷六,《大正藏》第38册,第554页。智和吉藏学说的思想渊源都可以上溯到印度大乘佛教龙树之学,中观般若学说以阐释“诸法实相”为本,故称诸法实相为大乘佛教义理的信印。佛教又称《杂阿含经》卷十所指一切行无常(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为三法印。三法印加“一切行苦(一切有为有漏之法皆迁流不息)”则称四法印。四法印再加一切法空(一切现象虚幻不实)则称五法印。智说:“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之,即是佛说。……大乘经但有一法印,谓诸法实相,名了义经,能得大道。”《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八,《大正藏》第33册,第779页。
龙树在《大智度论》中对“诸法实相”命题从不同角度作了阐述,“观诸法实相,非空非不空,不有非不有。”《大智度论》卷五,《大正藏》第25册,第99页。“三世诸佛,皆以诸法实相为师。”《大智度论》卷十,《大正藏》第25册,第128页。“诸法实相即是般若波罗密。”“此中实相者,不可破坏,常住不异,无能作者。如《后品》中佛语须菩提:‘若菩萨观一切法,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等,亦不作是观,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是义,舍一切观,灭一切言语,离诸心行,从本已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一切诸法相亦如是,是名诸法实相。”《大智度论》卷十八,《大正藏》第25册,第190页。“诸法实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门:空、无相、无作。”“问曰:何等是诸法实相?答曰:诸法自性空。”《大智度论》卷二十,《大正藏》第25册,第207页、213页。“不可得空即是诸法实相。是‘不可得空’义,如先‘十八空’中说。”《大智度论》卷三十九,《大正藏》第25册,第346页。“诸法实相,所谓性空、无所得、空等诸法门。”“离是有、无二边,处中道,即是诸法实相。”《大智度论》卷九十九,《大正藏》第25册,第746页。大意是说,离有(空)、无(有)二边双遣双非的中道般若“性空”之理,名“诸法实相”,亦可称之为“涅槃”、“般若波罗蜜”等,是最高的、绝对唯一的真理。“诸法实相”同时也代表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本不可言诠的成佛境界,但是通过“诸法实相”的表述似乎亦可言说,这就是《中论》所云:“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中论》卷一,《大正藏》第30册,第1页。“众生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中论》卷四,《大正藏》第30册,第33页。
对比《本际经》“十二法印”所反映出来的理论特质,无疑是大乘佛教“诸法实相”真理价值判断标准的“悖论”。然而,《本际经》对“重玄”之道的诠释却和“诸法实相”命题中离有(空)、无(有)二边双遣双非的思辨方式、认识方法有相通之处。说明,此时道教在恪守传统理论前提下,与佛教既融合又斗争的过程中,注重借鉴“关河学派”所传中观般若学的哲学方法,开创出有别于“昔教”(小乘道教)的“今教”(大乘道教)的真理价值判断标准。“将示重玄义,开发众妙门。了出无上道,运转大乘辕。……不有亦不无。空假无异相,权实故同途。道场与烦恼,究竟并无余”,宣扬重玄体道“开演真一本际法门”,这也是《本际经》的思想宗趣之所在。道体与道性的理论特质无疑是大乘道教的“诸法实相”。《本际经》标榜自己“此经大乘,兼包众经,一切官属,悉从其教”,“此经说真道根本,能生法身慧命。十方得道过去未来三世天尊等,莫不履行而得至真,具一切智,成无上道,到解脱处,为大法王”。《本际经》自然也就是道教经教体系中的大乘究竟“了义”经典了。
四“法印”中的“大我”及“常、乐、我、净”思想
第七法印“真一妙智,自在无碍,神力所为,随意以辨,故名大我”,将智慧升玄得道解脱的境界称为成就“大我”,“真一妙智”即“道”之异名。
“大我”本为佛学概念,意思是远离我执、我见达到自由自在境界之最高“我”。如《大宝积经》说:“菩萨静虑,自在而转;诸有所作,善圆满故。菩萨静虑,是为大我;以妙智慧为大我故。舍利子,如是无量菩萨静虑,皆是菩萨摩诃萨依静虑波罗蜜多之所集起。”《大宝积经》卷五十,《大正藏》第11册,第294页。在《大般涅槃经》中把“大我”理解、解释为“大涅槃”、“大自在”,“云何复名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云何名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则名为我。何等为八?一者能示一身以为多身,身数大小犹如微尘,充满十方无量世界。如来之身实非微尘,以自在故现微尘身,如是自在则为大我。二者示一尘身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来之身实不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无碍故,直以自在故满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为大我。三者能以满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轻举飞空过于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无障碍。如来之身实无轻重,以自在故能为轻重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来一心安住不动,所可示化无量形类各令有心。如来有时或造一事,而令众生各各成办;如来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为根自在耶?如来一根亦能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如来六根亦不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来之心亦无得想。何以故?无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为得,实无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来计有得想,是则诸佛不得涅槃。以无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诸法故名为大我。七者说自在故,如来演说一偈之义,经无量劫,义亦不尽。所谓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来尔时都不生念我说彼听,亦复不生一偈之想。世间之人四句为偈,随世俗故说名为偈。一切法性亦无有说,以自在故如来演说。以演说故,名为大我。八者如来遍满一切诸处,犹如虚空。虚空之性不可得见,如来亦尔实不可见。以自在故令一切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以是义故名大涅槃”《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一,《大正藏》第12册,第746页。“大我”含有常一主宰之意,为涅槃四德“常乐我净”之“我”。意思是说没有得到解脱的众生所执著的自我之身心无自在性、常一性;唯有佛陀所证得之涅槃才是真实、常住不变的,故称为大我,义同真我。
“常乐我净”之“常”即永恒性,说明佛身是常,指“法身”;“乐”亦称常乐,表达永恒的精神宁静,指“涅槃”;“我”又称“大我”,指“佛身”。“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大般涅槃经》卷二,《大正藏》第12册,第378页。“净”又称“大净”,指佛法。涅槃四德同时也是佛性四德“佛性常乐我净”,意在突出强调“佛性是常,三世不摄”《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三,《大正藏》第12册,第562页。,“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实、三真、四善、五净、六可见”《大般涅槃经》卷三十四,《大正藏》第12册,第568页。围绕“泥洹不灭,佛有真我(如来常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形成佛性的有无、成佛的可能性等佛性论的中心议题。南陈沙门真谛将佛性进一步解释为“般若波罗蜜是大我种子”,是“法身四德”之一《摄大乘论释》卷三,《大正藏》第31册,第173页。
对比“十二法印”中也包含了“常乐我净”思想,如:“至道常住”(常)、“真一妙智,自在无碍,神力所为,随意以辨,故名大我”(乐、我)、“离二无常,不受诸爱,心相寂灭,故名清净”(净)。只不过此“常乐我净”意在突出强调对道体理论特质的诠释性描述,此“道”亦指智慧升玄得道解脱的最高境界。
“十二法印”的思想实质同时也是继承了《庄子·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南华真经注疏》第615页,中华书局,1998年。的思想。“以本为精,以物为粗”,成玄英疏:“本,无也。物,有也。用无为妙道为精,用有为事物为粗。”“十二法印”将“以本为精”发挥为道体的“常乐我净”;“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发挥为有为之法无常(第一法印)、一切世法无我(第二法印)、有心之法苦恼(第三法印)、世间不净秽恶(第四法印)。发挥了太一(道体)“以本为精”、“常无有”、“空虚不毁万物为实”的特点,突出了道教之“道”的本体性、实在性、神圣性。
在印度佛教史上源自印度哲学界之“大我”思想,一度被佛教《般若经》和龙树以“诸法实相”原理之无我、空观等思想所彻底否定。在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说:“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实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萨自性空,菩萨名空。……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生、不见灭、不见染、不见净。何以故?但假立客名,分别于法而起分别;假立客名,随起言说。如如言说,如是如是生起执著。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如是等一切不见,由不见故不生执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1—200卷(卷四),《大正藏》第5册,第17页。一切语言、概念乃至佛学理论中关键“名相”的绝对实在性,均在“无分别”的观念下给予彻底的、毫无保留的否定。《中论》一开始就提出:“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中论》卷一,《大正藏》第30册,第1页。龙树通过对四对彼此对立的范畴的遣执,阐述了“中道”与“缘起”思想,因而被称为“八不中道”、“八不缘起”。“众生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中论》卷四,《大正藏》第30册,第33页。被看作是对“中道”的解释。只有把“性空”与“假有”紧密结合起来才是中观学派所谓的“空”,从此定义亦可说明,“中道”的思想价值体现在对般若空观命题的阐释上。《中论》以一系列偈颂阐述了“无我”的观点:“若我是五阴,我即为生灭;若我异五阴,则非五阴相。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名得无我智。……内外我、我所,尽灭无有故;诸受即为灭,受灭则身灭。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中论》卷三,《大正藏》第30册,第23页。破斥了众生之所以能够产生执著有实体自我观念的根本条件“五蕴内”、“五蕴外”、“我所”皆一无是处,即便可以成立也都是缘起性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认识程度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能得到解脱。针对小乘佛教法体实有的主张,《中论》反驳道:“众缘中有性,是事则不然;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义?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若诸法有性,不应从众缘出。何以故?若从众缘出,即是作法无有定性。”同上,第19页。“实体”如果能从多种条件及因素中和合产生,说明它仍然是被“炮制”出来的,根本就不具备永恒性。从“缘起性空”的立场分析,法体实有的主张无异于“戏论”。
“《般若经》等在打破了世间与涅槃的绝对界限后,将二者的本质统一在‘性空’上,而《大般涅槃经》则将二者的本质统一在‘妙有’上,《般若经》与中观派虽讲‘性空’与‘假有’的统一,但实际侧重在否定一面。《大般涅槃经》则明显侧重在肯定的一面。”姚卫群:《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第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由《大般涅槃经》所体现的“涅槃四德”、“佛性四德”、“法身四德”思想,反映出来的“佛性”、“法身”的本体性、实在性、神圣性特质与印度大乘佛教般若中观理论是格格不入的。
中古时期的道教思想界无疑敏锐地洞察到了佛教理论体系中存在的这一“吊诡”,并巧妙地为己所用,充实、完善了道体论学说体系。综合分析“十二法印”中的“大我”之说显然具有“性空妙有”的特征。当道教徒开发显现自身独具此本体之“道”时就发现了“大我”,自我主宰的独立个体——能知的主体与所知的主体的统一——主体自我与本质存在的完全合一,发现了“太初”某种与他们自身相同的先天因素。如同加达默尔在论述黑格尔有关教化理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只要单个个体于其中生长的世界是一个在语言和习俗方面合乎人性的造就的世界,单个个体就始终处于教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对其自然性的扬弃中”,“构成教化本质的并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理所当然以异化为前提的返回自身”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基于对“此在”之道的认识与诠释,道教建立起我命在我、神仙可学、神仙可致的生命本体论哲学。
五“大我”之说与中古时期的佛教中国化
“大我”之说之所以能够被道教哲学成功借鉴、转化利用和这一时期的佛教中国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