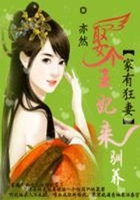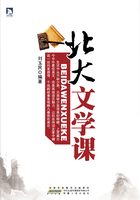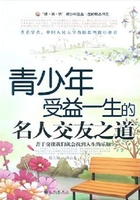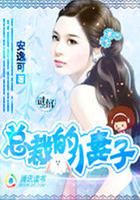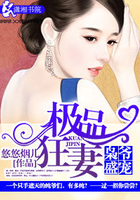尽管奢嫁之风盛行于清代社会,但是与女性记录的缺失一样, 有关嫁妆的记录在清代的官方史书中也处于缺失状态,我们只能从一些侧面的记叙中得到只言片语。譬如一向被视为婚姻之完美程序的“六礼”,全部为男方家庭的行为和礼仪,“六礼备而婚姻成”, 对于女方家庭在婚姻缔结当中的作用丝毫没有提及。其中的“纳征”,即男家向女家下聘礼,被视为六礼的关键步骤,而女家的陪送妆奁则显得无足轻重。清代官方对于婚礼所做出的规定,一方面
强调对于“礼”的尊崇,如何告庙、如何礼宾、如何合卺等;另一方面严格婚礼中的等级顺序,如详细规定了官员士庶的婚礼标准, 以防止百姓僭越。但这也是针对男家而言的,对于女家的陪嫁,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只有一句:“婚期前一日,女氏以奁具往陈婿家。”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五,《礼部》,9439页,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可见,从官方的角度讲,对于嫁妆或者婚姻中女家的行为并不重视。民间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从众多的地方志、私人笔记等记载中可以发现,首先女方家庭在婚姻缔结中往往掌握着相当的主动权,俗谚“抬头嫁女,低头娶妇”即蕴涵了这个道理; 其次嫁妆不仅是百姓婚姻缔结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而且其从筹备到发送亦有着诸多的讲究和仪节,并不逊色于男家的“纳征”之礼。可见,百姓对于嫁妆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官府,通过对嫁妆以及陪嫁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清代不同地域的习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于婚姻和女性的不同理解,这也是本书所要体现的主旨之一。
嫁妆既然是围绕女性展开的,必然对女性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儿没有继承权,这是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因为财产继承的方式为诸子均分,女儿无权参与其中,宗祧、官爵等继承权利就更与女性无关了。但是,我们通过对分家文书等史料的研究发现,家庭在分家时十分注重女儿的经济利益,如果有女儿尚未出阁,要预先留出她们成婚之前的生活费用和成婚时的嫁妆花费,而且后者往往从厚。如果分家时女儿已经出嫁,一些家庭还会追赠她们一定数额的嫁妆,以补从前之不足,其实是以追赠奁产的名义分给女儿部分家财。这虽然不能充分说明女儿具有对母家财产继承权利,或者说女儿不能与儿子具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利,特别是在家庭有儿子的情况下①(清代法律规定,在家庭没有亲生子和合法继子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家庭财产,见马建石、杨育尚:《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八,419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得到嫁妆是每个女儿的基本权利,家庭在分家时必须关注女儿,特别是未婚之女的这种经济权利,而女性也通过得到嫁妆参与了对于母家财产的分割。清代,女性本身对于自己的这种权利已经有所认识,并且积极争取,许多竹枝词和民间歌谣都有此方面的反映:
玉满奁,珠一斛,宝钿金钗杂罗縠。席卷母家财,女心犹未足。昔人嫁女仅卖犬,今者几至田宅典。锦绣以上侈裁剪, 犹道父母力弗免。女勿恹恹愿尔思,异日亦有嫁女时,破费不赀当自知。②(《中国风土志丛刊》第35册,《吴俗讽喻诗》卷三,14页)
女儿亲,不是亲,全副嫁妆还嫌轻。③(《沙川县志》卷十四,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檐前鸟,噪奁前,看新娘子好妆奁。妆奁少,一定恼。④(《连城县志》卷十七,《礼俗》,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
尽管词和歌谣的作者是站在维护男权的立场上斥责女儿对于家庭财产的分割,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向处于家庭阴影之中的女性开始勇敢地站出来,向父母争取自己应得的经济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男不言内,女不言外”①(《礼记正义》卷二十七,《内则》,8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传统礼教的规定将妇女的活动范围和视野局限在家庭之内,即使在家庭中,她们还要从父、从夫、从子,扮演着第二性别的角色。除了儒家思想的渲染外,女性没有经济来源也是她们在家庭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她们需要依赖男性生活,没有独立决策事务的能力和机会。而嫁妆几乎是女性在婚后的漫长岁月中唯一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这份财产无需融入夫家、不参与将来的分家,翁姑和丈夫都无权干涉,特别是当嫁妆达到一定的数额时,无疑成为女性一笔可观的人生财富。女性恰当地使用自己的嫁妆奁产,不仅可以帮助她们树立和巩固其在夫家的地位,例如不少妇女用奁资孝养翁姑、资助丈夫入仕或经商、为家庭其他成员谋福利等,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由刚刚踏入家门的“新妇”逐渐转变为整个家庭内部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凭借嫁妆所提供的经济实力,女性开始扩大她们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除家庭事务之外,一些妇女还利用嫁妆救济贫困族人、辅助族中老弱病残,从而得到宗族的认可和尊敬;另一些妇女则通过对丈夫和儿子事业的干涉,展现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才能,这也建立在她们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
嫁妆除对女性有着积极的影响之外,也引发或加重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尽管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但是“奢嫁”给家庭造成的经济压力和女性对于嫁妆权利的争取,加重了人们———主要是作为社会主导性别的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这首先表现在,在奢靡之风的影响下,婚姻的各个层面都日趋豪奢,而人们对于嫁妆之奢格外反感,“嫁女装资浪费,尤所宜戒”②(《海澄县志》卷十五,《风土》,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男家之不识事理者,犹以妆奁多寡揶揄;妯娌行坏俗不情,莫此为甚”①(《成安县志》卷十,《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至奁具,则糜费已甚,始而富家稍炫其妆,继而迭出求胜,渐至贫窭效尤,典卖以从,此则侈靡之宜变者也”②(《万载县志》卷一,《方舆·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等等。不少地方志作者以厌恶的口吻描述了奢嫁对于社会风俗的恶劣影响,其中暗含着对于女性及其嫁妆权利的偏见。其次,“奢嫁”导致溺女之风日趋严重,“自俗之弊,竞炫妆奁,铺张街衢,女随其后入门,盛饰则翁姑喜,否则反唇相稽,率以女为劫,诞女则仇之,溺女之风于是乎炽”③(《德兴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八年刻本); “嫁女重妆奁,鼓吹迎送,炫耀俗目, 贫者固难取办,富家亦难为继,故溺女成风,始作俑者流害不浅”④(《龙南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光绪二年刻本);“中人家行嫁,无明珠、翠羽之属,卒以为耻,故愚拙之民生女多不举”⑤(《长泰县志》卷四,《地理·风俗》,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女亦人也,虑其嫁之不足以逞,忍绝其天性之亲以为得计,是丰于嫁者之为祸烈也”⑥(《阳江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二年刻本);“嫁女资奁亦病于厚,女生多不举,盖有由矣”⑦(《淳安县志》卷一,《风俗》,光绪十年刻本); “贪者较妆奁,故有生女不举者”⑧(《萧山县志》卷八,《风俗志》,康熙三十二年刻本);等等。溺女之俗在中国存在已久,其成因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尽管清人也承认“惟溺女,旧有此风,询之州人,大半亟望生男者为之,未必预为奁饰计”⑨(《广德州志》卷二四,《典礼志·风俗》,光绪七年刻本),即性别歧视是溺女的主要原因,只是人们更乐意将其归咎于嫁妆罢了,这直接导致了对于女性的歧视。人们还将童养媳、抢婚等社会现象归为嫁妆的高昂,也是这个原因。再次,父母无力与“奢嫁”或“厚嫁”的社会风气抗争,转而将怒气宣泄在女儿身上,生育女儿称为“贼入家”,“率以女为劫,诞女则仇之”,嫁女“破娘家”等,将家庭贫困的根源归咎于女儿,更加重了人们对于女性的歧视。
三、清代嫁妆的差异与变化
嫁妆在清代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年代的嫁妆均有一定的差异或变化,具体体现为城乡差别、人群差别和时代差别。
清代的城乡差别反映在婚嫁之中为“大概乡里多俭,城市多侈”①(《安福县志》卷二四,《风俗》,同治八年刻本)。以嫁妆的抬送时间为例,清代法令规定嫁妆应于婚期前一日抬送至婿家②(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五,《礼部》,9439页),城中多遵循这一规定,而乡村则多于吉期当日抬送。如《思南府续志》记载:“城中女家,于未嫁前一日,押送妆奁到婿家陈设,为女挂帐而归;乡村道里辽远者,则随彩舆以往。”③(《思南府续志》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457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其实,道路遥远只是不提前抬送嫁妆的客观因素,主要原因为“乡村则随轿抬送,以节靡费”④(《沧县志》卷十二,《礼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先期抬送嫁妆是婚姻缔结中较为隆重的仪式,需要有相当规模的陪送物品并且配以迎、送嫁妆的队伍和鼓乐等,是婚礼中最为热烈、最吸引外人关注的仪式之一。这对于自给自足的乡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且中国广大乡村一向保持着质朴的民风,不尚繁文缛节, “乡人辄以杯酒联姻,妆奁不以金玉为饰”⑤(《清平县志》第四册,《礼俗篇》,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因此先期抬送嫁妆在乡村往往简化为“随轿抬送”,这在士人眼中被看作“乡居不能备礼”⑥(《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一,《风俗》,民国十二年刻本)。而城市,特别是那些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百姓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较高,人们追求享乐,崇尚繁文缛节,奢靡之风正是从这里兴起:“嫁女奁仪,应当随家丰俭,近日趋于奢侈,古风渐靡,然惟城市大家为然”①(《万源县志》卷五,《教育门·礼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奢风既起,城中普通百姓虽“苦陪送”,也只得勉为其难,以免贻笑大家,多数城市家庭的嫁妆相对比较丰盛,在婚期之前隆重地抬送至男家。
清代各地的嫁妆都有其习惯构成,分为三六九等,如京城一带,嫁妆以抬数计,“中等之家,大半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富者则自数十抬至百余抬不等,贫者则十六抬、二十抬, 再次则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雇扛肩人送去,不上抬”②(《北平风俗类征》,《中国风土志丛刊》第13册,128页)。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不同等次的嫁妆。因此,嫁妆的等次直接体现着家庭的社会等级,不同等级的人群陪送的嫁妆亦不相同。贫家的嫁妆可以十分简略,“随身奁箧而已”③(《汾阳县志》康熙五十八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 599页),甚至“妆奁有若无者”④(《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富家则“奁具美备,动费千金”⑤(《武昌县志》卷三,《风俗》,光绪十一年刻本)。清代的婚姻论财的记载多出现在贫困之家,如河南巩县“贫家亦有论财者”⑥(《巩县志》卷七,《民政·民俗》,民国二十六年刻本)、宜阳“夫小户贫家有论财者”⑦(《宜阳县志》卷六,《风俗》,光绪七年刻本),湖北钟祥“亲迎、纳采,称其家之有无,女之妆奁亦如之,独小户贫家始有论财之说”⑧(《钟祥县志》卷二,《建置沿革·风俗》,同治六年刻本)。贫家之温饱问题尚难解决,不仅不能为女儿提供嫁妆,而且希望借此缓解家庭的贫困,因此多索彩礼,少陪妆奁;富家一来实力雄厚,分财与女,二来追求时尚,奢靡夸耀,三来不愿有“卖女”之嫌,因此多多陪送妆奁。清代有俗谚,“上等之家贴钱嫁女,中等之家将女嫁女,下等之家卖儿卖女”,说的就是此种情形。因此,嫁妆与聘礼的多少往往成反比,“盖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其妆必少,甚至毫无。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其妆奁反多”①(《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嫁妆的时代差异集中体现在它的由俭入奢、奢靡日甚,这也是清代嫁妆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地方志中有关这种变化的记载俯拾皆是:
《长寿县志》:“近来风气渐趋奢靡,物价奇昂,以数百金嫁一女,殊不足道,视前辈饶裕之家,至多以二百金为限者,且数倍矣。”②(《长寿县志》卷四,《风土》,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兴宁县志》:“嫁女者,前此奁物不过日用布帛,富者侍婢、奁田;今则中等之家亦彼此相效为观美装。郎须寒暑衣服,女更倍之,绫缎远求京扬,珠翠争夸新样,一切器具备极精工,除婢女外,尚有奁钱数十千、数百千不等。”③(《兴宁县志》卷五,《风土志》,光绪元年刻本)
《广宁县志》:“乾隆年间,中平之家妆奁之费大约数十金,或百金,即富厚之家亦不过三五百金。迩来多有倍于此者。”④(《广宁县志》卷一二,《风俗》,道光四年刻本)
《上林县志》:“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钱二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中资之家,每经一次婚嫁,为儿女还债必磬多年艰苦居积。”⑤(《上林县志》卷六,《社交部·风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定海县志》:“赠嫁之具,昔颇简朴,中人以下之家不过略备衣服、箱笼、用具,约值二三百金而已。迩年习尚奢靡,富家倡始于前,一女出嫁,动辄数千金,中家相率效尤,大抵以千金为律, 甚至割产举债而不惜,亦可异也。”⑥(《定海县志·方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昌乐县志》:“二十年前,中产之家嫁女妆奁无多,今则华靡相竞,较前不啻倍蓰。婚姻论财, 不为怪,此风俗之大变也。”①(《昌乐县志》卷九,《风俗考》,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代嫁妆规模的逐步升级,以及时人对于这种变化的惊诧和感慨,发出力挽此风的呼吁,这为清末新式婚姻的出现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文明结婚”。清末有关“文明结婚”或者“新式婚姻”、“自由结婚”的记载甚多,在“文明结婚”中,一切传统的婚
姻礼仪都被弃置一边,婚姻的目的不再是“合二姓之好”,而是以自由结合为基础,不索要彩礼,不陪送嫁妆,使禁锢千年的两性思想得以解放。但是客观地讲,清末的“文明结婚”或者“新式婚姻”,仅限于少数“通都大邑”中的部分人群,广大的农村和内地受到的这种影响很小。“先进思想家从西方引进,并以微弱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和职能集团为依托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近代化观念与信息,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地漂浮在广阔的乡土文化带的上空”②(程肃欠:《晚清乡土意识》,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并没有给清代社会带来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