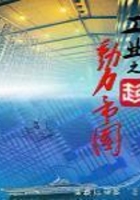§§§第一节 汉魏之际庄学的复兴
本书谓庄学在汉魏之际复兴,是相较于秦初至汉末以前这一段时期的庄学传播和发展而言的。《庄子》一书所代表的庄子学派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这是毋庸置疑的,《庄子·天下》和《荀子·解蔽》在总结先秦学术时都把庄子列为一个独立学派,其地位与孔子、老子并列《庄子·天下》把天下学术分为六大派:墨翟、禽滑厘一派,宋钘、尹文一派,彭蒙、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桓团、公孙龙一派。《荀子·解蔽》列举了七个并立学派,即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和孔子。今人刘笑敢先生通过统计战国末年文献引用《庄子》的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庄子》一书在当时就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在战国末年,《庄子》书中至少有十四篇被《吕氏春秋》、《韩非子》引用过,这十四篇占今本《庄子》三十三篇的百分之四十二左右,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假如当时《庄子》尚未成书、尚没有较广泛的流传,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但此后至汉末以前,庄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庄学的潜行时期参见阮忠《庄子创作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从总体上说是比较准确的。这一时期《庄子》的接受和传播非常有限,上不及皇室统治集团,下不见于平民百姓之家,知识阶层中,也只有少数人对《庄子》真正倾心,如贾谊、司马迁等,他们都是在有过特殊人生遭际之后才将目光投向《庄子》。对《庄子》的研究就更少了,只有淮南王、司马迁、班彪等人有过只言片语的评论。有研究者盛赞《淮南子》首次将老庄并称、《史记》首次为庄子立传,他们认为这是庄子地位提高的标志。这是将西汉中后期(《淮南子》和《史记》创作的时期)的《庄子》接受与西汉前期的《庄子》接受相比而得出的结论西汉前期,笃信黄老,主要以为统治术,兼以为养生术,《庄子》几乎没有影响。变化大约起于景帝时期,至武帝时期更甚。如果将比较关系中的后者换作先秦时期,则可知老庄并称不是提高了庄子的地位,而是取消或至少是降低了《庄子》思想本身的独立性。
这时期的庄学几乎都在老学的荫蔽之下。《淮南子·要略》云:“《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考之前后文,可见老庄并称的着眼点在于对祸福、利害、得失转化之势的关注,而这主要还是老子的思想。《史记》中的庄子小传完全是老子传之后的附言——“庄”不仅不见于列传题名中,司马迁还将庄子思想一言以蔽之,称“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庄子思想独有的价值——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庄传中列及庄子篇目时,对于最为重要的、最能反映庄子思想理论的内七篇只字不提。
总之,这一时期《庄子》思想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开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汉世虽然内忧外患不断,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完整、一统、稳定的时代,整个社会按照既定的秩序运行,士大夫也遵循学/行(学,主要指儒学;行,指德行)而优则仕的规则演绎自己的人生,他们对于社会及其统治秩序大体是认同的,因此,无暇亦无意旁骛;二是因为汉代一统天下之后,其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其统治,而对于统治者而言,黄老思想、儒家礼治、法家法治思想都是可以选择的统治术,《庄子》主要讲个人的解脱之路,于政治只有“无为”一道,而其无为的思想主张最终回到远古没有统治者、统治术的时代,这与千方百计要维护、完善君主集权的汉代政治是背道而驰的。一心要为帝王之师、尽忠于现实政权的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将《庄子》纳入到自己的对策中来,更遑论那些只想着以学问进官阶而没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庸碌之士了——这都造成这一时期庄学的沉寂。
庄学的复兴当始于东汉中后期。有学者认为,庄学的复兴是魏晋之际的事,如李建中先生云:“包括《庄子》人格理论在内的庄学的第一次复兴,发生在魏晋时期。”李建中:《〈庄子〉人格理想与魏晋文学的人格起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有人甚至视庄学复兴为魏晋之际思想文化的突变,他们以惊异的目光看待这次复兴,闻一多就曾以诗人的激情描述这次“复兴”:“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没有注意到庄学复兴自东汉中后期就已经悄悄发生了。这在当时的史书中多有记载:
《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帝令三公整顿吏治的诏书中说:“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日计、月计”出于《庄子·庚桑楚》:“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
《后汉书·崔骃列传》载,崔骃专心学术而不急于仕进,时人不以为然,作《达旨》加以解释。《达旨》提到“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识”。“大庭”、“赫胥”是《庄子》所说的上古帝王称号,《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轩辕氏、赫胥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后汉书·周盘列传》载,周盘向友人解说自己不出仕的原因时提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这“支父”是《庄子·让王》中人物。
《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融以非其所好,不应命,后来社会动乱,米谷踊贵,马融陷入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左手……愚夫不为”,也见于《韩诗外传》、《淮南子》,马叙伦认为本出于《庄子》,见《庄子佚文》马叙伦《庄子义证》末附,(上海)商务印书绾1930年版。
《后汉书·李固列传》载,梁商以皇后父亲身份执掌国政,李固劝他在功成以后及时退权,不要像有些外戚那样贪恋权势,李固的话中提到:“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伯成之高”,典故出于《庄子·天地》。
《后汉书·文苑列传》载,刘梁,桓帝时除北新城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畏垒,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庚桑楚故事,出于《庄子·庚桑楚》。
《后汉书·文苑传》载,赵壹曾作《刺世疾邪赋》,其中有:“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字句,这是用的《庄子·列御寇》中的典故。
《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法诫》,其中说到:“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这里“左手右手”典故,亦来自《庄子》佚文。
以上所举,并没有囊括现有资料中东汉时人引用《庄子》的全部事例。较之西汉,读过《庄子》并受其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从社会身份看,包括帝王将相、下层官吏、隐士等,及于社会多个阶层;从引用者对材料的态度、引用之目的看,有的用于安邦治民,有的用于律己,有的用以待人,有的用以著书立说晓谕世人。由此可见,东汉之世,《庄子》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宽,指向越来越多,渗入社会生活的程度已相当深。
但是,这时期的《庄子》接受仍然只是出于个人志趣的相投,还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甚至在知识界也未为主流。而且,这时期的庄学往往与道教仙学、养生学联系在一起,在士人的思想世界中尚未取得独当一面的地位。
庄学的全面复兴当在魏晋,尤其是正始之后,以至有的学者称这时期“《庄子》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说如果将先秦两汉时期《庄子》的流传比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状态,那么从此之后,《庄子》的传播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的确,魏晋是一个钟情《庄子》的时代。《庄子》研读之风盛行,其时人三日不读《老》、《庄》,则觉舌本间强。据统计,在《晋书》460余位文人的传记中,明确表明与《庄子》有关的就有56人,占12%左右。而且,这一时期《庄子》接受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庄子终于摆脱对老子、对道教的依附地位,一变“老庄”为“《庄》《老》”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汉魏道家的发展轨迹:黄老—老庄—庄老。这时期文献资料中往往是庄老连称,而庄在前。
翻阅史书,可见其中所记某人如何青睐《庄子》之处不胜枚举,即以《晋书》为例:
其《王济传》云:“少有逸才……善《易》及《庄》《老》。”
又《山涛传》云:“介然不群,性好《庄》《老》。”
又《王衍王澄等传论》云:“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显列,顾漆园(即庄子)而高视。”
又《阮籍传》云:“博览群籍,尤好《庄》《老》。”
又《嵇康传》云:“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又《向秀传》云:“雅好老庄之学。”
又《庾峻传》云:“时重《庄》《老》而轻经史。”等等。
由此可见一时之风气。这种风气甚至及于小儿,《世说新语·言语》所记孙放兄弟事即是明证。当然,其时也并非没有不重《庄子》之人,例如范宣就曾自言不读《庄子》,但是他并不讳言“小时尝一览”(《儒林传》)。王坦之倡言废庄,其《废庄论》却透露出其烂熟《庄子》的信息。因此,梁启超云“要而论之,当时实道家言独占之时代也”,“乃至父兄之劝诫,师友之讲求,莫不以推究老庄为第一事业”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9、75页。
《庄子》是这时期“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闻一多)。有时候,玄谈就围绕《庄子》的注解或文旨的理解问题而展开,《世说新语·文学》明确记载魏晋清谈所涉及的《庄子》篇目就有《逍遥游》、《齐物论》、《渔父》等。一些著名的玄谈论题直接或间接取自《庄子》,如言意之辨、有无之辨、形神之辨、自然与名教之辨、圣人有情无情论等等。对于清谈者来说,不学《庄》则无以言。而有人不读《庄》却也谈《庄》,谓庄子“了不异人意” 《世说新语·文学》载庾语。可见庄子思想与其时士人精神之相契。
此外,这时期注《庄》论《庄》之风也蔚为大观,《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者数十家”,《晋书·郭象传》也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这数十家《庄》注名录已残缺,有明确记载的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录的六家:
崔《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晋议郎。《内篇》七,《外篇》二十。
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为《音》三卷。
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绍统,河内人,晋秘书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
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内人,晋太傅主簿。《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为《音》三卷。
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真,颍川襄城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为《音》一卷。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详何人。
这时期的论庄之作有阮籍的《达庄论》,嵇康、向秀的《养生论》和《难养生论》,王坦之的《废庄论》等等。
老庄思想风靡天下,道家思想成为社会意识之主流,势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作风和道德实践。除知识阶层研读、谈论、注释《庄子》之外,《庄子》还以多种形式深入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晋书·嵇含传》引含《吊庄周图文》云:“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今人吕思勉亦曰:“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4-1385页。可见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之风遍被大江南北,为社会各界所接受。
§§§第二节汉魏庄学复兴的原因
庄学在汉魏之际复兴的原因较为复杂。以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几个误区。一是关于庄学与魏晋玄学的关系问题。本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庄子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内容、骨架、构成部分和经典文本,这在颜之推谓《庄》、《老》、《周易》为“三玄”的提法中就已有表现。今人汤用彤、汤一介等研究者关于魏晋玄学本质的论述中均对此有所反映汤一介先生认为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参见其:《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王晓毅先生在其专门论述魏晋玄学形成的著作中,也明确指出了老庄道家是魏晋玄学的构成因素参见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版。但有的学者在论述魏晋庄学兴盛的原因时,又将其归为魏晋玄学的影响,这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笔者认为,魏晋玄学是接受了庄学的因素而形成的,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部分。玄学从宇宙本体、终极的角度为现实政治人生寻找依据这一点看似与汉代的天人之学相同,其实不然。汉代天人之学,其实是将人世秩序投射至天,再为了神化、权威化这种秩序,而说成是天启示人,人效仿天。如冯友兰先生论董仲舒云:“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转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1998年版,第66-67页。)而庄学、玄学的天人之学,是建立在对宇宙时空的比较冷静、客观的观察基础上的,是真正由天到人。《庄子》一书恰好符合这种思路,或者确切地说是《庄子》启发了这种思路,因而被玄学视为经典文本。而且,魏晋玄学的发展嬗变也大都是围绕着《庄子》解读而展开的关于这一点,李建中先生概括得很好,他说:“先是‘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文心雕龙·论说》),继之有向秀注《庄子》内外篇,‘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向秀传》)。从何、王之学贵‘无为’,到竹林诸贤崇‘自然’,再到郭象调和‘有’与‘无’、‘自然’与‘名教’之关系,魏晋玄学的发生与演进紧紧围绕着对《庄子》的解读而展开。”见其论文《〈庄子〉人格理想与魏晋文学的人格起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玄学讨论的热烈之势,也推动了庄学自身的发展。
与这一问题相似,有的学者认为此期庄学的复兴是因为庄子精神与“魏晋风度”有着某种契合。这同样是颠倒了本末。我们认为是庄子思想影响了魏晋士人,才熔铸成了所谓魏晋风度。
庄子思想是魏晋思想文化构成的因子,因此,我们探讨其兴起的原因时就不能单纯采取上述思路,即从魏晋思想内部来寻找,而必须同时从外在的社会政治状况、取士制度、学术走向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