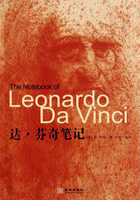首先即是赋序中提到的作赋时间问题。研究者注意到了序中“黄初三年朝京师”之说与史载陈思王、任城王等黄初四年朝京师的史实相左。“四年”作“三年”恐怕不是笔误,而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要真言,却故作假语。这是典型的寓言、小说笔法。”
尽管不可摆脱人神永隔的命运,这一场相遇到底在她心中留下了太深的痕迹,爱与恨都还在心里,因此,女娲清歌。傅正谷先生在其文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洛神赋》创作的时间,该序称系‘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据考证,实为黄初四年,因曹植‘朝京师’(洛阳) ,是在此年。那么,又何以言‘三年’?‘朝京师’这类大事作者是不可能记错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似乎作者有意不写真实年代,以表明所写的是寓言而不是事实。”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2期。但遗憾的是,傅先生只把这个寓意当成“梦幻”而没有揭示背后的寓意。
与此相关的还有赋序中提到的作赋缘起,即“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这其实也是作者施用的一个障眼法:《洛神赋》不过是借用了宋玉《神女赋》以神女说事的讲故事的模式,两者的思想情感并无根本的联系。学界一般都认为宋玉《神女赋》以巫山神女为原型,描写了一场人神之恋。后世文学创作中,也多引“高唐”、“神女”以喻男女之事。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赋序感神女事而作赋的自述是一种有意的误导——作者还是怕自己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怨恨会被人窥探了去,嬉戏游玩,从而试图将读者的思路往神女、爱情等方面引。从后人研读情况看,作者的目的达到了。钱钟书云:“植之辞赋,《洛神》最著,虽有善言,尚是追逐宋玉车后尘……”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卮言”是怎样影响到了《洛神赋》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叙述过程中角色的跳跃与转换使得文本呈现出扑朔迷离的面貌,引来读者对于主旨等问题的诸多争辩。而如果我们能把握文本“卮言”的特点,就能不为其惝恍迷离所迷惑。
结语
因为与汉晋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士人深层心理需要相契合,《庄子》深深地融入了当时士人的思想、心态及行为方式中,也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本书即描述了汉晋文学接受《庄子》的大致状况,尤其对汉晋文学与《庄子》在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的建构及叙述方式上的深层联系进行了专题式研究。
研究过程中,笔者感觉到《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时的一个主要兴奋点,这是因为,终汉晋之世,社会危机四伏,人的生命时刻遭受威胁,人们对于死亡问题,对于自身生命问题自然更为敏感,更为忧虑,好不和谐,更加渴望找寻一个能寄托其自由理想、生命精神的所在。《庄子》关于宇宙、生命的思考,对于理想人生境界的建构正符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需要,给了他们莫大的启示,因而能在他们的生命及记录生命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迹。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指出:“历史是对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事物的记录。”艾伦·阿克赛尔罗德:《历史学家箴言录》,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庄子》在汉晋时期被接受的过程,正是这样一种“值得关注的事物”被记录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场相遇中,“于是,洛神经历了希望-失望-绝望的心路历程,最后虽然是不得已绝望而去,但依然充满了缠绵和不舍。联系该赋写作的背景,我们不难得出“人神相会”即取自曹植刚刚结束的那一场 “君臣之会”(也即“兄弟之会”)的结论,同样的充满变故,同样地有怀疑和猜忌,同样的令人心伤,而曹植也和“洛神”一样满是真诚、满是热情、满是希望,又同样的承受打击、承受失望,满是凄凄的哀怨,哀怨之余,还满是缠绵与执著。因此,笔者认为,洛神乃曹植自喻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我们的目光不应只在所谓“君臣大义”上打转,与其说曹植是为了作“道德”的表白,还不如说他是借洛神抒发生活中郁积而不得发的情感。而文中对于洛神形象的极尽能事的描绘,与其说是出于对真人原型的摹写,还不如说是作者怀着自恋式的热情在描绘理想的自我形象。这一点,与屈子亦是有着相似之处的,《离骚》中,屈子一有机会就不遗余力地描写抒情主人公“我”是如何如何地修洁、美好。这种“自恋”其实都反映出失志之人的自伤和自怜。至于人神相遇故事中的“我”,好不热闹!相较之下,虚伪、畏缩、猜忌,带着“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的阴暗心理,周明先生也认为:“其实,赋的中部的‘余‘是个多疑、自私、绝情、背义的人物”,他断定这个“余”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曹植,“曹植也不会把自己写得如此卑劣”周明: 《怨与恋的情结——〈洛神赋〉寓意解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我”不是曹植,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理想的“爱人”形象,而曹植却仍然对他爱恨交加,甚至爱的成分还远远占据上风。那么,这个“我”究竟何所指?联系曹植后期生活中对于当权者近乎病态的爱恋与哀怨,我们当不难得出结论。
由布克哈特的论断我们还可以生发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各个不同时代对于同一个“值得关注的事物”的记录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正可以作为研究各个时代不同特征的一个入口。因此,我们讨论汉晋时期的《庄子》接受时,也注意到了具体各时期《庄子》接受的不同特点,借此来观照各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和文学上的特征。于是,越北沚,过南冈。
《庄子》对于汉晋文人思想行为的渗透是全方位的,文学领域中的《庄子》接受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本书选择了“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叙述方式”几个问题来进行探讨,希望能窥一斑而见全豹。
汉晋士人选择《庄子》而改变了人生和文学的面貌,《庄子》思想又因为这种选择和接受而获得了再阐释的机缘。是汉晋士人选择了《庄子》来演绎自己的人生,还是《庄子》选择了汉晋士人来演绎自身的思想,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常有不知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这样的惝恍迷离之感。
主要参考文献及引用书目
先秦宋玉风赋 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腾猿得枳棘枳句之间,振动悼栗。
语词
又曰空阅来风,桐乳致巢,命俦啸侣,此以其能苦其性者。
意象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语词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
语词
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孔子谓盗跖曰:“将军齿如齐贝。”
语词
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蓬头突鬓。?
语词
汉邹阳于狱上书自明一首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申徒狄諌而不听,负石自投河。
典故
贾谊鵩鸟赋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思想
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
典故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子黎曰:“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庄子曰: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为生,散为死。
念及此,洛神不禁“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良会永绝,“一逝而异乡”,多情的神女临别时还无忘以明珰相赠:“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说完,洛神就消逝了,“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一个人神相遇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惆怅。
思想
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
思想
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假于异物,川后静波,托于同体。
思想
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思想
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贪生失理。
思想
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不肖繋俗。
思想
至人遗物兮,独与道拘。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孔子谓老聃曰:“形体若槁木,似遗物而立于独也。”
思想
眞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道德之至也。
思想
仲尼问于颜回曰:“何谓坐忘?”回曰:“堕支体,黜聦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思想
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
思想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思想
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老聃曰:“其居也渊而静,其唯人心乎?”
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次指出的是,《庄子》“卮言”更多的是随兴而走,出乎天机,而《洛神赋》的“卮言”恐怕主要是为了避祸——虽说赋文的写作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但是,在君权政治的社会中,个人不过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固定好位置的零件,并没有真正自由的权力,包括自由写作的权力。更遑论曹植当时的处境是受人如防贼般的防备,他的生存状态没有人在意,他的言行举止却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中。因此,冯夷鸣鼓,纵有千种仇怨,他也不敢直接抒发。更何况曹植终其一生都空怀抱负不放,对于曹丕、曹睿父子敌意的猜忌,他宁可相信是小人挑拨所致,因此,他总希望能有真正的沟通,希望有一天君王能真正明白他的心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曹植是热切的,又是软弱的,他不敢反抗,甚至没有要反抗的念头,他是怯懦的,求生避祸的念头紧紧地攫着他的心。这都使得他心中的愁怨只能以一种幽隐的方式表现出来。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洛神赋》要设计这样一个讲故事的结构:曹植深知这种直指君王的怨恨不能明示,但又郁积于中,不得不发,因此,作此依托之言,而且还力图隐蔽,以免被人察觉。于是他要说明,自己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故事,不必当真。
思想
不以生故自寳兮,养空而浮。泛若不繋之舟,屏翳收风,虚而遨游。
思想
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苑风曰:“愿闻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也。”
思想
圣人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故无物累。
思想
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揭竿求诸海也。
语词
天下云?而响应,嬴粮而景从。今使民曰某所有贤者,嬴粮而趣之。
意象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庄子曰:“大树其絜百围。”
语词
吊屈原文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濳以自珍。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
意象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弟子谓庚桑楚曰: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也。
意象
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庚桑楚谓弟子曰: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
意象
枚乘七发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巳,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瞿鹊子问长梧子曰:“夫子以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腾文鱼以警乘,离去之时,洛灵还不免“纡素领,回清扬”,回头眷顾,又恨又怨,“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自莫当”,盛年难再,这样的相逢今生恐亦难再有,可恨人神毕竟道殊,终不能相遂成欢。”
语词
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异鹊感周之颡也。
而同时期创作的《赠白马王彪》序文中有“意甚毒之”一句,汉女相携,一个“毒”字可见怨恨之深。但该文却同样未有直接指向君王的语句。明了这一点,则《洛神赋》中的其他一些疑问也可砉然而解。
语词
白刃硙硙,矛?交错。孔子曰:“白刃交前,视死若生者,这一场与“人”的交接使洛神感到了心伤和孤独。这时众灵陆续而还,烈士之勇也。”
语词
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出于崖涘。
语词
于是澡槩胷中,洒练五藏。愁其五藏也。
语词
涊然汗出,霍然病巳。泚然汗出。
语词
枚乘上书谏吴王人性有畏其景而恶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阴而止,景灭迹絶。渔父曰:“人有畏景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逾数而迹疾而景不离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景静处以息迹愚亦甚矣。”
典故
夫十围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橡樟初生,可抓而絶。
典故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且夫淸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伯乐曰:“我善调马,前有饰橛,而后鞭?之威。”
语词
上林赋绰约绰约若处子
语词
长门赋惕寐觉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君惝然若有亡。
意象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广成子谓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语词
难蜀父老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腠胝无胈,肤不生毛。”然而,还是免不了犹豫踌躇,欲去而不忍,欲留而不能,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动无常则,若危若安。两袒女浣于白水之上者,二妃相从,禹过之而趋曰:“治天下柰何?”女曰:“股无胈,胫不生毛,颜色烈冻,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神相遇故事中的“我”与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载云车之容裔。在前后故事框架的叙述中,“我”是指曹植,而故事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洛神”才是曹植。也就是说,文章的叙述出现了跳跃,呈现出“双重叙述”的特征,故事叙述者的叙述与故事中抒情主人公的叙述交替进行:于前者而言,只是讲述了一个人神相遇的故事;于后者而言,则是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洛灵不禁感叹自己的孤独就如“匏瓜之无皮”、“牵牛独处”。她终于决定要离去了,抒发了郁积之情感。周明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赋的中部搞了人称换位,以洛神自喻,向‘君王’(曹丕)寄心,抒发了怨与恋的复杂感情”周明:《怨与恋的情结——〈洛神赋〉寓意解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但我们认为“人称换位”的说法不足以概括《洛神赋》在结构上的特征。如果联系我们在前文对于《庄子》“卮言”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洛神赋》的叙述正采取了“卮言”的方式,叙述的跳跃、人称的转换都在似乎无心的状态下完成,难以为读者所察觉。
典故
封禅文而后陵迟衰微,千载亡声,岂不善始善终哉。善始善终,人犹効之。
语词
东方朔答客难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魏牟谓公孙龙曰:“乃规规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
意象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一首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鲁哀公问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
意象思想
庚桑子曰:“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不知所如往。”
王褒洞箫赋于是般匠施巧,?襄准法。匠石之齐,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见栎社树,匠伯不顾。
语词
嚚顽朱均惕复慧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施及三王,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鬻夏育也。
典故
薄索合沓,罔象相求。黄帝游赤水之北,遗其亥珠,象罔求之而得。
典故
四子讲德论并序也夫蚊蝱终日经营,不能越阶序,附骥尾则渉千里,攀鸿翮则翔四海。
蚊蝱噆肤语词
行潦暴集,江海不以为多;鳅鳝并逃,九罭不以为虚。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百川归之而不盈。
意象
恩及飞鸟,惠加走兽。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至德之世,禽兽成羣,草木遂长。
思想
圣主得贤臣颂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徳之至。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