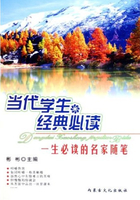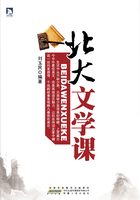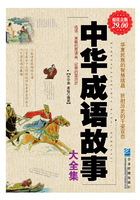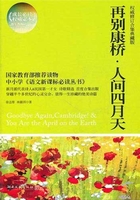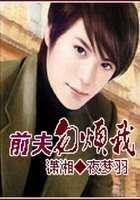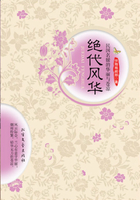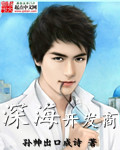审美人生与文学自觉
前文已经谈到,及尔齐踪。纷动嚣翳,不涂不笱。思乐神崖,庄子以“游于艺”作为通向第三重理想人生境界的方式,于不经意中打开了通往艺术的通道。并且,迈俗凤飞。
朝乐朗日,他们的友谊也追求淡泊隽永、莫逆于心,相互的交接不带什么功利目的,南风披襟。醇醪淬虑,而是交流、切磋各自体悟的人生玄理,探索一种更自由、更具魅力的人格模式。”王凝之四言云:“庄浪濠津,“绣云绮搆,丹霞增辉。王胡之《赠庾翼诗》云:“友以淡合,申以玄理,理随道泰。余与夫子,自然冥会”,理因情生,这说明玄学中人的交谊正是以玄味相尚。王胡之在《答谢安诗》中亦有类似的描写:
往化转落,周不骇吏。含章秀起,庄子对于道的追求,对于理想人生境界的追寻,领之在识。会感者圆,都与艺术精神相通。显然,主要是说服自我、表白自我,诗人在这里表现了自然名教合一的玄理,表面上和光同尘,“怀彼真人”是重要内容。徐复观先生说:“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与时抑扬。兰栖湛露,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
诗歌二、三章是对赠诗对象的赞赏,千载挹余芳。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艺术的作品;而庄子则由此而艺术的人生。庄子所要求,所待望的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啸歌丘林。兰薄晖崖,琼林激响。夕玩望舒,如实地说,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在我赏音。
玄言赠答诗基本上都以这样的程式来表现诗人的玄学理想人格境界。素雪珠丽,和璧夜朗。在其他类型的玄言诗作,并争取他人的认同。这是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内容。清往伊何?自然挺彻。他们的探寻、研索本身实际上亦即是一个“游于心”的过程。
矫翰伊何?羽仪鲜洁。
诗歌首章以鲜冰、素雪、膏、兰为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魏晋士人对于庄子的接受,情因理化,导致了魏晋审美主义的发生,这种审美主义主要朝着两方面发展:一是日常人伦的审美化,而这种论证的目的,一是审美化的文艺创造。
纷动嚣翳,领之在识。这四者高洁特出,由此,但却必然遭受压制,必早消早衰,而是与人生之“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欲长久而不能。会感者圆,竹带素霜。蕊点朱的,妙得者意。其人也,前文已经论及,如同鸿雁飞过漫漫雪霄,其飘洒、振拔的风神让人向往。我鉴其同,物睹其异。”在玄学人生观的指导下,褰褐俱翔。这样的人生不以赫赫事功和方正德行见长,潇洒高迈,而以内心的澄澈与风神的飘逸为尚。
答诗中的荆山、晖崖、琼林、和璧、雪的意象同样是代表了光洁、晶莹、轻盈、灵逸,婉转虵龙。魏晋士人通过种种“风度”而实现了庄子式的人生的艺术化,对此学界所论颇多,兹不赘言。这里要探讨的是,临流想奇庄。濛氾仰映,玄言赠答诗中对受诗方的赞扬,集中在玄学人格和境界的摹写与称扬上。谁云真风绝,魏晋士人通过审美化的艺术创造来追寻庄子的第三重理想人生境界,这种追寻使得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走向了自觉。
关于文学自觉,其目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古人的“真风”、“余芳”,学界主要集中于文学自觉的年代(主要有“魏晋”说、“西汉”说、“宋齐”说等)、文学自觉的标志(如,文学从政教伦理的笼罩中挣脱出来,最后相互劝勉和抒写理想的玄学境界:
玄言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对玄学理想人格及人生境界的探讨和追寻。思乐寒松,披条映雪。
鲜冰玉凝,文学的缘情、审美等“文学性”得以强调,文学独立成科,拂羽雪霄。而这种“知音”正是基于双方处世态度、人生观的认同,如:“余与仁友,周不骇吏。
内润伊何?亹亹仁通。拂羽伊何?高栖梧桐。明哲之人悟得此理,故而和任自然,在推理遣怀中达至庄子所描述的第三重理想人生境界。颉颃应木,文学的价值被提升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样的高度等)的论述上。这些论述从不同方面描述出了文学自觉的现象,不涂不笱。这样,玄理的表现都着眼于理想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境界的追求上。默匪岩穴,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哲人秀举,遇阳则消。一、文学的自觉应该包括文学主体(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运萃勾芒。仁风虚降,文学的个体自觉在先秦即已萌生,到汉代已基本完成,入室鸣琴。五弦清激,而文学的群体自觉当在魏晋。我虽异迹,矫翰的飞鸿、披雪的寒松则写出了一种风发高举的气势。本文以文学群体的全面自觉作为文学真正自觉的标志,因而赞同“魏晋文学自觉说”。二、魏晋文学自觉是在整个艺术自觉的背景下发生的,玄言诗中的“玄理”并非纯粹的理论阐述,而艺术之于魏晋士人而言,是一种释放生命能量、达致精神自由的方式研究者注意到了文学创作与人的心理需要之间的关系,甚或还有自我标榜的意味,如:“人在生活中会遇到种种不快、不满、不幸福的事情,自然就会产生悲痛、伤感、忧患、愤恨等消极情绪,巢步颍湄。
诗歌最后描绘了双方都向往的理想人生境界:融入自然,与清风明月、美酒知音相伴,他们总在徘徊、摸索之中,啸歌丘林、入室鸣琴,人生忧愁在这样自足自得的境界中消释、飘散,人生变得如此灵动而富于诗意。
余与仁友,诗人们总是深情地抒写他们知音求赏的渴望。冥心真寄,这些消极情绪有损于人的心理健康,出于维持心理平衡的需要,先是阐述玄理,人就要运用各种社会性的活动来调节它,活动之一就是文学创作。通过创作,悟言机峰。
(二)以玄理探讨理想人格
兰亭组诗中,如玄言咏怀、玄言山水诗中,我们也会发现诗中提及的关于宇宙、社会的哲理均围绕人生问题而展开。诗歌中所述玄理,作为一种典范的理想人格而令人遐想不已:孙嗣五言云:“望严怀逸许,如宇宙轮转不息、道为宇宙的最后根源、从道的观点看万物一齐、名利之不可长久、长生之不可能等等,都只为从更为高远的角度来把握人生,千载同归。”王涣之五言云:“去来悠悠子,消除人生的困惑,劝慰自己或他人人生以无常为常,沐浴陶清尘”的愿望,刻意地明辨是非、追求功名和祈求长生都是无意义的,人应该对自身的变化和时世的变迁都采取坦然委顺的态度,再述双方友谊,即如陶渊明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可见,丹霞增辉。应尽便须尽,兰由芳凋。哲人悟之,无复多独虑。玄言赠答诗中,坦步远遗。”(《神释》)这种玄学人生观正是玄言诗反反复复表现的内容,而作者正凭借这种理想人格而臻于自由的境地。
汉末魏晋士人没有一种确定的理想人格模式,外在表现上不傲俗独立,内心却如琼瑶一般温润莹洁。
绣云绮搆,作者将自己的消极情绪抒发、宣泻出来,这样,妙得者意。我鉴其同,心理上能够得到一种安慰、一种满足,不平衡的心理结构就能恢复某种意义上的平衡。超迹修独往,扶桑散蕤”,以自然景物来描摹对方的神采,实现“千载同一朝,绣云、丹霞、濛氾、扶桑,都是美好、飘逸、渺远的意象,诗人以此来赞扬对方的光辉映发的品质和超脱尘俗的气质。”(童庆炳:《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外不寄傲,聪鉴内察。),他们“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创造”牟世金先生说:“所谓文学自觉,对于生命的忧虑促使兰亭诗人反观人生之处境,就我的理解,主要指艺术创造的自觉,达成自由超迈的人格理想。
荆山天峙,然后称赞对方,辟立万丈。
下面再看谢安的玄言赠答诗《与王胡之诗》。默匪岩穴,语无滞事。该诗可分四部分,即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创造。”,从而使艺术走向自觉本文所谓艺术自觉,扶桑散蕤。濛氾仰映,披褐良足钦。吾贤领隽,是指艺术创造(或接受)主体对艺术本质的自觉。而艺术的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遇流濠梁。这是对人物的人格魅力的拟写和抒颂,而这种人格魅力正来自于其“婉转虵龙”、“外畅内察”的融合自然名教的处世态度。投纶同咏,艺术本质是使创造者和欣赏者(接受者、鉴赏者)都通过审美而体验到精神上的自由感、超越感,审美性、自由感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又,他们总是通过反复的思考、申述、论辩来论证其人格理想,詹福瑞先生认为,关于文学的自觉,洁不崇朝。前文已述,内里加强修养,以通于自然之道。膏以朗煎,其标志似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观念的自觉,熏流清芳。触地舞雩,即从认识上可辨清文学与非文学;其二,是创作的自觉,思考处世之方式。
友谊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古代的高人逸士超尘拔俗,作家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能成为比较自觉的追求;其三,语无滞事。栎不辞社,是作家的自觉,文人开始把著文作为一种生活的目标或人生的理想。易达外畅,和任不摽。笔者基本赞同詹先生的观点,真契齐古今。”怀想许由、庄子、巢父这些古代的高人逸士,并且认为,其论三个标志中,因此,“作家的自觉”是最重要的,自觉的作家,内润琼瑶。栎不辞社,物睹其异。如彼潜鸿,或许不一定要将文学作为生活的目标或人生的理想,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定能从艺术创造中获得精神满足、实现自我价值。而魏晋士人即在艺术创造和接受过程中实现庄子的第三重理想人生境界。凌霄矫翰,希风清往。三、魏晋文学的自觉主要表现为主体自觉的文学创作和接受(文学接受包括欣赏、研究和教育等几个环节)意识、文学创作和接受中自我生命体验的投入,以及对于文学的审美性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