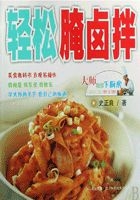一些研究者没有看到庄子人生哲学有层次之分,他们总想用一个词语,如某某主义来给庄子思想贴上标签,如有人说庄子哲学是混世主义、滑头主义、阿Q精神的;也有人说庄子哲学是避世主义或逃世主义的;有人说庄子哲学是超世主义的;还有人认为庄子哲学是美学,或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由于学界对庄子的理想人生境界的探讨总是围绕“逍遥游”思想而展开,因此关于“逍遥游”的含义,又是众说纷纭。而笔者在仔细检索以往的研究资料时发现,尽管这方面的争论很是热烈,但真正的交锋却并不多,观点之间真正的对立就更少了,这主要是因为大家的讨论很多时候不在同一层面进行,所谓讨论,大多是自说自话。而正是这种自说自话,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阐发了庄子的人生思想和“逍遥游”的含义,这为我们全面把握庄子的人生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另一方面,已经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庄子人生理想的层次感。如孙明君先生认为:“庄子哲学是一种自然人生哲学,此一哲学体系涵摄三大人格境界:一是理想人格境界,又称真人境界;二是隐士境界;三是士大夫境界。”孙明君:《庄子哲学中的三重人格境界》,《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康中乾先生也在其《庄子人生哲学三境界论——〈逍遥游〉主旨试析》一文中将庄子的人生哲学分为:绝对精神自由的超世主义,理性认识的处世主义,服从现实的顺世主义;对应的三种“逍遥游”:一是主体精神的价值之游;二是理性认识的认识之游,三是肉体之躯的现实之游文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 。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的划分方法,如孙先生划分就有问题,他所说第二、三重境界不管是人格主体(即隐士和士大夫隐士相对于仕宦之士而言,都同为“士”。按孙先生的思想,其实分作隐士和仕士更合适。)还是人格境界(顺世而不失于天)都没有根本的区别,而这三种人格境界其实都是理想中的而非现实的人格境界(关于庄子的现实人格,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他们这种思考的方向是可取的。本文即循着这种思路来考索庄子的理想人生境界。
一游于方外
这是庄子的最高理想境界,臻于这个境界,就能物物而不物于物,能游于六合之外,能获得精神和形体的全面自由。
第一,物物而不物于物。
在得道之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上,以上所提到的得道之人“无需凭借外物”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庄子》明确地说他们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还需“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等等,也是离不开外物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逍遥游》)研究者多以这段话来说明大鹏高举需凭借厚风,因而大鹏是不自由的。岂不知大鹏能至大境界,正在于它能积厚风,能物物耳。而小鸟则为物为己所限定,是“物于物”也。至人之所以能至于无穷,也正是因为它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物物而不物于物。
得道的、绝对自由的境界是物物而不物于物、无所拘束的,这在《庄子》其他篇目中也有反映。《山木》篇云:“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昔,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物物而不物于物,则故可得而累邪!”
第二,游于无穷。
庄子的第一重人生境界承载了庄子的最高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理念化的产物,是庄子根据其对“道”和宇宙时空的理解提出来的,带有浓重的理念化色彩。这一重人生境界也不是在六合之内的。《逍遥游》中的得道者是“游于无穷”。对《逍遥游》主旨持精神自由说的研究者认为“游于无穷”是指游于“精神境界”。其实不然,这里的“无穷”当是指六合之外的境地,即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定,这正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境地。
较之世俗人生,这种境界是高远而超拔的。但六合之外是怎样的,庄子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在这里,庄子其实遭遇了表达的困境。绝对自由的境地是方外、六合之外、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无穷,如: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应帝王》)
庄子思想中道的境界是超时空的存在,但他却只能借助于已有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想象和表达,山和野都是我们熟悉的空间,只是庄子用“无”的方法将其模糊化了,使得我们想象不出空同之山、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的真实面目,只是一片氤氲混沌萦绕脑海。这些模糊的词语表现的是庄子理念中模糊的境界,由于缺乏现实体验作基础,庄子的表述就只能停留在这个模糊的阶段。
第三,精神和形体的全面自由。
臻于道的境地,则不仅主体精神自由无碍,形体亦可不受时空限定,可乘云气,御飞龙,游于九天之外,更可忘年忘义,振于无竟: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大宗师》)
闻道之人,年龄的增长不会改变他们的容颜,他们永远色若处子,青春长驻。他们能游于自由自在的境地,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他们的精神充满天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田子方》)他们的形体不受拘束。《秋水》篇云:“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 《达生》篇云:“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
二游于有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庄子第一重人生境界是较为虚无缥缈的,在道教仙学产生之前,这种境界不太可能得到实践的验证,从而不具备可操作性。也许庄子自己也认为其绝对自由的理想不可实现,于是退而求相对的自由,那就是游于有间,亦即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联系上文我们对庄子自身处境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现实的夹缝中求得生命的保全和相对的自由才是庄子超越哲学的重心所在。关于“游于有间”,“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有非常生动的说明: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踦,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 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里的关键词有:无厚、游、有间、养生。首先,关于“养生”,许多研究者将其理解为保养身体,而实际上,此处的“养生”更应指保全性命,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庄子哲学的最根本出发点就是保命。因此,如何解牛,即是说在现实社会中如何保全性命,并争取生命的自由空间。从主体而言,庄子认为应该“无厚”,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无己”,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产生矛盾的时候,以消解矛盾的一方“我”来消解矛盾;从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契入而言,就是要寻找“有间”,即寻找现实社会的空隙;而“游”既是一种生存方式,又是一种人生境界,如同“逍遥游”的“游”。
在这种处世哲学中,“无厚”即“无己”,是指不带主观成见,不固定自己,也就是随机应变,这样才能利用空隙,为自己求得存身之地和周旋的条件,即“游刃于有余”。游刃于空,故无所碍。不与外物相冲突,则自己也就可以免受伤害,即所谓“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如果说,“游于无穷”是一种生命理想的话,“游于有间”的人生境界就是一种生存智慧。
“游于有间”的智慧或表现为主体自身灵活机动地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秀天年,则处其不材;雁以不能鸣而死,则处其材。
或者回复到“儿子”一样无心无己的状态,顺自然而作,《庚桑楚》篇论“卫生之经”云:
南荣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卫生之经,即养生之道。庄子认为应该像天真无邪的婴孩那样,不知所为而动,不知所之而行,完全消除了主观性、目的性,身若槁木而心若死灰,不以己为意,一切顺乎自然。这样,就无有祸福,人灾自然也就不会降临。
“游于有间”还表现为主体于现实世界中寻找一个藏身之处以免于网罟之患,且藏身越深眇越好:
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庚桑楚》)
这便是庄子的隐逸思想。关于庄子对隐逸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庄子认为隐逸行为的发生应该是为“全其形生”而隐(按:此处的“生”指“性”),也即自适其适,而非适人之适。对于适人之适而隐的所谓“隐士”,庄子是极为鄙夷的: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大宗师》)
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骈拇》)
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骈拇》)
庄子认为隐逸行为应该是出乎自我本性。若不是出乎自然本性,而是为了道义等外在的因素而隐,则必定会残生害性,这就与盗跖的残生害性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二,隐逸越深越好。这并不是说,要隐逸于深山老林、四海之外。庄子所谓藏其身“不厌深眇”,主要是指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等方式,使自我消融为零,使他人视“我”如不存在,即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果在人群中,“我”的存在还是被突显出来,则意味着藏得还不够深。因此,庚桑子居畏垒之山,畏垒之细民“洒然异之”,欲“尸而祝之”,这让庚桑子感到不安不悦,而至于深刻反省。(《庚桑楚》)而《则阳》篇中蚁丘之隐者,知道孔丘认出自己后(“知丘之着于己”),旋即离开。
总之,庄子的“隐逸”是出乎自然而非刻意,枯槁赴渊不一定是隐逸,真正的隐逸者可以“无江海而闲”。隐逸即“陆沉”,将自己沉没在现实的世界中:
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则阳》)
相较于第一重人生境界,“游于有间”的人生境界中,主体不再是无所不能地“物物”,而是尽量与物处而不为物所伤;也不再是逸出六合之外,游于无穷之境,而是游于现实的夹缝中;主体的身心也不再能自由无拘地舒展,而是倾向于自我封闭以求全身。庄子用曳尾泥涂之中的“龟”的意象来表现自己的人格选择。“龟”是长寿之物,它有着坚硬的外壳,危险来临的时候,它靠“龟缩”(即自我封闭)的方式保全自身。这个意象的选择恐怕不是随意的,可惜的是,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涂中之龟与神坛之龟在生与死、自由与不自由问题上的差别,而没有注意挖掘庄子在“龟”身上所寄托的特别的人格内涵。从以上分析来看,“龟”正可以作为庄子第二重人生境界的形象代言人,如同“鹏”可以成为第一重人生境界的代言人一样。
三游于心或游于艺
游于无穷的绝对自由和游于有间的相对自由在落实到行为层面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难度,物物而不物于物,精神和形体都超越飞举,是神人才能达到的,而“游于有间”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毕竟现实生存如同游于羿之彀中,一不留神就会遭到伤害。全身远害既不能实现,残损和死亡不可避免,则只有寄希望于虚幻的精神超越。
《庄子》书中出现了大量的畸人形象,这些人是游于羿之彀中而不幸中箭的人。但是,在庄子看来,他们虽然畸,却能赢得大众的追崇,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的奥义,这就是《庄子》所表现出来的第三层面的自由。这种自由完全是精神意识上的、是虚幻的。庄子说这些人是畸于人而侔于天,他们是掌握了大道的,因此,形体的残缺不能掩盖他们精神的完满所带来的巨大魅力,《德充符》中的兀者因无为顺道而为师,《大宗师》中的“古之真人”均奉无为,以无为者为友,他们与道同在,其人格已臻于至美的境地。他们通过对道与世界的体悟和把握化解忧愁,获得心灵愉悦。这就是庄子的第三重人生境界:游于心。
《德充符》中申徒嘉谓子产:“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所谓游于形骸之内,即指游于我心世界之中。与前文所论的朝向外部世界的“外游”不同,这里的“游”是朝向“内心世界”的“内游”。《列子·仲尼》中列子与壶丘子围绕“游”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是庄子“内游”的最好注脚:
列子好游。壶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而曰固与人异欤?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壶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视。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观矣,是我之所谓游、我之所谓观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