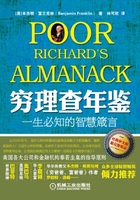由于李侗以实见天理为静坐的直接目标,而天理又分殊于生活,实见天理的见证是要在生活中见出分晓,……他认为万物统一于天理,万物的形成只是天理的变化。蒙文通认为,无论是一本之理(即天理),还是万殊之理,都是性,都是“天之所以与我者”。他说:“率性尽性之学,自子思、孟子、延平、程、朱是一致的。象山所谓于人情世事物理上用功,亦是如此。所谓洒扫应对之微,即精义入神之妙。释家说要于事上观,亦是此理。”性即理,要践形率性,即是要明物察伦,即要于日用之中进行道德践履,使形上与形下相结合。他反对把理看作佛教、道家的“空”与“无”,他说:“若把理也看成空无,非所敢知也。延平言理会分殊,阳明言感寂,是儒家正义,所谓性也。”理与性均具本体性涵义,说其形上,只是要与形下之器(物)相区别,是抽象与具体之差异,而不是空无与实有之区别。阳明所说的寂然不动是心之体,感而遂通是心之用,均就心而言,而其心即理,即性;他的心、性与延平的理一、万殊之性一样,都有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涵义,故蒙文通说“是儒家正义,是性(善)”。
由于宋明理学家有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天地之性、天命之性、血气心知之性等等说法,蒙文通对此作了评述。首先,他区分了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他说:“宋人又分气质之性、本然之性言之,然外气质又安得有本然之性。”本然之性寓于气质之中。孟子曾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为能践形”,是兼言形上与形下。蒙文通认为,如果离开了形色,则无以与本然之性相合。所以他说:“盖有物有则,则乃本然之性,性即理也,君子存之,存此理此则而已。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血气之性,物交物引之而已。心之官则思,心乃知善知恶者也,知此理此则者也。践形即率性也。”本然之性是则,是理,理不外于物,本然之性不外于气质之性,不外于形色,君子所存的就是此则、此理、此本然之性。心之官则思,心能知善知恶,能知此则、此理、此本然之性。若只靠耳目等感观,则不思此则、此理、此本然之性,则必然被物所役、为欲所诱。因此,要存心,存心才可循理,循理才能见本然之性。“循理,即血气之性皆本然之性。气机所至,即性之所至,亦即理之所至。”性与理均为本体性范畴。
其次,蒙文通分析了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他说:“义理之性是气质合当如此者,不如此便不安。”“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性,义理即从气质日益发展提高而益明。夕惕乾乾,只是要日新。颓委则昏惰而益昧。”同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的关系类似,蒙文通认为,义理之性依于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由气质之性日益发展而来;气质之性变动不止,义理之性承于气质之性,而又高于气质之性。义理之性是合“理”的,而气质之性则未必。要“从气质之性以明义理之性,此性学也。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此心宗也。理是人所认识”。蒙文通认为,通过气质之性以明义理之性,是儒家之学;不讲形色、不讲气质之性,直接谈性,则是佛学。
3.性本善却须养
在性善恶与否的问题上,蒙文通认可孟子的先天性善论。他说:“性善之理,古人都见得分明。只此一理,延平从未发处说,象山从已发处说,已发、未发,一也。”延平的理一、分殊,讲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是就体而言,是从未发处而言;陆象山混言心性,认为善是心、性共同的属性,心、性均有灵、有知,将情、性、心、才都只作“一般物事”,主张于事事物理人世上用功,主张收拾精神,“发明本心”,下刀锯鼎镬一翻工夫,是就动而言,是从已发处说。蒙文通认为,不论已发、未发,都是讲性善之理。他还说:“气无不善,心无不善,所谓性善也。‘只心存,则善不善炯然自见’。有不善未尝不知,心之本体,自无不知。”既然心体至善,具有灵明知觉功能,故不善一旦产生,心即能知之。“不知性之善,是谓外铄之学,是无源之水。若说不假修证,不免误认凡夫为即圣,以至认圣凡无别,无善无恶之说以生。阳明说愚夫愚妇生而知之,知的是什么?圣人学而知之,又是如何学?所谓识得本体好做工夫。”蒙文通认为性善是本。若不以此先天性善为本,言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所依托;若不加强心性修养,就会把凡夫当成圣人,从而认为圣人与凡夫毫无差别。实际上,“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此天之所以与我者,性善之义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养气之工也”。蒙文通认为圣人、凡夫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同具有先天的性善本体;之所以有别,则在于存心、养气的工夫有差异。圣人是“识得本体”,能时时存心以明善;凡夫则时不时让宫室妻妾之美把不屑不顾的心抑制下去,为其所诱惑,无法“识得本体”,自然不能时时存心、尽性。也就是说,恶源于后天,源于所禀气的不同。有善即有不善、有恶,善、恶是相对而言的。
蒙文通对朱熹的“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进行了评述。他说:“四端皆一性之著见,而用各不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去不善而成善者知也。朱子言仁为四端之首,而智能成终而成始。”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把孟子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比作性之四德,即仁义礼智,认为是性的不同表现,其作用也各不相同,认为仁为四端之首,而知(智、心)能改过迁善,故能成终(即达善)亦能成始(性本善)。
蒙文通赞成薛敬轩“以太极说性”的观点,认为此说“最妙,不落有无,默而识之”。他说:“有物有则,理者气之理,理传于气;气违于理而心自知之,而知传于理;知亦气之知也;三者一而已也,合而言之性也,无极而太极也。”“气也,理也,知也,合而言之性也。”性即太极,兼理、气、心于一体。
性虽先天本善,但受所禀气质的影响、物欲所蔽及后天工夫的不同,导致恶或不善的产生。蒙文通赞成明代理学家陈确“教养成就以全其性”的观点。他说:“陈乾初说:庶民皆天之所生,然教养成就以全其性者,圣人之功也。非教养成就能有加于生民之性,而非教养成就则生民之性不全。陈氏之说最为的当。”陈确不同意《大学》“知止于至善”观点,认为“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认为没有绝对不变的“至善”。他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积习,主张“气”、“才”、“性”三者不能分立。蒙文通赞同陈确注重后天工夫的观点。因为,“性者心之性”,尽心是工夫,工夫越深,则性越显,即可以知性。因此,他从扩充的意义上、从发展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知皆扩而充之;性虽善,要在扩充,始能尽性”。事物在变化,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变化,虽然人心具有先天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但仅是就本体而言,事实上,要达到那个先天的认识、那个理,尚需一个过程,即需要一段工夫。“不知良知现成,则本体不明;误认良知现成,亦是本体不明。”这就是所谓的“识得本体,好做工夫;不可只有本体,缺了工夫”。理是气之理,识理就要养气,这就是工夫。当养得浩然之气时,自然识性、知天了,因为,“浩然之气即性也”,所以,蒙文通说:“认良知本自现成,就本体说,原无不是;但就工夫说,这便是有一段养气工夫的境界;无此工夫,即无此境界,而说良知现成,则非真实而流弊生也。沈静精明,亦即性之本体,亦即我之工夫。依本体是还他本体,即是工夫,即是创造,亦是发展之所至。真理实现成,但待人放心,即非全是现成,但有物(气)的基础。”真理既现成又非现成,故认识真理是即本体即工夫,是一种扩充和创造与发展。因此,“惟养气是尽性率性之要,所谓内外交养。”“性亦在养之而已”。
蒙文通在1952年写给张表方的书柬中,说道:“文通于四、五年前,于良知本自具足、本自圆成之说,始有所疑。人之有赖于修养,由晦而明,由弱而强,犹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非易其性,特益长而益完,何可诬也。”前文提到,蒙文通曾自述五十多岁的时候,渐渐了解了陈乾初的人性论,并逐步认可。从这段话看,他已经完全赞同陈氏的“物成然后性正,人成然后性全”的观点了。后天的教养成就、道德践履,非是改变人性之本然,而是扩充其善端,使人之性更加全面、完备。他接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犹良金之在矿;圣人之不思不勉,则精金百炼、扩而充之之功也。”蒙文通以良金与精金来形容愚夫愚妇同圣人之关系,真是太妙不过:既指明了圣、凡具有相同的本然之性,又表明扩充之工夫对成为圣人的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蒙文通又认为,性无所谓善恶。他说:“耳目口鼻之于声色臭味,心之于义,皆性也。任其自然,皆是天则,即此本色,本自无恶,何须有善。”既然“性乃天之所以与我者”,是气之性,而“气之流行,本无善无不善,只本体之自然而已,即此是本来面目”,故“率性是直做前去,何计善不善”。“人生而静,即《易》之寂然不动,《中庸》之无声无臭,所谓性也。一性而已,还言什么善恶;言性善是不得已事,况言恶乎?存久自明,是从发展上说(见),所谓尽心、知性、知天也”。不论是《乐记》以“人生而静”言性,《易》以“寂然不动”言性,《中庸》以“无声无臭”言性,都是就未发之性而言。性即是本来面目,无所谓善恶;说性善主要是为了给天地立本,因此是不得已之事。程颢说“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是说人心只要保持内在的实践工夫,久而久之,你就会识得“仁”本体,从而与天地相通。蒙文通在此借用“存久自明”是要强调:性的被认识,是通过持久的扩充善端的实践工夫而完成的,也就是从扩充意义上说,从发展上说。这就是蒙文通的性善却需养的观点,亦即其在晚年,侧重于孔子的性近习远之说、发展孟子性善的扩充之义观点的一个表现。
蒙文通先生在其理学著述中,涉及了诸多范畴,除本章所谈到的心、性、理、欲等以外,还有很多,如太极、无极、慎独、情、良知、意等等。这些范畴不光涉及儒学,还关涉道家道教及佛学。因为,蒙文通治学是“儒、释、道,无所不窥”。限于作者自身水平,这里暂未过多论及。
总之,通过分析蒙文通的主要理学范畴的涵义及相互关系,梳理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对蒙文通的理学思想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因而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理学思想在其儒学思想、乃至整个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比之于同时代的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学者,蒙文通在治儒学、理学的思想和方法上则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同。生活在西学传入、外敌入侵、变法革命迭兴、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中华文化面临严重挑战的动荡年代,蒙文通和熊十力、梁漱溟等人一样,看到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并致力于发掘、改造、创新儒学的“恒常之道”和“人文睿智”来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由此批判地审视儒学、理学的文化价值,维护儒学的本原性。不过,与冯友兰、贺麟等人更多地引进西方思想,侧重于融合中西、贯通古今,试图从儒学的“内圣”真正走向“外王”有所不同,蒙文通偏重于从中国固有传统中开发新知,阐述其中蕴含着的能为现实社会所用的思想,并改造创新,以经世致用、解救时艰;强调儒学,尤其是理学的“内圣”一面,并身体力行、“优游涵泳”于理学近一生。同时,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清理,在中国文化内部融通儒、释、道三教,在新形势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弘扬理学之精华与优长,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由此可见蒙文通理学思想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