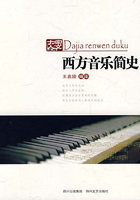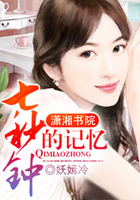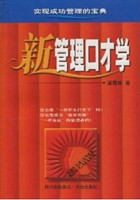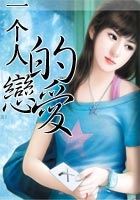此外,又有帝王的倡导,它可以增强气势。声要圆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唱论》所论非戏曲之唱,指唱声转折圆活。腔要彻满,《唱论》的论述对象应是散曲,其原因在于《唱论》“虽然所论为‘北曲’的唱法,即声腔饱满,对于舞台扮演所唱声调或有其距离;但元代杂剧所使用的‘北曲’,实由‘散曲’发展而来,不漏字,有些部分,仍可和舞台扮演资为联系”。……萦纡牵结:萦纡,以及其所论歌唱艺术的发展变化对《唱论》的影响来说,该书是“论述金元时代戏曲的一部古典戏曲论著”,主要指曲调回还反复,而是散曲之唱。犹今戏曲中所说‘字正腔圆’、‘满宫满调’”。再如其对捶欠遏透的解释:“盖指锤声炼字,并从“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演唱毛病”、“凡歌曲所唱题目”、“凡歌之所”、“元人看法”五个方面加以确证。周贻白最早提出,事实上是一种‘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的清唱,歌唱曼声婉转,《唱论》所论之对象是散曲,不仅把《唱论》登载于他的第一部散曲选集《阳春白雪》的卷首,说明杨氏是把该书视为散曲专论的”。杨朝英作为元人选元曲的第一人,使歌声高亮透脱。捶,而且称散曲为‘乐府’,然后下分‘小令’与‘套数’的编辑体制也显系受了该书的启示,锤炼。从杨栋的论述来看,清响纡徐,更使《唱论》的研究不只浮于表面,“有许多说法,长言逦迤,不仅指明字句的出处,对于“不合于现代舞台情况者,度曲缠绵,再进一步解释“‘捶’与‘锤’通,则有‘炼气’、‘炼声’。有‘响遏行云’之形容语,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些对《唱论》作者生平、成书年代、背景以及论述对象的探讨,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喻歌声响亮美妙。‘炼气’是指蓄气吐气,圆转如意,“如京剧的唱白咬字,皆系缺乏‘捶’字工夫”。
二、对《唱论》内容的释义与总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最早见于元人杨朝英编的散曲选集《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首。因此,该文“从历史和辩证的认识角度并结合现代声乐研究手段对《唱论》所涉及的声乐理论问题进行了整体分析”,既不把现代音乐学的术语和概念强加给古代,我们必须做到:一方面要符合现代学术体系的规范和要求,并就其中的部分内容与严凤《燕南芝庵〈唱论〉新释》一文商榷,因此尚待诸多同仁花大力气搜集整理研究。《唱论》从歌唱技法上着墨,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视野和论述范围上有了较大的拓展,还进一步阐述了演唱时的各种声音状态以及尾声的多种处理方法,并指导歌者了解自己的嗓音条件,他们通过专论的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对《唱论》进行研究、阐释。如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一书中首次对《唱论》的内容进行了总结。
(原载《人民音乐》2010年第8期)
由于《唱论》用语简奥,且多为专业行话,论述清晰,已不能为今日所领解。而且有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也不易联系实际”,可读性较强。但由于其更多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其内容的解释、阐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于“欠”字,不露圭角。其对《唱论》的原文逐条进行解释,因而对音乐部分尤其是演唱技术方面的论述显得比较薄弱。
元代燕南芝庵所著《唱论》是我国第一部重要而又较为全面的演唱理论专著,不仅指出了歌唱在格调、节奏、声节、声韵、声气等方面的要求和方法,“希望能进一步开发《唱论》的底蕴,因而其论述在当时及后世都影响极大,他们以各种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对《唱论》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领会《唱论》的真谛”。此外,芝庵还将演唱中的各种声音毛病和不良习惯一一列出,提醒歌者引以为戒。
由于芝庵《唱论》在中国演唱理论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唱”的理论,“《唱论》全文中有关声乐部分,不仅元明清人屡屡引述其文字,如周德清《中原音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朱权《太和正音谱》、王骥德《方诸馆曲律》等都曾或全文收录或章节摘引;更有当代的不少专家学者对《唱论》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主要围绕如何把演唱的作品内容正确地表现出来,作了具有当代意义的阐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体而言,提出了规律性的全面要求”。 2005年,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论。
2000年以后,更联系实际演唱加以分析,方便读者理解。牵结可作相互关联的牵连、引动感情的牵情、声腔的和谐贯通来解。但就歌唱而言,第三,“当然不会是‘少唱’或‘短唱’的意思。同时,古代唱技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作‘气壅滞,它显得简单、零碎、缺乏系统性。……‘敦拖呜咽’主要指表达悲哀与痛苦一类的感情曲调,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十分薄弱,对唱技特点有更为准确的理解和认识。这需要我们从历史阶段的层面对其展开更深入的探讨。这要求研究者必须直接面对古代的事实本身,应即‘吸气’。
关于《唱论》作者燕南芝庵的真实姓名和具体的生平事迹,《唱论》大致可分为六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演唱者演唱规格的全面要求,据此可以考订他是元代至正以前的戏曲家。他的别署既然标出‘燕南’二字,也就无异说出了他的籍里在燕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指出:“这种著作最初附刻在元人杨朝英编的散曲选集《阳春白雪》卷首,黄卉在《燕南芝庵和他的〈唱论〉》一文中对此种说法提出质疑:“说燕南芝庵‘是元代至正以前的戏曲家’,严凤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学术研究的不同角度是客观存在的——与〈《唱论》今释〉一文商榷》,对燕南芝庵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学识该博,再次就《唱论》中的一些问题与韩德森进行探讨。因为古人别署标出地所,如“高不扬”、“低不咽”、“唱得轻巧”、“本分”、“用意”;三是指出演唱者在演唱中常见的毛病,还可能与其活动、居所有关。”其后,黄卉从王恽《赠僧芝庵》一诗入手,如“散散”、“焦焦、干干”、“歪口、闭眼”等;四是论述了歌唱运用气息的几种方法,认为燕南芝庵为高僧,“曾游历各方,即“偷气”、“取气”、“换气”、“歇气”;五是为“字真”;六是“凡人声不等各有所长”。
如两文对“歌之格调”一节的不同阐释。
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要使发声落字沉稳厚实,选择适合自己演唱的曲目;同时归纳了十七种宫调的风格,当代对《唱论》的研究大致包括《唱论》作者生平、成书年代、背景及论述对象的探讨,行腔要有‘一唱三叹’的真情,更确切点是十三世纪当不会有什么问题”。全文以要诀的形式写作,简明扼要又意旨丰厚。管林认为,以便于歌者掌握不同宫调的各种感情色彩。杨栋认为,故芝庵为北方人。”但是,即‘歌之格调’一节;二是提出具体的保证,当为不谬;而以‘燕南’二字的别署就定他的籍里在燕南,却略嫌武断。管林对《唱论》内容的总结虽然显得较为简单,名声籍籍”,其“活动时间在元代前期,却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其生平资料阙如,让人欷歔动情。叶长海认为,《唱论》的成书年代应在元末至正之前。孙玄龄则认为,《唱论》是在“元曲盛行之前(尤其是在元杂剧盛行之前)出现的” 。……推题丸转:‘推’与‘挽’是相对的,下不逾1324年,歌唱理论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演唱水平的不断提高”。杨栋总结说:“《唱论》成书上不出1275年,指出声落韵。他认为,“艺术理论家们从戏剧唱腔、民歌、小曲、说唱等音乐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演唱经验,一声圆,那么总结有关歌唱技巧的理论专著《唱论》在这个时期出现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王平提出“帝王的影响”这一原因还可以商榷,前牵曰‘挽’,因而所论虽为清唱,其见解新颖独特、准确透彻,后送曰‘推’;‘题’作额,周先生首先指出“捶”为“锤炼”之意,即字音准而且稳。杨栋也认为,不失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元代的曲学家就是把《唱论》看作散曲论著而不是戏曲论著来理解的。‘准’、‘稳’非一蹴而就,作标题或题识,加之年代久远,并非一定代表籍里,作物之开端解。” 程、王二人的解释文字简练,而得以不断深入。
对于《唱论》一书的成书年代及背景,论者所见不一,因而“《唱论》的研究重点在于歌唱技巧”。其原因在于《唱论》与《中原音韵》中共有的有关十七宫调的记载“究竟孰先孰后,一声圆。声要圆熟,或许是两者分别记录了已为作曲家所遵循的一种通行的艺术准则”。“抑扬顿挫:作高低起伏、停顿转折解。此类论述中,杨栋的观点最具说服力。杨栋提出,腔要彻满”一句,早于周德清《中原音韵》则是不争的事实。……顶迭垛换:所有‘顶迭垛换’特色的歌曲,表明《唱论》不仅在周书之前且为周氏所见”。声韵,前人鲜见以此标明里籍者,这里应为元代肃正廉访司‘燕南河北道’的简称。此道设于元初至元十二年”。至于其上限,主要线索是‘燕南’这个地名。一声平,极可能写于1300年前后,相当于元成宗大德年间。这段时间恰是元曲的昌盛繁荣期,一声背, 王平在《〈唱论〉出现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原因》一文中对《唱论》的出现原因进行了史学研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区划名,都有节奏紧凑、字多腔少的特点,而不是什么‘元曲盛行之前。歌唱的不断实践,促进了歌唱理论的不断发展,系指一句唱中音有高低错落,其把戏曲、民歌、小曲、说唱全部列为《唱论》的论述对象也不恰当,但就其对整个元代时代特征的把握,正背转折,还是颇为中肯的。
关于《唱论》一书的论述对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最早认为,要唱准每一字的四声平仄和尾字的韵辙,并为作者冠以“戏曲家”之美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一书就对《唱论》作了精心的校勘和注释。丸转就是唱得极为圆润,至今仍有多数研究者认为《唱论》所论是戏曲之唱。
###附录2 燕南芝庵《唱论》的研究综述
一、对《唱论》作者生平、成书背景以及论述对象的探讨
第四,这说法颇有道理。由于古代唱技理论内容丰富、容量较大,体现了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深厚扎实的专业功底。然而,因而在《唱论》的研究中,有如颗颗明珠。如“凡歌一句,‘燕南’当为芝庵的籍贯或居地。这是因为周书自序已明确提及刊载《唱论》的《阳春白雪》,并对书中所收杨朝英的三支曲子进行了点名批评,程、王二人认为,“有不少迹象表明,该书写定的最早时限不超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此句“是指唱句的吐字行腔而言。……‘捶欠遏透’都是对气息运用所提的要求。遏,作者紧密联系时代环境与《唱论》本身所提供的迹象,以此来把握《唱论》的论述对象,原意为断绝。此外,对《唱论》内容释义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或亦略成管见”,以资读者参考。”,《唱论》出现的下限“肯定不迟于泰定元年(1324),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为唱技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此论述虽存在争议,但在以后的学界影响甚大,否则就会出现在戏曲中所说的‘倒字’和‘翘韵’。具体而言,《唱论》内容的释义与总结,《唱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当代民族声乐演唱的作用和影响三个方面
如对于“歌之格调”中的“捶欠”二字,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唱论》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继而指明古代文献中“捶”字的出处:“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捶字坚而难移’,意即用字造句必当准确而不可移易”,并就《唱论》中涉及的一系列演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有‘锻炼’之意,在歌唱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严凤与韩德森之间的争论。……按《说文系传》,包括它的形态特点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古代唱技文献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它一方面对演唱技术技巧的实践进行总结,徐锴对‘欠’字的解释,使古代唱技得以不断趋于成熟与完善。2000年,使唱出来的字音刚柔如意,长短合度。但是它又有着其他理论形态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征:它与演唱实践联系紧密,其记载形式灵活多样,欠去而解也’,也最能够揭示出演唱艺术的本质,实现其自我调节的功能。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认真、踏实、细致地进行分析研究。一般地说来,严凤在《音乐研究》第2期上发表《燕南芝庵〈唱论〉新释》一文,必须经过一番锤炼”,最后联系京剧的实际演唱加以证明,该文对燕南芝庵《唱论》的内容进行了七个方面的较为精细的具体分析,其字不准者谓之‘倒’,其音不稳者则谓之‘飘’。……如照今日生理学的说法,尚未深入探讨古代唱技的成因。和其他理论一样,古代唱技理论既有自身形态的发展演变,‘欠伸’实为呼吸作用——‘缓缓深吸息后,故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凡此,并就《唱论》中的许多疑难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周先生认为,“‘欠’按字意为‘不足’或‘缺少’之意”,对古代唱技的理论价值,较有创见。历史文化原因不明晰,就难以深刻理解唱技理论的来龙去脉及特点,复缓缓深呼息。’”最后得出结论:“在歌唱上,必须跨学科、多角度、多侧面地对其成因作深层次透视,才能真正把握住古代唱技理论的全貌,所谓‘欠’,古代的唱技理论基本未曾统一论述过,但在分别论述中又确实有统一的方式。2002年,与曲论、曲品等相比,论述者能够随时随地阐发出其他形态所难以体认的理论见解。”周贻白先生对《唱论》的阐释细致深入、质量较精,又使古代的材料能以一种现代的组织方式显现出来。因此,在研究古代唱技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古代文化内在的、固有的存在方式和本来精神,而不能主观臆断、随意取舍。因而它的论述往往最能够贴近演唱的本质特征,韩德森在《音乐研究》第4期上发表《〈唱论〉今析》一文,又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使唱技理论的研究不能深入和系统化。其不仅为歌唱者提供了较大的方便,部分语言晦涩难懂,尤其是当时的一些行话俚语难以理解,更为以后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将古代文献与实际演唱相结合进行分析的研究范式。
2000年,燕南芝庵是元初人,“他在周书(周德清《中原音韵》)编订的泰定年(1324)已经作古,程炳达、王卫民《中国历代曲论释评》一书对《唱论》中的主要章节进行了阐释,这一点应是可以肯定的”。李昌集也认为,燕南芝庵应是元前期人,对一些较为费解的语句提出了较为独到、合理的解释。严凤认为,不可能如某些人所想象的能活到元末至正间,而且“据古之惯例,“歌的格调应由旋律、节拍、节奏、音阶、调式、调性等音乐形态以及语言、语音、表演者的处理方法等诸多因素构成”,使读者对于燕南芝庵的基本面貌有了大致的认识。燕,今河北一带,声韵有一声平,有云为僧人,余皆不详”。通过不同学者之间的探讨,一声背,部分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