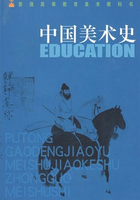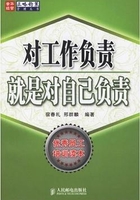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气息是歌唱的根基与动力,气在歌唱中具有引字、导声的作用,三者关系密切,不可偏废。其理论结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确立了气息技术理论的基础观念是“气为音帅”,即气息在歌唱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歌唱的第一要素。第二,对调节、运用气息的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总结,对指导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气息理论与西方的气息理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其一,在研究观念及表述方式上,中国古代唱技理论家往往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他们更多地从唱者的心理、意念出发进行理论阐述,强调唱者意念对气息的调节和运用,而很少进行“为什么”的理论分析。其表述更多的是建立在对气息的直观体验上的,故显得含蓄、深奥。西方唱技理论则通常以理性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同时采用科学论证的方法对气息技术进行研究,以此探明歌唱气息的产生过程和原因。因而西洋声乐理论善于从生理与物理特性的角度指出声带必须通过气流的冲击才能发声,并对呼吸时各个身体器官与肌肉的活动详加阐释。其二,在理论内容上,中国的气息技术理论更注意气息的灵活运用,注重对“点”的详细阐述;西洋气息理论更强调对气息的整体控制和保持,突出对“面”的整体把握。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气息技术理论内容更为复杂、多样并富于变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节 气息技术的理论结晶
早在战国时代,我国民间歌手就能在演唱中自如地控制气息,但一直到隋代,才有关于歌唱气息的记载,即虞世南《北堂书钞·乐部·歌篇》中的论述。其后,历代歌唱家、理论家对气息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气为音帅”——气息技术理论观念的确立
“气为音帅”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唱技理论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命题。早在隋唐时期就开始了对气息运用的探讨,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气息问题成了理论家们普遍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在“气为音帅”的表述方式上,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感悟性、随意性特征。历代理论家很少直接提出“气为音帅”的观点并加以论述,更多则是通过气息对演唱字、声、情的影响来阐明气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此表明气息是歌唱的根基与动力,气在歌唱中具有引字、导声、带情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唱技理论史上,较早对“气为音帅”观念有所涉及的是唐武则天敕撰的《乐书要录》。书中载:“夫道生气,气生形,形动气缴,声所由出也。然则形、气者,声之源也。”尽管这里的“声”并不仅指“人声”,更多包括的是“乐声”,但是,它毕竟已把气息作为发声的一种重要因素来对待,为后世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基本的方向。
“气为音帅”观念的真正确立者是唐代段安节,他明确指出演唱的首要之事是调整气息。其《乐府杂录·歌》云:“善歌者必先调其气”,即善于歌唱的人必须先调整气息。只要气息调整得当,就可以分辨出“抗坠之音”。“抗坠”二字,最早见于《乐记·师乙篇》:“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抗”、“队”(通“坠”)通常指歌唱时的高音和低音,而段氏之论因联系气息运用而言,故笔者认为“抗坠之音”具体应指气息与喉头、膈肌相对抗所发出的声音。气息与喉头的对抗指歌唱呼气时气柱上升,喉头向下抵抗气息的冲击(喉头放下挡气可以获得良好的共鸣);气息与膈肌的对抗指气息托着声音进入头腔时需要深呼吸,腰围扩张,与膈肌对抗,由此产生下坠之感(音越高气越深)。这两种上下力量的对抗,既可以保持喉头的稳定,又可以使由上至下的共鸣腔体(头腔、鼻腔、口腔、喉腔、胸腔、腹腔)充分打开,从而获得良好的共鸣。故段安节说:“既得其术,即可至遏云响谷之妙也。”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呼吸方法,就可以获得阻碍行云、震荡山谷的声音。可见,在段安节看来,决定歌唱质量好坏的关键在于对气息的调整运用。
段安节之后,北宋陈旸对“气为音帅”的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既继承了段氏“善歌者,必先调其气”的观点,又有所发展,将气息对声音高低、强弱的影响作了具体的阐发。其《乐书》云:“……而抗坠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于抗越,细而不至于幽散。”(详见上篇第二章第一节)
明清人对“气为音帅”的基础观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他们对气息在演唱中的基础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歌唱时的吐字、发声都离不开气息,字声二者的协调平衡更需要气息的支撑。明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曰:“其妙在喉管之交,其用常潜于声气之表。……有贱工者,见乎善为乐者之若无所转,而以为果无所转也,于是直其气以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复,是击腐木湿鼓之音也。”该段话大意指(歌唱)的妙处在于声音,其用法常隐藏于气息对声音的调节中。……那些技艺不娴熟的人,看见善于歌唱的人(歌唱时)好像没有调整气息,以为(歌唱时)真的不用调整气息。于是直接呼气出声,结果往往是气息一泻而尽,声音好像敲打腐木湿鼓一样的沉闷破烂。明应谦《古乐书》序曰:“声之变有万,而不离有五:喉音宫,齿音商,牙音角,舌音徵,唇音羽。五者备矣,无中气则不发。”大意指,声音虽然千变万化,却无非是宫、商、角、徵、羽五音而已,但即使这五者都具备了,没有气息的作用也是不能发声的。
清方苞《诂律书一则》云:“气就形者,以人之气而就乎乐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气之大、小、缓、急调剂而成,故曰就也。”方苞认为,声音(包括人声、乐器声)的高、下、疾、徐等变化,都是根据演唱(奏)者气息的大、小、缓、急调剂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清王德晖、徐沅澂提出的“养气”论,阐述了气与声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其《顾误录·沈衣冲养气论》云:“度曲者得四声之是,虽拙亦佳,非徒取媚于听者之耳也。……而其要领,在于养气。谭子《化书》云:气由声也,声由气也。气动则声发,声发则气振。”王德晖、徐沅澂引用谭子《化书》中的观点指出:气息随声音而出,声音又由气息决定。气息推动使声音发出,而发出的声音又使气息产生振动,因此,度曲的要领在于养气。王、徐二人论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指明了气息与声音在歌唱中是相依共生、缺一不可的,这是一个颇为辩证的看法,是“气为音帅”观念的延续与深化。显然,明清人对歌唱气息的特点和功能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故他们在关注气息的基础地位上,又对气息的功能以及其对吐字发声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从而充实和完善了气息理论。
1918年,近人陈彦衡在《说谭》中将“气为音帅”的观念在理论层次上大大提升了一步。他说:“气者,音之帅也。气粗则音浮,气弱则音薄,气浊则音滞,气散则音竭。”“气粗音浮”指气息过多而不善于控制会使声音轻飘虚空,如歌唱时声带不闭合或闭合不好,则容易先漏气后出声,使声音被气吃掉;“气弱音薄”即气息浅而少时会使声音显得单薄,如气息没吸到肺的下部,膈肌就无力支撑,容易导致声音软弱无力;“气浊音滞”指气猛力重而导致声音不流动、不灵活,如吸气过多,呼气的冲击力太大会使声音显得笨重;“气散音竭”即气息的用力点不集中,致使声音轻弱松散、后力不济,如歌唱时不善于安排气口,易使气息不够用,导致声音散漫无力。这些论述表明,到近代,人们对“气为音帅”的观念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做出总结性归纳,使其在理论上得到了一个较为完满的总结。
可见,“气为音帅”在古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观点,它表明古人对歌唱中气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歌唱时的发声和行腔必须依靠气息的支撑。人体歌唱时运用的共鸣腔有头腔、鼻腔、口腔、胸腔和腹腔。歌唱时,气息自腹腔经胸腔到达口鼻腔再贯穿头腔,使气流在共鸣腔里连续激荡,形成声流的振波,从而产生共鸣效应,实现声音的美化。只有掌握调气的要领,运用共鸣腔体来控制气息,才“可得遏云响谷之妙也”,才能获得好的共鸣;同时,要通过气息的贯穿来调节声音的高低、强弱、连断和起伏,才能达到“气盛而化神”,使行腔圆满而流畅。其次,气息与歌唱的咬字吐字关系密切。歌唱的声音表现主要借助于母音的发挥,而母音的发音既要依靠口部共鸣腔形状的改变,又必须通过气息运用使声带振动而实现。因此,没有气息的支持与作用,母音就不能完成音高与共鸣。同时,子音虽然大部分不振动声带,但它更需要气息的支撑去突破发音部位的阻碍,即通过气息的力量去发挥喷口的作用。加之大多数子音不颤动声带,故字头的时值极短,这样发音在蓄气成阻时就要根据字的需要来控制气息,气息越充分,发音除阻时才越有弹性。因此,无论是母音,还是子音,都离不开气息的支撑,无气则无字,气在歌唱中具有引字、导字的作用。尽管古代气息技术理论的论述不够详尽完备,却是当代民族声乐气息理论的有力依托,没有前人对气息理论观念的逐步确立,当代民族声乐气息理论的发展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气息技术技巧的细致研究
在“气为音帅”观念的指导下,古人对调节、运用气息的各种技术进行了分析、总结,这些论述直观深入,是现实气息技术技巧的规范,具有明显的实践技巧性。其主要技术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不同声音、不同旋律进行时采用的气息技术。南宋张炎在《词源·讴曲旨要》里对不同唱腔的用气方法阐述得颇为精到:“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好处大取气留连,拗则少入气转换。”现以南宋姜夔词乐《扬州慢》上阕为例,对张炎的论述加以阐发。《扬州慢》前三小节均是一字一音,速度略快,演唱这类曲疾字密的唱腔时,要快速而不慌乱地吸气,即“忙中取气急不乱”;第四小节的“程”字需要延长两拍半,唱时要保持气息的连贯性,以免气竭力衰,断了声音;而八分休止的地方一定要声停气断,以免乱了节奏,即“停声待拍慢不断”。第十小节是高音区的进行,在高音出现时,须提前吸足气,以确保声音的圆润流畅,即“好处大取气留连”;第八到十二小节的曲调连绵不断,此时气息量不能贪多,要把握好气口,学会小换气(即偷气),否则会破坏曲调的完整性,即“拗则少入气转换”。显然,张炎对气息与不同唱腔之间的关系已有了清晰的辨析,他的论述具体、实在,是切实可行的技巧法则。
其二,演唱不同字音的气息技术。清徐大椿《乐府传声》一书中曾多次谈到不同字音的气息运用方法。如《归韵》一节曰:“如东钟字,则使其声出喉中,气从上腭鼻窍中过,令其声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则东钟归韵矣。江阳,则声从两颐中出,舌根用力,渐开其口,使其声朗朗如叩金器,则江阳归韵矣。”在唱东钟韵的字时,当气流从喉咙出来以后,使其通过上腭和鼻孔,一半归入鼻腔,一半从口腔出来,这样发出的声音就可正确归入东钟韵;唱江阳韵时,舌根用力,使气流从口腔的两侧挤出,同时口型逐渐张大,发出一种类似敲击金属器皿的琅琅声,这就是江阳韵的正确归韵方法。
在《收声》一节中,徐大椿结合气息的特点来解释吐字收声的重要性:“至收足之时尤难。盖方声之放时,气足而声纵,尚可把定;至收末之时,则本字之气将尽,而他字之音将发,势必再换口诀,略一放松,而咿哑呜乙之声随之,不知收入何宫矣。”演唱一个字的收音处是最难的。因为当其刚发音时,气息很饱满充足,声音可以收放自如好控制;但到收音处时,为这个字发音而送出的气流量已大大减弱,而下一个字的字音紧跟着就要发出,因此必须要准备变换下一个字的发音口诀,这时只要略一松懈,就会发出一种含混不清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字音了。由于昆曲多是一字数音,因此尤其要注意字尾收音时对气息的调整。
其三,对于不同的歌唱情感的气息运用方法,古人也颇多论述。其中,清中叶苏州老艺人吴永嘉对不同声情的用气方法进行了总结,其论述简洁、精到,颇有见地。其《明心鉴·勤学集·声》云:“声欢:降气”、“声恨:提气”、“声悲:噎气”、“声竭:吸气”。《明心鉴·勤学集·气色诀》中又对以上论述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气降心发喜欢笑,气升心发怒恨恼;气噎心发苦悲伤,气急心发惊竭叫。”整体大意是:表现欢乐的声音时要将气息沉下去,即吸气要深,这样发出来的声音明亮饱满,给人欢声笑语之感;表达愤恨的声音时,要将气息提起,即吸气后将气息控制在胸部,使人觉得呼气受阻,不畅快,这样发出的声音显得沉郁压抑,给人愤懑之感;表现悲伤的情感时须噎气,即呼气时时断时续,呼吸急促,给人悲痛难抑的感觉;表现声嘶力竭的情感时,呼吸要急促,要像吸气一样快速而突然,这样发出的声音不够圆润连贯,有断绝之感。
$第二节 气息技术理论的民族特色
中西方的气息技术理论在基本原理和作用上大体相似,所遵循的自然规律也基本一致,但是在理论内容、研究观念及表述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古代气息技术理论中“点”的具体研究
中国古代唱技理论家们善于对气息技术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注重对“点”的详细研究。他们往往通过气息与发声器官、气息与咬字吐字、气息与行腔的巧妙配合来采用不同的呼吸方法,以满足不同字音、不同曲调,以及不同风格歌曲、不同声乐形式的演唱需要。
如明代程明善在《啸余谱》里列出了发外激、内激、含、藏、散、越、大沈、小沈、疋、叱、五太和五少十二种啸声的方法,这些都是在气息和发声器官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如发外激音:“以舌约其上齿之里,大开两唇而激其气,令其出,谓之外激也。” 发外激音时要将舌头抵在上齿里面,上下唇尽力张开,使气息冲击牙齿而出。发内激音的方法是“用舌如前法,闭两唇于一角,小启如麦芒,通其气,令声在内,谓之内激也”。“芒”,稻麦等子实壳上的细刺,指将舌头抵于上齿内,两唇关闭,但留一个像麦芒一样的小孔,气息从其中通过,使声音包含在嘴里。再看如何发大沈音与小沈音,“沈”,读作chén,同“沉”。发大沈音时:“用舌如外激法,用气,令自高而低。大张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含气煌煌而雄者,谓之大沈。”即将舌头像发外激音一样抵在上齿内,气息自高而低。喉咙打开,好像嘴里含着大东西一样。气息充沛而雄壮的,就是大沈音。小沈“用舌如上法,小遏其气,勿令扬大。小沈属阴,命鬼吟龙多用之”同上。。发小沈音时,舌头仍然抵在上齿内,将气息略为阻挡,使其不致扬大。小沈属阴,常用在命鬼吟龙之处。尽管程明善论述的是一般的啸歌之法,但对于舞台演唱仍然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