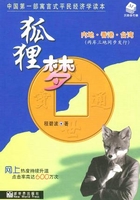到汉景帝时,邓通钱就不许制造了,而且西汉第一官商邓通在家产被没收后也给活活饿死了——死时身上一枚铜钱都没有。即或这样,朝廷也没有禁止邓通钱的流通。邓、卓二人对邓通钱的制造工艺要求得非常严格,采用先进技术自不用说,他们绝不允许在钱币里掺和杂质,其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上至王公大臣、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邓通钱。
不许造钱并未给卓氏带来麻烦和大的影响,那时,他的钱已多得不用造了,并且,他一定又攀上了汉景帝或朝中另一位权臣——不然,何以在邓通案中泰然度之、无涉惊险?
如此华丽转身,是“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趋炎附势,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趋利避害,只有卓王孙自知了。此外,我们一定没忘当年卓王孙得知女儿与司马相如私奔而气得发青的那张脸,可后来,当司马相如乘驷马高车荣归故里时,他又瞬间转变为大喜过望的一张脸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司马相如被汉武帝拜为中郎将来西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公干中,作为岳父大人和川商翘楚的卓王孙,在利用自己的蜀滇影响力和筹资能力帮助女婿打通南丝路等实际作为中,还是出了大力的。
$古书中若隐若现的川商背影
网上有个“中国古代十大富商”群英谱: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桑弘羊、邓通、卓王孙、石崇、蒲寿庚、胡雪岩。十席中,川商占了两席。
“十大”之外的候选者还有:猗顿、程郑、计然、寡妇清、董贤、王元琛、王元宝、沈万三、伍秉鉴……
商人是商业的主体——没有商人,何来商业?
在当今这个“拜金主义”至上的社会,商人的地位大概是仅次于官员了。有时,二者之间还可以相互切换——不想官了就下海为商,不想商了就上岸为官。而官员把自己切换为或农或工的身份,却是鲜见。
也就是说,当今,商人的身份几乎到了可与官员身份作平等换算的地步了。
但在古代,却正好相反。
一鳞片甲、吞吞吐吐、语焉不详……现在,我们来看看若隐若现在残书中的川商背影。
在管仲为国人各身份人等排定尊卑、高低、等级次序前,“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穀梁传》)自从这位有过经商经历、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说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管子?小匡》)后,商人的地位虽各朝各代各地时有小变,但大体上或基本上都身处末位。
但管仲还是说了,“四民”是国家的砥石、骶柱,士农工商缺一不可。
士、农、工、商,古代“四民”中处于第一等的士阶层指的是仕途中人、文士和武士。尔后依次的等级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
正因为商人在强势话语权和公共话语权中位居末等,所以哪怕你特别优秀如士,特别忠孝节义如农工,也很难在那些由统治者掌控的史书中和民间文人的笔下,留下自己清晰的面容。
就算入书,商人也多是以一些出格行为或偶发事件出场的,如欺行霸市、豪狭、奢华、行贿、斗富、资助、结交权贵、走私等。还有一些是因“拔出萝卜带出泥”出场的,如子贡、范蠡、管仲、吕不韦、桑弘羊——他们商人身份的曝光,很大程度上是非商人身份的作为。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为保证入书内容的干净,司马迁一再声称,他在《货殖列传》中所描述的郭纵、乌氏倮、蜀卓氏、程郑、婉孔氏、曹邴氏等10几位富商均属于“贤人所以富者”,而“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但实际也是并非如此。
一鳞片甲、吞吞吐吐、语焉不详……现在,我们来看看若隐若现在残书中的川商背影。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他们既是一个族群、一位王者、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与遥远记忆,也是那个时代的川商名号。北宋蜀人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对蚕丛的从商经历有过记叙:“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
前面已详述了第一川商卓王孙的故事,简叙了亦官亦商、以家乡蜀郡为基地、以钱为经营产品的邓通。在此不赘。
链接资料里所列的从古蜀到近现代的川商清单可以看出,天地广大,人文浩瀚,各界英雄层峦叠嶂、挟江裹海,但几千年下来,有名有姓的川商
却是稀薄如斯、模糊如斯——像雾霭深处的谜团。古代商人地位有多低,于此可窥斑见豹。
“三教九流”中的“九流”有此一说: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民、工人、商贩。与“四民”中的排位一样,商人在“九流”中依然处于打底垫背的末等地位。
在晋代,对商人有个侮辱性的要求。商人穿鞋,必须一只白、一只黑——免得造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让商人浑水摸鱼。
古代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想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管子?轻重甲》篇对商人作了如是界定:“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管仲认为,如果对富商巨贾任其自流,其后果是“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大商人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将一些重要物资和农产品聚拢,最终发展壮大到形成对国家经济的垄断,操纵国家各行各业的命脉,甚至干预政治,威胁君主的统治地位,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另外,国家“公务员”的腐败,大多是商人行贿造成的。总之,用武力等手段推翻政权,或让国家在腐败中自行崩盘,商人都有基础和能力。所以,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豪商巨贾。
这是站在统治阶层的立场讲的。站在官吏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提携”商人以便中饱私囊,另一方面他们打压商人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进一步索取资财。
以其他“三民”士、农、工视阈看,因商人比他们混得滋润甚至奢华而闷闷不乐——仇富心理由此产生。
事实是,不仅古代商人排序位居末等,就是将时间上溯到尚未“改、开、搞”的30多年前也是如此——那时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是一颗大星,加上下面的4颗小星。这4颗小星,一颗是工人阶级,再一颗是农民阶级,又一颗是小资产阶级,最后一颗是民族资产阶级。这4个革命阶级,既是一种政治分层,也是一种政治定位。工、农、兵、学、商,即是这个定位的惯常表达。
那时,与工、农、兵、学、商对立的,还有一个排序:地、富、反、坏、右。这应该是一个从性质“最坏”、地位最低,到性质“稍坏”、地位偏低的排序——否则,富裕的地主怎么排到不穷的富农前边呢?按这个排位法,具有商人性质的地主和富农,其地位比“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还低。
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红五类”是指个人履历表上出身一栏填写的本人身份: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在“红五类”中,工、农、兵、学、商“五民”中的商人和读书人被剔除了。
说白了,“投机倒把”就是指某人在A时空以低价买物,在B时空以高出卖物。
得以印证的是,《成都概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年5月版)“知名人物”中,历数上下三千年的成都名人,居然没有一家商人。
商人的地位在今天都如此,遑论古代。
$川商弄潮:一个人的大千世界
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乔家大院》等的热播,国内骤然间掀起一股“商帮文化热”。
明清中国,九大商帮纵横商海、身影卓然:晋商、徽商、闽商、粤商、潮商、赣商、苏商、浙商、鲁商。但川商未见其影。
2006年5月,各路商帮齐赴杭州西子湖畔,参加首届中国商帮峰
会——川商未能在大会上现身。与会的有浙商、苏商、粤商、闽商、汉商、京商、沪商、鲁商、豫商、冀商十大新兴商帮代表,有领改革开放之先风的港商、台商代表,还有历史上曾经辉煌的晋商、徽商、龙游帮后裔,以及今天重新振兴的晋商、徽商、龙游帮代表。
2010年6月,新一届中国商帮峰会召开,浙商、徽商、苏商、闽商、粤商、晋商、鲁商、湘商、川商、京商、沪商、赣商、豫商等著名商帮企业领袖人物云集郑州。郑州,我们见到了川商的席位。
川商不缺勤劳吃苦的创业精神,豁达开放的开拓精神,诚实守信的立业精神,运筹帷幄、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但在举国公认的商帮排名中为什么毫无优势可言,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团结不够?
散兵游勇,单打独斗,互相防范——如此形态与作为,自然形不成川商群像的话语权及由此造成的对全国公共话语的影响力。
浙商信奉“有钱大家赚”,喜欢抱团打天下。在一个地方哪怕只有3个人,他们也能形成合力,团结互助,共同赚钱。他们常常集中强大兵力,先撕开一个市场缺口,然后从家乡不断搬兵加入,安营扎寨,从小盘到大盘,不断做大,除非市场有变,否则绝不撤退。
商帮是群体,商人是个体——商帮是个体的集合。
群体川商的确需要大胸襟、大境界、大包容,需要“团结团结再团结、发展发展再发展”。一个商帮要有出息,这是必由之路。
——虽然每一个川商都有一个大千世界,都是一个大千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都的双燕冰箱与成都牌电视机、峨嵋牌自行车等产品曾轰动一时、畅销国内,写下了“成都造”的辉煌——现在,哪里还有它们的身影?改革开放32年来,一个个的川商踩着中国经济前沿浪潮的峰巅,在一步步走来的路上,可谓几多沧桑、几多辉煌。《川商》杂志主笔张镜先生在《川商30年:光影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一文中,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了这段川商历史。一部川商史,就是一部中国经济发展史的浓缩版。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并用48页的篇幅介绍了邓小平和打开国门的中国。
正是这个四川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出场,中国商人的舞台才被历史性地搭建和启幕。
1992年春天,深圳,还是这个四川人的一次“南巡”讲话,举国上下顿时掀起了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经济热”、“下海热”、“经商热”。
念商经、数商人、谈商事,我们怎能绕开改革开放初期,成都地区出现的一系列的中国第一:
5000年前,世间最早的货币——天然“海贝”在三星堆时期使用;
晋十六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在成都诞生;
北宋初年,世间第一张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
1998年,成都水井街发现中国烧酒(白酒)第一坊——水井坊遗址;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商业广告在成都诞生;
1980年,成都发行了全国第一张股票——蜀都股份;
1985年,成都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民间股份制商业银行——汇通城市合作银行;
1987年,成都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成都华茂典当服务商行;
1988年,开办了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市场;
1991年,开办了全国第一家交易所式的批发市场——成都肉类产品批发市场;
200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十大城市私家汽车拥有量,成都(233119辆)排名第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家乐”发源地,三圣乡“五朵金花”被评为4A级景区;
中国商业网点密度最高的城市。
呈现和实现商业的平台是市场。换言之,市场无,商业无。市场有各种各样的形态:露天市场,室内市场;临时市场,节会市场,永久市场;果蔬市场,汽车市场,粮食市场,钢材市场……
翻查市场的脉络,追寻市场的源头,一定会发现一个词:庙会。
成都庙会历史悠久,是一幅如梦如幻、五彩斑斓的“清明上河图”……
佛教的大慈寺、道教的青羊宫及二王庙——此三地庙会,闻名中国。
千百年来,大慈寺一带因庙会而成为商贸集散地,至宋代始更是庙会频频:农历二月十五卖花木蚕器,称蚕市;五月卖香药,称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七宝市……
庙会其实就是依托庙宇开展的一次又一次的商品集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不惟庙宇,置身闹市的会馆也是商机重重,人影憧憧。会馆里的各种祀祭活动,与庙会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川是移民大省,成都是移民城市,因此,外省同乡会兴建的会馆鳞次栉比,比如广东会馆,又比如湖广会馆……
能够将宗教与民俗整合成市,商业力量的厉害,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