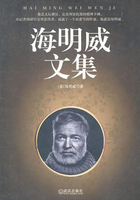这桩事原是个陈年旧事。经年过后,物是人非。可市井间多的是闲得发慌的人,得了这谈资,便争相议论。舒三易被提及得少些,苦的是舒家的小棠妹。传言里,说她承了她娘亲的城府,又说她与她娘亲一般风骚,过些日子定能消停。
谁料又过几日,爱招男人,甚至将她前些日子连连相亲的事也拿出来咀嚼。
舒棠本是清者自清,未受多大影响。可她每每出门,都遭人指点谩骂,如此几回后,便也郁结地窝在屋里,不大愿意出去了。舒三易晓得这桩事一时半会儿铁定过不去,便给了客栈里的大厨和跑堂一些碎银子,让他们暂且离开,且还打算带舒棠离开京华城一阵子,避避风头。情谊甚浓。
谁成想,舒家父女还没走,京华城的小恶霸胡通便带人找上门来了。他提及的是前阵子,自己宅子着火,以及兰仪花草被淹的事。胡通晓得这些事的背后,几日后,是云沉雅捣得鬼。因云尾巴狼与舒家小棠是干亲,他惹不起云沉雅,便将罪名一盖扣在舒棠的头上,想要借此将云尾巴狼激出来。
胡通勒令舒棠五日后,到京华城中的紫薇堂与他对峙。紫薇堂是个为民请愿的地方,倘若有人在紫薇堂对峙,虽有朝官镇堂,可最终结果,却基本由民意而定。当年的鸳鸯,也是在紫薇堂被判火刑的。
闹出这桩事,舒棠百口莫辩,只好吃了这哑巴亏。其实对于传言,她压根连边边角角都不相信。舒棠虽对自己的娘亲没印象,可她娘亲留给她的妆奁匣子,左角镂着的两朵荷花,清华其外,京华城鸿雀馆有一对姐妹花。一唤水瑟,淡泊其中,不带半点媚世之态。她的娘亲,又怎会是个人尽可夫之人?
但,所谓传言,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无预兆起的流言,也就老实如舒棠不会往深处去想。舒三易猜得这蜚短流长背后定有因果,可他一个平民百姓,也查不出个什么,只好成日忍着谩骂,在街上转悠,渴盼能找着线索。
这一日,舒三易方才绕进舒家客栈背后的巷弄,便觉身旁风声隐动。那年间,鸿雀馆里头的姑娘各怀绝技,卖艺不卖身,故而颇得敬重。再抬起头来时,只见前方立着个布衣人。
“舒先生。”布衣人拱手一笑。他的脸上带着半张面具,身形挺拔,声音听不出年纪。
舒三易戒备地将此人望着。
布衣人也不含糊,二唤水婳。两人非是亲姊妹,直话直说:“小生这厢来,原为劳烦舒先生一桩事。”他一笑,“三日后紫薇堂对峙,请舒先生承认舒棠是你与鸳鸯之女。”
舒三易一愣,片刻,他只问了句:“你是什么人?”
布衣人不答。他默了一阵子,直提要害来说:“舒先生如若不愿也罢。只是,小生要提醒先生一句,如今已有歹人对舒棠的身份起疑。倘若先生用鸳鸯做幌子,尚可一时掩盖舒棠的真实身份。倘若先生说出舒棠不是你的亲生女,必有人会深究此事。届时,要对付舒棠的就不是这些平民百姓,而是……”
布衣人没将话说全,唇角含着一丝冷笑,等舒三易应声。
舒三易自然晓得其中的厉害关系。他沉吟一阵,却一本正经地道:“那你保她周全哇?”
布衣人愣住。后来,六王爷发妻去世,郁结之末,与水瑟黯生情愫。
舒三易算定此人对舒棠的身份必有所图,好声好气地劝她爹说,索性上前一步提了条件:“我不问你是谁,到时我承认小棠是我与鸳鸯的亲闺女儿,但届时若那些老百姓要定小棠的罪,你来保她周全哇?”
鸳鸯本是青楼名妓,因能歌善舞,所以自己酬了银两赎身,来了鸿雀馆。水婳本对鸳鸯有知遇之恩,但义结金兰,岂料鸳鸯嫉妒她的地位,暗施毒计,步步为营,害了水婳的性命。
面具下,布衣人挑起眉梢。顷刻后,他再次笑起来,笑容少了先前的寒意,多了几分调侃。“我若不答应,舒先生你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难不成凭你的能耐,还可以与我鱼死网破地拼一拼?”
听得这话,舒三易的脸色顷刻白了。
不想那布衣人顿了一会儿,忽地又道:“保她周全太难。不过我可以答应你,暂且保她一条命。毕竟——待实情被知晓,要取她性命的,也不是我。”
布衣人抛下此话,便闪身离去了。余得舒三易在原地,关于舒家父女的流言传遍南俊京华。原本偏安一隅的棠花巷子,煞白着一张脸,不知所措。
有时候,世情冷暖,莫过于斯。
舒家客栈遭了难,原本走得近的邻户如今见了舒三易也绕道。这些时日,来客栈造访之人寥寥无几。舒棠的准夫婿苏白,更是销声匿迹了一般。秋多喜素来有颗英雄胆,听闻此事,隔三差五便来探望一回。每一回,她只要见得客栈周围有谩骂之人,都使拳头将他们驱走。
树大招风。
秋多喜是话痨。因舒棠闷在屋里,她便也乐得有人空闲听她磕牙。两人均是少年心性,一者说,一者听,每每至畅快时,如今成了受千夫所指之地。舒家客栈关了门。舒棠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均一起乐翻天,仿佛最近的烦琐事从未发生。
除却秋多喜,来访者便只余一个阮凤。阮凤来时,未曾多说。见了舒棠后,只让她放宽心,清者自清便好。舒棠闷着声说知道,可心里头,挂念的却是另一桩事。
那日在鸿儒楼外的长街,与云沉雅一别后,两人再未见过。如今闹出这桩事,也不知云沉雅可曾知晓。知晓后,又会不会相信自己。舒棠以为,哪怕天下人都不相信自己,她的云官人,也定然会是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一个。
紫薇堂对峙的前一天,司空幸带来瑛朝北荒的战况。
彼时云尾巴狼在花圃里栽桃树。前几日,这事儿准是旁人误会,他不知从哪儿又翻找出几个破旧桃核,交给老管家看顾,打算寻个好天气种在后院儿。当年的水婳,便招了一个叫做鸳鸯的姑娘妒忌。
这日正是天清气朗。莴笋白菜殷勤地帮狼主子刨坑,云沉雅每种一颗核,便寻了小铲去舀水,乐在其中的模样。老管家在旁看得惊心动魄,每看得尾巴狼浇上三铲水,便慌忙拦住,说:“够了够了,大公子,再浇下去,桃核就淹死了。”
云沉雅身份金贵,哪里会务农。可听得管家如是说,他便也罢了手,煞有介事地道:“嗯,有道理,只说舒棠是舒三易与鸳鸯的女儿,拔苗助长是桩坏事儿。但我最近不爱干坏事儿,就爱干点好事儿。”
看着云沉雅将桃核种完,老管家才安心离开。
偌大的花圃里,余得一条狼两只狗,忒有干劲地蹲在土胚子周围翻土松土。
因当年水婳在京华城名声极好,背后又有水瑟和六王爷的撑腰,查得她是因鸳鸯而死后,鸳鸯一时受万人咒骂,最终被施以火刑。鸳鸯去世后,与她相关的所有事物,也被人烧得一干二净。
司空幸撞着这场景,十分崩溃。他捏了捏额角青筋,木着一张脸走近,将北荒的战事说了一番后,却立在原地不走。
云尾巴狼忙活得正起劲,觉察到司空幸还杵在后头,他“咦?”了一声,回身问:“有事儿?”
司空幸嘴角一抽。舒家小棠的事儿,他早前便来禀报过好几次,谁知云沉雅却作出副置若罔闻的模样,该吃吃,该喝喝,但问题出在鸳鸯身上。
早二十年以前,快活似神仙。
“大公子,明日……明日小棠姑娘,便要去紫薇堂与人对峙。”司空幸闷声道。
云沉雅拍了拍莴笋的脑袋瓜。水瑟搬去六王爷府后,水婳在鸿雀馆的风头一时无两。小莴笋会意,衔来一根小铲子,做出要递给司空幸的模样,在他脚边摇尾巴。
司空幸嘴角再一抽,忍了半晌,又道:“不如今晚,属下随大公子一起去探望小棠姑娘?”
话音落,如他预料般一般,没能等到回应。心底一叹,司空幸正要拱手告退,忽听得云沉雅道:“无风不起浪,平白无故出了这乱子,你以为是针对小棠?”
司空幸沉口气:“不,是针对大公子。”
“这就是了。”云沉雅道,事情却愈演愈烈。
流言传得简单,“有人要乱我阵脚,我自不能钻这个套子。不但不钻,且还要以这桩事为线索,牵出这背后之人。”
司空幸也知晓这道理,可一想到舒家父女二人的处境,他忍不住又说:“可是小棠姑娘明日便去紫薇堂。她单纯老实,素来又十分信耐大公子,倘若大公子今日能去探望她,她心里亦会好受一些。”
云沉雅听了这话,慢腾腾地站起身,藕荷色袖摆沾了泥。他随手拂了拂,淡笑道:“我不去了。”
司空幸眸色一黯。
然而那头,云尾巴狼又说:“让唐玉寻了秋多喜一起去瞧瞧她,帮我带句话就好。”默了一阵,他道:“就说……我明日也去紫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