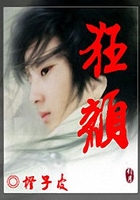没过几天,他果然接到她的电话,问他:“你在哪?”
他正在开会,底下一大片的人,而且全都是企业的高管,只能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过会再打给你。”
那个会开得有点长,等会议结束他把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她已经到了他家的别墅,说和张阿姨一起做了饭等他回来,本来会议之后还有个酒会的,他找了个借口先走了,弄得他那些叔叔伯伯们一脸的不满。
在苏家,他之所以实权在握,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爷爷的偏爱,他那些叔伯们早就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只是忌惮爷爷和外公在他背后撑腰,因而才不敢造次。
可他却还是要时时刻刻地提防着那些叔伯们有什么小动作或是自己有什么把柄会落在他们的眼中,香港的事就是个例子,他刚刚救了左锦弦,马上就有人把这件事捅到老爷子那里去,害得他挨了爷爷一顿臭骂。
像他这样一个人,在旁人看起来风光,其实其中的勾心斗角是又怎是那些外人所能猜到的。
停好车,穿过院子,走上台阶的时候,他就闻到有香气,像那些日张阿姨不在的时候锦弦做给他的饭菜香,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很想念那种味道,以至于饥肠辘辘。
还没有拿钥匙,门就开了,锦弦生动的笑容映入眼睑,他有了错觉,以为她会投进他的怀抱,但事实上是她让在一边,用很愉快的声音说:“就知道是你,我赢了。”
看他不解,她低头为他拿拖鞋,说:“我和张阿姨打赌来着,我说你回来了,她不信。”然后她靠近他悄声说:“我听到刹车的声音了,可是张阿姨耳朵不好使,没听到,所以我就赢了。”
她顽皮地向他眨眼,长长地睫毛上像是有无数的星星在闪耀,晃得他心里乱乱地。他饶有兴趣地问:“拿我赌什么了?”
“赌今天谁洗碗。”她扬了扬头发,说。
“看来是张阿姨了!”他配合着她的情绪,杨着眉毛说。
“不,你洗!”
他手一滑,拿出来准备放到茶几上去的手机掉在了地毯上。
两个人同时去捡,不小心头碰到了一起,她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像是对待一个闯了祸的孩子,悄声说:“也就是做给张阿姨看,别害怕,我会帮你的,我就是说说,张阿姨不信,你就当配合我好了?”
他不知道这个女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大了,但是不是和他熟稔了,就代表她对他已没有了戒心?他禁不起这样的诱惑,就胡乱地答应着,说:“好。”
饭毕,他挽了袖子进厨房,张阿姨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和锦弦说笑,哪能当真……”
他淡淡地说:“没事,你出去吧。”
锦弦也过来眨着眼睛推张阿姨,她无奈解下围裙出去,又很担忧地望了一眼苏楚,她是从苏家老宅子清风苑里过来照顾苏楚的,又怎会不知道这个少爷是怎样的娇生惯养,这边犹豫着,已被锦弦含笑推了出去。
锦弦关了厨房的门,把不知道先放水还是先放洗洁精的他拉到了一边,调皮地说:“哪会真让你洗呀,我洗,你看着就好了。”
她系围裙,而后问他:“你没有洗过碗吧?”
他摇头,看她纤细的十指在洗洁精的泡沫里移动,心思恍惚。真正的幸福也许就应该这样,藏在这柴米油盐洗碗做饭之间。
坐在精美的饭店里,吃着大厨做的服务生端上来的饭菜固然享受,但缺少了这种看似平常的生活,日子终究像一把塑料花,好看是好看,但怎么说都是假的。
从厨房出来,锦弦拿了一个纸袋给他,说:“还给你的。”
“什么?”他略略有些明白。
“买手机的钱,我哥去问了价格,让我把钱还给你。”她规规矩矩地说,说实话,五千多块,是他和哥两个月的生活费,她很是心疼,可哥说这个钱一定要还,正因为钱多,才更不能收!
苏楚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手把袋子放到了一边,没有和她客气,而是问:“孟凌东就是你哥?”
锦弦的心放了下去,她还总是担心怕他会生气的,这个人有时候怪怪地,不像哥,就算是生气也是做个样子给她看罢了。
“你知道我哥?”女孩的脸上有了荣耀感。
苏楚也是后来才得知的,路雪把孟凌东的电话给了他,他找人查,很快就知道了孟凌东是锦弦的哥哥。不管别人是怎么评价孟凌东,他对他还是略略有些佩服的,没有任何的背景和势力,一个靠智慧和头脑白手起家的草根平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抢了他未婚妻的人竟然是锦弦口中那个重情重义的哥。
“知道吧。”他淡淡地说:“你哥很能干,锦弦以后可以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
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一会,总是切不到主题,或者他们之间也没有主题,因为他们貌似已经很熟悉,其实终归是有距离的,对他,她始终有一道防线,他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逾越这道防线,女伴他是没有缺过,但恋爱,他没有经验。
静若流光,空若此生,她浅浅而笑,眉梢眼角里的愉悦都只为一个人而开,他在她的世界里是谁,一个观众,或是过客?他无从猜测。
她坐了一会,要走,他没有去送她,而是叫了家里的司机。
司机到了,她站起来,说:“我要走了。”
他“哦”了一声,依旧没有起身,锦弦有点意外,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似乎很高兴地说:“没有发烧!”
他没忍住,笑了出来,站起身,说:“我送你出去!”不管是在和她生气还是在和自己怄气都是徒劳的,没办法,他的人想说不,他的心却向着她走。
司机小王早等车门处,为她开了车门,她上去了,车子发动起来,她又下来了,跑回到他身边问:“我们能做朋友吗?我是说好朋友,像……”她想了一会,终于想到:“像我和路雪一样的,好朋友。”
她在这个城市里并没有什么朋友,苏楚虽然怪怪的,但却是除了哥以外唯一的一个愿意听她说话而她又愿意说给他听的人,她很单纯的想,或许苏楚会愿意和她做朋友,像她和路雪一样的朋友。
苏楚很无语,但还是爽快地答应,说:“好!”或许一切男女关系的开始都是由朋友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