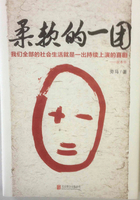玉秀在纺织厂里工作,脸圆圆的,人显得极为壮实。到二十六岁,谈了一个朋友,在折多河边逛过几次路。那个叫国平的男人非常腼腆,动不动就脸红,俩人一块儿逛路,玉秀走在前面,他隔一段距离跟着。玉秀要去看电影,他怕碰上熟人,打死也不去。玉秀对他不满意了,但她知道自己的条件,人不漂亮,都二十六岁才谈上一个朋友。玉秀只好忍着他,这样忍着,玉秀发现了他越来越多的毛病。介绍人说他老实,他的确是个老实人,但老实得过头,生活中没一点儿爱好,要不待坐,要不就傻傻地把桌子擦了又擦。介绍人说他会持家,相处后她觉得那不叫持家,那是吝啬。玉秀讨厌他不自在时爱搓手的毛病,玉秀讨厌他习惯咬腮帮的动作,玉秀讨厌他跟在自己身后,一点儿也不像男人。玉秀说:“你这不像是谈朋友啊,你怕我干啥,我又不吃你。”她主动拉起了他的手,她发现他满手都是汗,还不停颤抖,他脸红得像喝醉了酒,喘着不顺畅的粗气。玉秀不知道他是欲火难忍还是怕羞厉害了,她嫌恶地甩开他的手,悄悄在裤腿上擦掉他的汗。
不过所有毛病加起来,都没有他不想陪她看电影严重。
和国平谈了半年时间朋友,又有介绍人找上门来,给她介绍砖厂的谭明康,玉秀本想说自己有朋友了,猛想起国平的种种讨厌,就答应去看看谭明康,多一个选择也是好事。
星期天下午,她和介绍人跨进了砖厂大院。进了谭明康家门,他正和隔壁的周光福下棋,招呼玉秀坐下,自己继续走棋。她坐边上,看见他神情专注,拈棋子时像拈一枚软蛋那样小心翼翼,他思考时,严肃的表情也像在运筹帷幄全世界的未来。玉秀瞬间就喜欢上他了,一个有爱好的男人是让普通生活飞翔起来的翅膀。
玉秀和谭明康谈起了恋爱,他们手拉着手去电影院门前等票,那时候电影票极为难求,到俩人结婚,他们实际上都没能看上一场电影,不过玉秀喜欢和谭明康一块儿等票的感觉,每一次去电影院,能不能看上电影倒不像紧要的事,就那样候着,那个过程就让她打心眼儿里甜蜜。
婚后谭明康不再去下棋,玉秀也似忘掉了电影,俩人过着瓷实的日子,到生下耀武,谭明康的老母亲千里迢迢赶到康定带孩子。耀武好带,不哭不闹,肚子饿了哼哼两句,吃饱就酣睡。到孩子两岁,老母亲让他们再要一个。谭明康和玉秀商量孩子的事,她觉得再要没啥意思,谭明康也不认为多带个孩子有啥好的。见他们对再要孩子的事不置可否,老母亲心里不受活,整天在谭明康耳边劝,说不管啥时候,人多不吃亏。架不住母亲的劝说,谭明康又给玉秀说这事,不过他换了个方式,他说如果再生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儿,其实也不错。生耀武时玉秀很让一些鸡仔补过,所有壮实的特点都给打了着重号。她脑袋里含糊地现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的形象,扎着小辫,在砖厂大院里跳橡皮筋。
一段时间里,谭明康和玉秀无尽地憧憬着这个不存在的女孩子,他们的想象把她勾勒得近乎完美,玉秀说,她的鼻子得像你。谭明康说,像我不行。玉秀说,我的鼻子不好看,蒜头鼻,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不能有蒜头鼻,你的比我的要好看一些。谭明康说,别的地方可得像你才行,像我就难看了。玉秀说,不行,她身材还得像你,高挑清瘦,这是女孩子最合适的身材。谦逊和美好的想象让他们像陷入了蜜罐子一样幸福得透不过气来,然后玉秀的肚子再一次隆起。
肚子一天天见长,玉秀和谭明康的母亲怄了气,他母亲看着玉秀的肚子说:“这肚子大得老尖,也不散胯,该是个男孩子。”
玉秀说:“不,是个女孩。”
往往婆媳间的矛盾都来自绵延不断的普通生活,在鸡毛蒜皮中一点点磨出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矛盾,要辩辩不明,要理理不清,各人把矛盾小心藏心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点儿小绊,放点儿小鞋,以此来平衡还得持续的日子。老母亲是千里之外赶来带孩子的,原本不和谭明康同住,她用不着把小小的不快掩藏起来,就说:“你看看你肚子,这不就是一个男孩?”
罗玉秀说:“怀男孩的感觉不一样,那时候耀武在肚里,我感觉他踹肚子的力量要强得多,我自己也特别爱吃酸东西,现在这孩子在肚里非常温存,我也只想吃辣的,酸儿辣女,可不正是这样。”
老母亲说:“那不一定,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玉秀说:“这样说来肚尖肚圆也不一定嘛。”
母亲说:“我这把岁数了,不会看错的。”
玉秀说:“我自己的肚子,我自己还不知道啊。”
有了气,两人不再说话,就等谭明康下班回家给判定和支持,偏那一天老等他都不回来。那会儿他正专注地看别人下棋。砖厂大院里的人普遍棋臭,这并不影响他们激烈鏖战,把棋子摔得天响。谭明康站边上看着,想自己久未摸棋,有幸福的生活垫底,他现在有点儿不屑于和这帮臭棋娄子下。
这边等不来谭明康,看看天暗下来,玉秀又特别想吃一盘辣辣的炒青椒,去厨房里翻出青椒,一根一根掐了把,端盆准备去洗菜,出门就见老母亲站在门前张望,老母亲不说话,只把耀武的手递给她,抢了盆就走。玉秀牵着孩子,望不到谭明康的身影。
老母亲端盆子转个弯就见谭明康伫那里看下棋,在他后背猛拍一下说:“你怎么给挪这里了?不知道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吃饭啊。”
谭明康慌忙回家做饭,玉秀跟在他后面,她腆着肚子,像一只企鹅,她不说和母亲争执的事,她只把谭明康忙碌的手拉过来放在高高翘起的肚皮上说:“明康啊,你说说这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谭明康不假思索地说:“肯定是女儿嘛,我们要的就是女儿。”
到一家人围着方桌吃饭,谭明康还没留意到母亲和玉秀无声的对峙。玉秀拈着炒青椒猛吃,辣了,猛喝冷开水。谭明康说:“玉秀,你别吃那样多辣椒,小心对孩子不利。”
老母亲说:“吃吧,吃给谁看啊,再吃也是个男孩。”
谭明康看了看母亲说:“是个女孩呢。”
老母亲说:“咋了?你也凑热闹,我说是男孩就是男孩。”
谭明康说:“真是女孩呢,我们要的就是女孩。”
谭明康这样说,老母亲即刻沉闷不语,吃过一小碗饭就领孩子转出门去。夜晚来临,整个砖厂大院都陷在黑暗中,母亲领着耀武在墙边木墩上坐下来,儿大不中用,小时候是母亲的儿,大了就是媳妇的儿。她想她早该明白这些事理,她只是觉得有点儿伤心,儿子不再信任她这个母亲了,她黯然神伤,两颗老泪不自觉地滑出来,无声地流淌。
三天之后母亲决定回到遥远的大儿子那里去,母亲说她受不了康定的冷,眼见天一天天高起来,秋季已至深处,雪也下到了四周的山巅,她待不惯了。谭明康把母亲送到车站,客车启动时,见母亲从狭小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母亲的目光中有些悲戚,还有些无奈,谭明康怅望良久,心里颤颤地生出些许感慨,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母亲生了他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