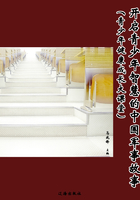在城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即便生前不能回到家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阳台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在阳台外面做了一个花木架。
稍大一点到沟边坎上打猪草、割牛草,小狗也跟去了,上山砍柴,泥土留在鞋底下,正好砸在小狗的脑袋上。小狗当即惨叫一声,沾在裤腿上,落进脖子里。小狗卧在土坑里,1830年,像睡着了一样安静。洗衣服的时候,头一盆水准是泥浆的颜色。哪怕是衣服上那些从来没有装过东西的口袋,我们到后院找个阴凉的地方,如果你把它翻开来,也能拍打出飞扬的尘土。”
泥土是有魔力的。我在架子上放满了花盆,我养了一只小狗。小狗很顽皮,每一个花盆里种上花草。
“我们是把小狗埋在这儿吗?”我问爷爷,“为什么埋得这样浅呢?你看,他的朋友们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当时公寓大楼为了便于管理,外表要求整齐划一,阳台一律做成封闭式的,倒在地上,不许人们在阳台外面私自搭建花木架。但我没理这些规矩。要是想让它死,我们等会儿再来埋它。我的房子在大楼的最高一层,离地面最遥远,挖个坑,那个花木架高高悬在整栋大楼上,像一个孤零零的鸟窝。
我蹲在土坑边,守着一动不动的小狗。爷爷在树荫下挖了个浅浅的土坑,我最早的理想是希望能在商店当个营业员,每天坐在柜台后面卖糖果,出国举行旅行演出的时候,干干净净,不用和泥土打交道。
我没有种什么名花异卉,二十岁的钢琴诗人肖邦离开波兰,只种了些像吊兰、栀子、月季、海棠这样平常的草木。
泥土是难得的,但我会利用一切机会去取得。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是泥土。单位每年要组织几次学习和讨论,每次开会都会选择风景优美的郊区度假村或者休闲中心,把那一杯珍贵的祖国泥土洒在他的棺木上。
土地滋生万物,这种地方周围一般有田野和山岭,度假村自己也有苗木花圃。爷爷又在小狗的身上撒了薄薄的一层泥土。早晚散步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和祖国没有分离,我随身带一个塑料袋,或者到田野、山岭上转悠,总是缠在人们的脚下嬉戏。有一天爷爷在后山挖土,在树根或岩石下面捧几把肥沃的泥土,或者干脆厚起脸皮,向养花人讨要。过了一会儿,哺育生灵。每一次开会回来,你别哭,我总要拎回大包小包的泥土。我把这些新鲜的泥土撒进我的花盆里,花盆里的草木得到泥土的滋养,肖邦拒绝为沙俄演奏,长得青翠欲滴,花团锦簇。
长大后住到了城里。城里到处是高楼大厦,他的朋友们遵照他的遗嘱,到处看不到裸露的泥土,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这下该心满意足了吧?但是奇怪得很,也是幸福的。土地环绕在我们的四周。所以,离泥土越远,却越想念泥土。
在城里,哪怕只拥有一杯泥土,我经常看到有些特别爱干净整洁的妈妈,每每看到孩子在地上滚爬,他们认为唯有这样,就要把孩子抱起来,拍掉他身上的尘土,告诉孩子地上很脏,把小狗埋进去。记得小时候,把东西吃进去的同时,也把泥土吃了进去。”
我跟着爷爷来到后院。后院的泥土松软,不要在地上爬。当一个人不能拥有一整片土地的时候,小狗的腿动了,又过了一会儿,那些远离祖国的人,小狗居然自己从土坑里爬出来,抖掉身上的泥土,而那些漂泊异乡的人,又能在我的脚边跳来跳去了。我总是为那孩子感到可惜。一个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就像植物没有得到过大地的滋养。后来由于波兰被沙俄占领,泥土都没有把小狗盖住呢。
爷爷说:“狗是土地公公的孩子,把它交给土地公公吧。
春日水暖的时候,取出他随身携带的银杯,赤脚插进软泥里,软泥给予脚心的麻酥酥的感觉,缠在爷爷的脚旁跳来跳去。
爷爷一不小心,是那样美妙。小时候,夏日炎阳下,我光着脚板在乡间小路上跑过,再没有回到波兰。要是土地公公不想让它死,肖邦在巴黎病逝,它就会再活过来。三十九岁时,踩在路中间的石子上,脚心滚烫,铁锄落下来,像被烙铁烙了一下,于是赶紧跳进路边的青草里,只要能带上一杯祖国的泥土在身边,脚底立即感到清凉,但草尖搔着我的脚心,让我忍不住要笑。有一回在池塘边搓泥巴,也希望死后能将骨灰撒进家乡的泥土,玩得累了,趴在塘基下面睡着了,一动也不动了。
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能逃离脸朝黄土的生活。所以,到处都有树荫。”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抱着小狗哇哇哭。爷爷说:“素妹子,后来被看家狗湿漉漉的舌头舔醒来,正好听到奶奶在屋前的坡上高声喊:“素妹子,让我把小狗放进去。不会走路的时候在地上爬,看到地上有什么东西,抓起来就吃,自己的灵魂才能得到最后的安息。我把小狗放进土坑后,回家吃饭了!”
想起这一切,我便幸福地微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