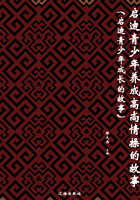Δ我为何要在婚礼上宣布离婚
□君实
爱情,就是在只该看一眼时看了两眼
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遇上了他。
夜幕下的旱冰场,在柔和的橙色灯光下,给紧张地编了一天稿子、头都昏昏沉沉的我一个妙不可言的享受。
我尽情地溜着,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得不少羡慕的眼光追随着我。这时,一位身着夹克衫的青年好像要和我比试似的,动作自由、洒脱,一贯高傲的我,也不由从内心里叫好。
我当然不会示弱,滑动更快,也做出几个最拿手的动作。忽然,我背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凭着直觉,我意识到有异性在一刻不停地盯着我,我回过头去,很不客气地“瞟”了一眼,是他!哼,我暗笑一声,“刷”地一声滑开了。
第二个星期天,我刚滑了一会,就发现有人跟着我,回头一看,又是他。这次他开口了:“你是搞艺术的吧,动作挺规范的。”
我本不想理他,心想,又是半路求爱者吧,这种人可没有少见,他们见面就套近乎。但一转念,这也不礼貌,再看看他的样子,还是很老实的。于是,我告诉了他自己的身分,并请他对我们出版的书提提意见。
他只是谦然地笑笑,接着告诉我,他叫卫京,77届武大哲学系毕业,现在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来,他滔滔谈起外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从书目选择到装祯艺术……
冰场关门时,他问我下星期还来不来,本来下星期要交书稿,不准备再来,可鬼使神差,竟说:“当然,我每星期都来。”
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我早早来到溜冰场,没想到他来得更早。他说:“今天我们来个比赛怎么样?”我什么也不说,一个“箭”似地赶先冲到前去,他一边说狡猾,一边追了上来,刚滑两圈,我一下重心不稳,摔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尖叫一声。
他要用自己的手帕为我包扎,“我自己来”,我本能地一收腿,哎哟,一阵钻心的痛使我不得不把腿伸到他面前。
他为我包扎。我敢说,他的手几乎没有碰我脚一下,据说,青年男女的好感是从互相尊重开始的。当时,我心里涌起一股对他的敬意。这是一个老实、正派,又懂得女孩子心理的小伙子。
他居然叫了一辆出租车。经检验、拍片,我右腿骨折。住院期间,他来过两次,一个星期后,他给我留下他的住址。
当我腿好出院,没想到出版社传开了,说我有了一个美男子,我当然矢口否认。
那天,我来到他的单身宿舍,一进门,他两眼深情地望着我,目光中第一次显得那么温柔、炽热,我预感到了什么。
就这样,我们相恋了。一年之后,我和他决定结婚。
那个充满魔力的夜晚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那天晚上,我来到他正在布置的新房。两人边聊边干,不知不觉快到十点半了,我拿起提包准备走,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柔声问:“别走了,不行么?”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我们还没有登记拿结婚证,也没有举行婚礼呢!
他笑了,好像我说了句大傻话:你说,我们是否真心相爱?是!何必让那些枷锁来折磨我们呢?美国人在这方面就开明多了,我们不要作茧自缚。他说得振振有词。他抱着我,没有再说下去。
我心一酸,便温柔地劝慰他不要这样,并告诉他:“你不懂我们女孩子的心,我越是爱你,就越用心做好准备,然后,把自己郑重地交给你。让我走吧,别生我的气。”
我看着他充满失望、凄切、甚至乞求的眼睛,没有勇气再看。我知道,只要这时他再喊我一声,我就会不由自主了。我狠下心,飞快冲下了楼。
汽车站就在楼下,可末班车刚刚开过。我咬咬牙,准备步行回家,却又回过头望着那扇熟悉的窗口。窗子里透着静谧、诱人的光芒,一个长长的影子在窗前徘徊。我猛地转过身去,不知从哪儿涌上一股力量,飞快地回到了他的身边。
那一夜,令人难忘。
可它也像催化剂一样,将我们之间隐蔽的矛盾激化了。
那是事后的第三天,社长叫我到东北组稿,他知道后说:“为什么派你去,那么寒冷!”我说社里眼下只有三个女的,又唯有我年轻。
“可你是我老婆,你应该听我的!”
我一下就从“恋人”变成了“老婆”。我终于明白了。
“你一天到晚编稿,为他人作嫁衣,又要经常出差。我考虑了很久,你必须调出出版社。”
他完全是一种命令的口吻,他为什么在我面前变成这样?
他大概知道我好强的性格,又换了一种温和的口气:“丽,那天夜里,我们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你不能老是那么固执,只想自己。”
尽管他说得委婉动情,但我感到他换的是一种更猛烈的进攻方式,这不明明暗示着一种威胁吗?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天之后的第45天,我在办公室编稿,他来了。问我能不能请假,他举着一份商调函让我去找领导谈谈。我生气地问:“谁让你干的,我同意了吗?”他说他以为女孩子沉默就是默许。
“可你没有权力这样做!”
“这一点,你比谁都明白。”他嘴角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犹如一个稳操胜券的征服者。
他又一次打出那张王牌,我都觉得替他羞耻,在我眼里,他那张英俊聪慧的脸,第一次变得如此丑陋、愚蠢,或者说像一个面具,而不是富有人性的“脸”。
我明确告诉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该获得对我的绝对统治权!
没想到,他竟然故意大声嚷起来:“请你自爱一点。即使再名贵的花瓶,一旦打碎,就失去原来的价值。”
我相信出版社里在座的人都不傻,他们都知道他那句话的含义。我脑袋轰地一声:天哪,我终于醒过来,他并不满足于对我的剥夺,而且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剥夺”我的原因,以期让我永远属于他。
啊,卫京,我恨死了你!
我要大声地宣布我与他今晚举行结婚和离婚典礼
整整一夜,我没一丝睡意,也没流一滴眼泪。他并不懂得爱,他爱的是我的年轻、美貌,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我想了那一夜的同居,我一直把它看成是我们相爱的开始,也是相爱的顶峰,我不愿说那夜是个阴谋,因为我是自愿的。但现在他开始践踏这种爱,他能值得我爱吗?
但我们仍然准备在“五一”节结婚。请你不要说我疯了,我明白,我比自己什么时候都要清醒。
婚礼在“五一”举行,他的好友同事都来了,还有我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一天,我细心地做了打扮,我打扮得十分漂亮。我想让大家看看,我这个新娘子哪怕是流星似地一掠而过,但却是有光彩的,并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婚礼开始了,第一杯酒斟好后,我第一个站起来,尽量以一种最平静、最从容的声音说:“请大家跟我举杯,为我和卫京的结婚和离婚而干杯!”然后,不管别人如何反应,我一口气把酒喝了。
一杯多苦的酒啊。
即使这时发生地震,也不会比我那句话的震动更大了。还是卫京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猛然抓住我的双臂,目光像一把刀子:“你疯了吗?开什么玩笑?”我沉静地说:“没开玩笑,我这是反复考虑后做出的选择。”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和我结婚?”
我笑了笑,但泪水一串串滚落下来,“我们是今天才结婚吗?”我转向大家说,“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就同居过了,在我的概念中,那就是结婚,而今天,不过是当众履行一个仪式罢了。也许你们会觉得费解,哪个姑娘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呢?可是,我是被迫的,我想借这个场合告诉大家,我已失身了,就像他说的,是一个打碎了的花瓶,不再有‘价值’。不过,请你们相信,我那时完全是出于对他的爱,而今天和他离婚,是他不值得我爱。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做,仅仅是因为我不愿苟且、侥幸而永远被‘爱人’耻笑。假如我像有些姑娘那样,一声不响地离开他,他就会一辈子嘲笑我、羞辱我,把我当成一个小辫子拿在手中到处挥舞。事实上,他已这样做了。我要剥夺他这种可耻的武器,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人们公布我们的关系,最理想的场合和方式,就是在婚礼上。”
当时,我不知道这一举动会给我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但我认了。我想,这不再是因为失贞就要成为他任意摆布、任意践踏、任意嘲笑的时候了。
阿波的死亡婚姻和婚外情
□王子君
我刚上岛的时候,就认识了阿波。那是在一个当杂志编辑的老乡办公室里,阿波来送图片。恕我孤陋寡闻,在此之前,除了从画报上,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拍过如此美妙的图片。我对阿波肃然起敬,虽然是同龄人,可他那名片上,已赫然列出一堆令人惊羡的头衔,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某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会长,等等。老乡更是一个劲地夸赞他,人是如何的质优,才华如何的出众,前程如何的辉煌,说得在座的年轻人个个自惭形秽,女孩子们两眼放光,有勇敢者甚至还思谋着怎样将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俘虏过来。
不料没过几天,阿波来送图片时,将一位美貌女郎带到了大家面前。那女孩子是他的妻子,他们一年前结了婚,双双来到海南。我们均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出色的青年何以这么早就结婚了呢。不过,他们真正是郎才女貌,以传统目光衡量,天生一对。
但阿波岂止是才。朋友们对阿波有一个昵称:阿波罗。他那深邃的眸子,自然拳曲的头发,高耸的鼻梁,真有些太阳神的气韵,俊朗、飘逸、高贵,身材挺拔伟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男子。
听阿波说话,却是没有一点阳刚之气的。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完全是一派温文尔雅的书生气质。比起他来,妻子娜不知要昂扬多少倍,一看,就知这个家庭是属于女权主义范围的。更令阿波头疼的是,老婆时常莫名其妙地吃醋,由吃醋引起猜忌,由猜忌发展到对阿波每日三“审”,最终爆发了家庭战争。最激烈的是后来朋友尽知的那次事件。
那天,阿波出外拍片,临走交待说晚餐不回家吃了,与同行学生小赵干完工一起吃饭。晚餐时,娜刚好路过小赵家,折了进去,小赵说一个下午不见阿波来呀,我一直在等他呢。娜脸上显出乌云,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她想也许在另外的好友家吧,实际上,她心里已有了别的猜想,只是不愿承认。那时,这些刚闯海南的朋友都不稳定,住的地方哪安电话,街头公用电话也极少见,BP机也未曾出现,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上门去找。娜一处一处的去找丈夫阿波,一次一次的扑空。走累了,所有平时阿波有出入的朋友住地找遍了,就是不见阿波的影子。回到家,却见阿波正跷着二郎腿在自斟自饮呢。娜气疯了,哭了起来,骂了起来,质问了起来,她坚决相信丈夫一个下午是与某一个女人在一起的。阿波大惊失色,想解释,没门。闹得天翻地覆、人也疲倦的时候,娜总算停止了歇斯底里,可仇恨的目光却是一点也没有柔弱。这时阿波才有机会说,他在海秀路碰上了足有五年没见面的大学同学,同学也闯海南来了,在一家企业做厂办秘书,说厂里正准备出画册,要找人拍照片,这下可好了,就找阿波。谈得投机,同学干脆请阿波去金融大厦喝茶。但那同学的名字极为陌生,娜不信,说若是真的,你现在带我去见。阿波笑说你“倒丁”(神经病)吗,这么晚了去哪找,工厂在郊区呢。娜便更加认定阿波在撒谎,他是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平时他拍过照片的女人一把一把的,随便约个女人出来不是轻而易举?哼,他那取景柜里的女人!娜又闹。阿波脸色铁青,再也忍不住了,酒杯往桌上一顿:我的朋友同学当中你不知道不认识的还多着呢,我已二十四岁,而你,只与我生活了一年多一点呢。而且你知道,要不是你的热心,你我也成不了夫妻!
阿波说着,突然悲从中来,他紧闭了双眼,不让往事溢满视线。阿波与娜结婚以前,很热烈地与一个女孩相爱过。在是否南下闯海南的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女孩对刚建省的海南特区,没有丝毫的向往之情,她说,你要去海南,我们就吹!阿波顺口答应:“吹就吹!”话未落音,女孩气得晕头转向,十天之内找了个人结婚了。阿波没料到多年的爱情原来是这样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兀自伤心痛悔一番,收拾起行李,更是铁了心的要来海南。这时,娜来了,娜一直在暗恋着他。她巴巴地说,让我跟你去海南吧。阿波看着美丽又勇敢的娜,看着她眼中可以为爱情吃苦的真诚,默默地感动了。他们匆匆办了结婚手续,在蜜月中来了海南。平心而论,娜是遵守了同甘共苦的诺言的,如果不是猜疑嫉妒的毛病,娜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女人。
阿波的话说过火了。待他意识到的时候,妻子的心已经受到了重创。娜突然平静了,她想,自己痴心热爱的丈夫原来是这么看待她当初的追求和他们的婚姻的呀!她以为婚姻早已使他们水乳交融,可亲密的表层下,却潜在着这么冷漠和鄙俗的思想!
从此,我们很难看到阿波和娜出双入对时亲密相偎的情景了,阿波也更加忙碌起来,健硕的身躯常常显出劳累的痕迹,俊朗的面庞有了憔悴的线条。他一个劲儿地赚起钱来,没时间考虑婚姻。
日子在吵吵闹闹、平平淡淡中飞快地过去。我们与阿波见面的次数日渐稀少,只知道阿波的钱赚得很辛苦。股票第一轮疯涨那阵,碰见阿波,阿波大呼“倒霉”“背运”,脸上却仍挂着熟透了的那种淡然的笑意。原来他在那家企业的同学,为了感谢他当年为画册的努力,给他争取到了五万原始股。那时原始股一股一元钱,可是阿波毕竟是个艺术摄影家,尚未有那么多的积蓄,也不懂这些股票将来的价值,推荐给身边的友人,也无人感兴趣,他自己咬着牙买了一万股。股票上市时,那只股票一下长到五元。阿波乐不可支,将股票抛了出去。没想到现在那只股票噌噌噌地往上窜,已经是21元了。这个帐前后一假设,竟是错过了成百万富翁的机会,阿波怎能不后悔不叹息!可阿波毕竟是阿波,最终也只是摊摊手,西方人似的耸耸肩,无奈地往“运气”一词上推:没这个运气,有什么办法。
其时阿波已经下海,开了一家摄影社。问及娜,他很平淡,说她在一家很有名气的大公司做公关部长,收入蛮高,对于传言中娜与公司老板之间的暧昧事实,阿波嗤之以鼻。但他们实际上已处于分居的状态,离婚的话题挂在嘴上,却不可能实施。娜是坚决不会离婚的,她看重丈夫的名分。“就这么拖着吧,只要她过得比我好,就行。”阿波淡然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