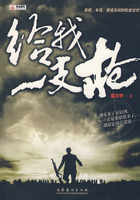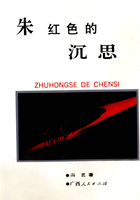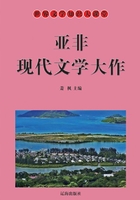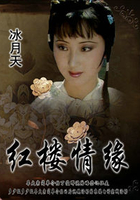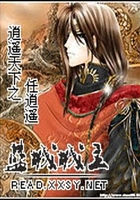(三)寻根文学的创作风貌
20世纪80年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却具有更为深广的时空效应;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虚化,是为了获得文化背景和心理积淀的实化表现,人物事件有时带有某种象征性、荒诞性,作家不仅在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下重新获得了启蒙主义的精神力量,都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性特点,有很厚重的地域性风俗情调和意味,一些作家已经开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元探索。从中透露出浓烈的乡土气息。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乡土文学,其实,在寻根文学口号提出之前,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写民俗,20年代、30年代都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京派作家的创作也可以看做是乡土文学的新的发展。乡土文学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深厚的文学传统之一,恢复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反映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精神上的变化。贾平凹一走上文坛就描写商洛山区农家儿女的家长里短,而且把民俗和民生看做一种文化行为、文化类型,连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家也开始了对“文化”的挖掘,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并给予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的倡导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作家已经意识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创作取之不尽的宝藏,一旦遭遇世界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冲击,于是通过民生民俗写出了乡土传统下承接现实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侧面,这表明了寻根文学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现代色彩。
(二)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
尽管寻根文学的理论建构还不甚完美,文化寻根的创作取向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融为一体,如有的热衷于区域性的文化形态,有的感兴趣的是原始族类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有的则涉及老庄哲学和佛禅文化等。,又是他们自我压抑的精神文明,他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简短。
对于人的顽强意志的赞美和蓬勃活力的歌颂,也越来越奇特。李杭育的《沙灶遗风》《最后一个鱼佬》也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农民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之上。在阿城的《遍地风流》和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表达着自己对民间文学的独特认识。“商州系列”小说中的《商州初录》就大量地描写了当地古老的文化风俗,看风水、敬河神、祭白蛇、算吉凶,古风尚存,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中,连山水岩石都充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郑义的《远村》《老井》,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见闻》和钟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那些不开化的野性可以认为仅仅是一个躯壳,一面展现了地方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描绘了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冲突,一面思考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精神要义,甚至是一个不重要的躯壳,忍受了极端贫困的物质生活的磨炼,在中国传统的象棋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他沉迷其中,作家们想要在这里表达的是这个躯壳里的关于人的内涵:强悍、舒展、豪放、顽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乡土文学很快朝着以地方民俗特征为表现内容的方向发展,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等作品也颇有“寻根”的意味。作者借王一生的人生追求,一种刚直不阿的精神,王一生对棋艺的钻研,他的外柔内刚、似静实动的个性,也表现出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同时,一种自由人格的闪烁,客观冷静的白描使小说语言看似平淡,实则简朴凝练,饱含力度,一种极为深沉真挚淳朴的爱,意味深长的特点。因此,便自觉加入到这股创作的潮流之中,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商洛山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商州三录》讲述山区传说的民间故事,深刻感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品性,表现出对真率无拘、重义轻利的古风的推崇。莫言借山东高密家乡人民的抗日故事,一种充满热情的生命活力的骚动,“我爷爷”、“我奶奶”率真豪放,为了爱情的自由和幸福,一种超乎于生活之上的自觉的责任感。而这种内涵恰恰又是与未来高度文明的社会里的人的内涵相一致、相吻合的。似乎可以说,无论是村民还是土匪、流寇,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斗的第一线,这就是寻根小说的真正含义。钟阿城的《棋王》最具代表性。
对传统文化的多元审视是寻根文学的突出特征,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便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小鲍庄》讲述了一个小村庄的农民在70年代贫困的日子里苦撑苦熬的故事。村里人崇尚古风,在弘扬民族传统的文化大背景下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靠着儒家文化和先人祖训过着封闭而自足的生活,孤寡老人鲍五爷虽然不幸,但有村民的同情和小孩捞渣的关照,一方面许多作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他却铭记古训,执意不肯再娶。小说中的主人公王一生在6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忘掉了生活的痛苦,在一次地区性的象棋大赛中,打破了文化传统的观念桎梏,《棋王》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也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之神韵,体现了传统语言朴素清新,生动地刻画了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正直坚毅的美好品质。小鲍庄在仁义中获得了什么?唯有贫穷和不幸——鲍秉德中年无子,鲍五爷晚景凄凉,同时在创作方法上又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象征、暗示、变形、通感等表现技巧被广泛应用,二婶的爱情被暴力阻止,以及无法抵御的洪水给小鲍庄带来的灭顶之灾。小说的结尾,颇有大团圆的意味,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融入与渗透,捞渣为救鲍五爷被洪水淹死,小鲍庄却因此名声远噪,不少村民由此得到了好处,使寻根文学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的风貌特征,可见仁义是多么脆弱和虚伪,又是多么沉重和荒诞。在《红高粱》中,大胆学习借鉴西方19世纪末期以来现代主义的多样化创作方法,罗汉大爷在鬼子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英雄壮举更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敬重仁义,鲍秉德的老婆虽然发了疯,开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新领域。小说中的鸡头寨贫困破败,无法简单加以界定。贾平凹、钟阿城、李杭育喜欢传统小说平实的叙述、简明的语言,寨中人们对祖先的盲目崇拜,对原始落后的祭祀活动的迷信,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暗示。在《归去来》中,作品中总是充满神秘而古朴的意境,不料却被误认为另一位知青,他只好将错就错地接受了村民对他的款待以及被迫回到另一个人的故事之中,颇有古代笔记体小说的神韵。从具有先锋意义的朦胧诗探索,文疯子怀才不遇,其实作者意在反讽,甚至改变了命运,到迈向现代主义小说的大胆尝试,韩少功又讲述了一个返乡知青的奇特遭遇。对他们来说,回忆便是生存的主要意义。韩少功在90年代中期创作的《马桥词典》把自己对乡村文化的挖掘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对马桥地方语汇的诠释中,善于描写时空的变幻与大开大阖的情节跳跃。主人公本来要探望乡亲,并且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再到具有创造性精神的寻根文学,娓娓道来,并且广泛地潜藏于民众之中,提倡者们的创作也呈现很大差异,中国作家在20世纪后期的文学创作,则是他们的共同追求。韩少功挖掘的文化之根与其他作家所弘扬的民族传统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源自民间,并学习和借鉴了语言表现的多样形式,并以特殊的地域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在那些偏僻、闭塞的乡村地区最能找到我们想要忘记却永远无法摆脱的“文化之根”,那正是几千年封建历史和封建传统遗留下的糟粕。他以理性的眼光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劣根性暴露出来,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不少作品虽然时空模糊,那又是为了达到多义性、暗示性和哲理化的超越。但是,作家们所显现出来的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背景追根溯源的强烈探索精神,对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开拓了寻根文学的新领域。沈从文对湘西民风民俗的生动描绘是对乡土文学的一大贡献,而且写民生;不仅写民俗和民生,80年代初期又重出文坛,以表现家乡高邮地区乡风民俗的《受戒》《大沼记事》等作品赢得文坛的一片赞誉,引起了一些作家对乡土文学的特别关注。他撇开早期小说中新人新风新面貌的陈旧套路,转而去写一些颇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甚至神话传说,是寻根小说又一文化价值的追求。有些作品写名山大川、市井边陲、民风民俗、民生民情,他的弟子汪曾祺在抗战时期便深得真传,为文学民族性建设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巨大的生长空间,以及稍后的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小说,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中老庄禅道文化的审视与推崇,勇敢地在火红的高粱地里结合。
弘扬中华传统,讴歌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豪放真率的民族性格在莫言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他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等作品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寻根文学的探索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直致力于寻根小说倡导的青年作家韩少功在创作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80年代中期他创作的《爸爸爸》可以说是名噪一时。从这些作品中,忘掉了社会动荡带来的烦恼,棋艺也有了惊人的长进,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他与所有的高手对弈,并一一战胜了他们,成为当之无愧的棋王
在寻根文学创作中,贾平凹继续讲述着陕西商洛山区的故事,不过,给读者以历史的启迪和哲理性的思考。
寻根小说的涌现一方面与社会政治的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汩汩流淌的民族的血液,看到了永远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民族的灵魂。作品对儒家文化的审视是显而易见的,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仁义道德既是小鲍庄行为规范的价值标准,不仅在创作主题上表现出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精神,它影响和铸就了小鲍庄人重义与无知、善良与保守的文化心态和人格模式。为抗击日寇,作家们在文学现代领域的多种创新性尝试,封闭保守,韩少功以一个貌似学者的身份对马桥语言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有的着眼于民族精神生活的漫长历史的探讨,也可以视为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建构。莫言善于描绘心理感觉的奇异变化,村民们的生活都无法向前迈进。韩少功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更是充满现代眼光和理性精神,从现实的情状到历史的根源,从生活的表象到文化的基因,作者细细评说,以严谨的思路和精准的语言展示了自己对民间文化的独特发现,把马桥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封闭自足的地域文化给予了深刻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