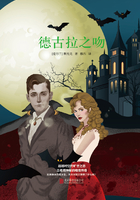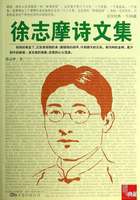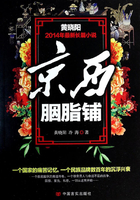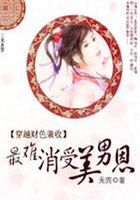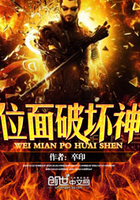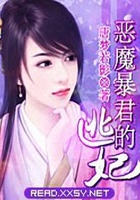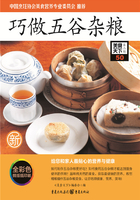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示文艺界要收集民歌,以配合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郭沫若在四川率先倡导,全国各地迅速跟进,形成一场全民文艺的“新民歌运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对新诗创作提出新的要求:“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就是后来文学创作的“两结合”原则。“现实主义”指的是在创作中要紧紧跟上时代生活,描写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浪漫主义”强调的是作家在创作中应该表现出政治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因此社会主义文学不仅要有对生活真实的描写,还应该具有高于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在新民歌创作中,“两结合”的写作方法被广为运用,其中充满激情的夸张和想象,正是这个社会处于亢奋的大跃进时期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形象表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引起文艺界的高度重视。1960年7月,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作了全面的阐述,要求作家用“两结合”的方法描写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形象,将文学创作进一步推向政治革命的轨道上。
2.“阶级斗争”理论的全面渗透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随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策划下,文艺界掀起一股“左倾”文艺思潮,他们以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为名,首先对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发难,称其为“反党作品”,接着又对戏曲界、电影界开刀,将昆曲《李慧娘》、电影《红河激浪》《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甚至《林家铺子》等统统打成“修正主义毒草”,在理论界也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大加挞伐,称他们全都是“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在1963年底和1964年6月,两次对康生、江青等人上报的文艺材料作出批示,称“建国后十五年来,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9—197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99页。批评文艺创作未能跟上政治革命的步伐。1965年10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文艺作家(吴晗)进行政治迫害,预示着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
3.“文化大革命”和“三突出”的创作理论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等人在上海组织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全盘否定十七年来的社会主义文艺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探索概括为“黑八论”“黑八论”包括“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陷入停顿和瘫痪状态,文艺机构被解散,文艺刊物被取缔和停刊,作家、文艺理论家被打成“牛鬼蛇神”。以江青、姚文元为代表的政治野心家把持了文艺界的话语权,提出文艺创作要全面表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体概括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根本任务论”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家的任务就是通过革命英雄的塑造”,表现“灭资兴无”的时代主题;“主题先行论”则要求作家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创作表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的政治革命主题,在当前的政治革命潮流中,那就是描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描写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冲突;“三突出”的创作理论主张人物塑造必须做到“三突出”:“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于会咏《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载《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塑造出“高大全”的社会主义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因极“左”思潮的冲击走向了扭曲和畸形的发展轨道。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对60年代以来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全盘否定,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艺界对林彪、江青等人给文艺创作造成的严重恶果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否定了“四人帮”在文艺界制造的“三突出”创作方法,也修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错误提法,恢复了“双百方针”的文艺政策,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民族性喧哗: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表征
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实践对50年代的内地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讲话》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工农兵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方向,除此之外,“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70页。周扬强调了文学在参与政治革命的建设中要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己任,以大众化的文艺风貌赢得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在艺术技巧上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文艺大众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目标。
(一)英雄传奇:小说文本的传统叙事
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传统章回小说的传奇叙事模式被作为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得到部分作家肯定。30年代后期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向林冰强调用民间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向林冰《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载《中苏文化》1940年第1卷第6期。,这一主张最终在解放区文学创作中被充分肯定并加以实践。部分作家创作出“新英雄传奇”,歌颂抗日游击战士和八路军的抗战英雄业绩,例如柯兰的《抗日英雄洋铁桶》,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工农兵不仅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也成为作者极力赞美的英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政治革命的精神风貌。以歌颂共产主义革命为中心,塑造新时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创作风貌延续到5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模式。作家大多选择革命历史斗争作为创作内容,集中描写政治革命的艰巨和复杂性,塑造出一大批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英雄形象。无论是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较量,还是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都表现出不畏艰险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并且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形成社会主义文学“英雄传奇”的叙事模式。代表作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等。
社会主义英雄传奇在文体形式上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情节结构的曲折性。如《保卫延安》描写延安保卫战从战略撤退到战略反攻,经历了几起几伏的过程;《红旗谱》写农民革命有一个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精神历程;在农村改革小说《创业史》中,蛤蟆滩的农民走向集体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和选择是十分激烈的。革命斗争总是有一个从低潮到高潮的发展过程,但最后迎来的都是胜利和光明。曲折而完整的情节发展形象地演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时也保持了传统小说大团圆式的叙述方法和结构模式。第二,英雄形象的类型化。作家把英雄塑造放到首要位置,着力描写他们参与革命斗争的曲折历程,凸显其坚定忠诚的政治品质,周大勇(《保卫延安》)、朱老忠(《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红岩》)等人物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代表;王金生(《三里湾》)、刘雨生(《山乡巨变》)、梁生宝(《创业史》)等则是农村集体化运动中一心为公的新时代英雄人物,他们的个性特征呈现单一的类型化特点,这与传统小说英雄塑造的方法十分近似。
正是因为叙事模式的“传奇”结构,社会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有着血脉上的联系,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质。
(二)时代歌者:新旧融合的新诗创作
50年代以后的新诗创作呈现新旧融合的特点。一方面,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继续发展,许多诗人运用自己熟悉的艺术方法继续诗歌创作,使自由诗在诗坛上呈现了活跃繁荣的局面,艾青、胡风、何其芳等在50年代中前期成为诗坛上较有影响的诗人,贺敬之还学习借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创作出气势雄壮、节奏铿锵的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学对诗人们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大多数作家转向对民族传统诗歌的学习,民歌体抒情诗、口语体叙事诗大量涌现,诗歌风格明显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倾向,贺敬之的《回延安》是其代表。毛泽东对新诗的态度也无形地影响着一些诗人的创作取向,白话新诗的奠基人郭沫若此时也有意转向格律诗创作,并在50年代后期与周扬一起全力提倡“新民歌运动”,制造了一场以传统格律诗为基本模式的民间诗歌的狂欢运动。绝大多数诗人都受到这一场文学民间化运动的影响,将半民歌、半自由体诗歌形式作为新诗的创作模式,创造出社会主义文学特有的颂歌文学,从歌唱革命领袖到歌唱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文学从精神到形式的重新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创作在新旧融合的艺术探索中取得较大收获的诗人是闻捷和郭小川。闻捷在50年代创作了大量抒情诗,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他在向传统诗歌的学习中融入民间口语,以轻松活泼的诗句描写新疆维吾尔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在对“劳动与爱情”的浪漫书写中,展现了新疆地区独有的民族风情,也拓展了当代新诗的题材空间。郭小川是一个在政治革命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对民族诗歌的音乐之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诗歌写作中,他学习继承了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品质,运用汉语言独有的音节形式创造出“新辞赋体”诗歌,在满怀激情的吟唱中抒发了一个战士兼诗人的豪迈情怀。其代表作《甘蔗林—青纱帐》更是将革命与生活融为一体,借对革命年代的追忆和对革命战友的怀念表达了继续革命的政治激情,其诗歌形式在自我创新中找到一条回归民族文学的艺术路径。
(三)中西杂糅:戏剧创作的民族回归
戏剧创作是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政治革命的大多数文艺作家都曾经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带动了中国文学参与到社会主义革命潮流中。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重大问题上,戏剧创作表现出较强的探索精神,毫无疑问,解放区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为作家的创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就是,将民族传统戏曲加以创新,将五四以来创建的西方话剧形式加以改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64年9月,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新形式。
戏剧改革在50年代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戏曲的改造上,主要方法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戏曲作品的内容进行全面改造,清除其封建主义的毒素。比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孝仁义)和宿命思想,增添新时代政治革命尤其是阶级斗争的主题,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传统剧目的面貌焕然一新,改造取得较大成功的作品有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十五贯》,它们基本保留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形式。
60年代中期,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全面渗透,文艺活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戏剧改革被提升到更为严峻的政治层面上。江青等人不仅对50年代以来的一些戏剧、电影作品全盘否定,还亲自指导京剧改革的“深化”和“创新”,促使戏剧界先后创作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八个样板戏”指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音乐剧《沙家浜》。。这些作品在创作主题上完全转向对共产主义革命历史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颂,突出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吸取了延安民族新歌剧的创作经验,将古今中外戏剧艺术的多种方法融于其间,开创了一种融多种戏剧表现形式(话剧、京剧、音乐剧、舞剧)于一体的“杂糅”式艺术风貌。作为主体艺术方式的京剧唱腔在戏剧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艺术功能,使受众(观众)既能感受到西方话剧的情节冲突,又能欣赏到民族戏剧独特的音乐艺术和表演技艺,因而在民众中获得广泛认同。“样板戏”在文学形式的民族化建设中产生了极为强大的政治功能。
四、现代性沉寂:政治革命思潮对文学主题的覆盖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文学一直与动荡的社会政治相互冲撞,也相互交融。改良政治,推进社会文化变革,成为大多数进步作家文学创作的中心内容。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后,左翼作家一直宣传革命文学理论,使马克思文艺思想不断融合到中国文学现代建构之中。然而,中国政治革命的复杂性又反过来制约了文学发展的现代性进程,在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左翼作家又过度强调文学的政治参与价值,在强调反映论时否定文学的自我特性,导致文学创作主体意识的逐步丧失。自5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中接受了政治思潮的洗礼,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与政治革命同步发展,五四以来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理念被全面消解,作家的主体意识全面消退,文学作品的艺术风貌大多呈现出规范化特征,文学现代性精神逐步转向隐逸和沉寂。
(一)文学主题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