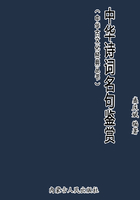作为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另一种文体,30年代的戏剧创作也收获甚丰,作家们学习借鉴西方戏剧的多种表现方法,使20年代以来的创作有了极大的提升。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作品成为此一时期最为优秀的戏剧作品。1934年曹禺发表《雷雨》,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走向成熟。曹禺学习了西方古典戏剧的多种方法,通过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独具特色的戏剧形象的塑造,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新天地。作为舶来的文学形式,戏剧创作在30年代的收获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演进和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明的交融有一种历史的渐进性,古老的东方文明在19世纪后期遭遇到西方现代性的刺痛之后,呈现了极为复杂的交融方式。在得到维新派的有限认可后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率先进入东方文明中,而文化的现代性则遭遇了更多的反对和抵抗,直到20世纪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正式倡导,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纷争不断,使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呈现出艰难曲折的历程。直到30年代,中国文学才开始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现代性表征不断凸显,传统文学的民族性特质成为相对隐逸的一种姿态,它在与现代性冲撞的过程中由初期的对峙逐渐转变为融合性建构,并因此将中国文学民族性传统更加深入地注入新文学的肌体之中。
(第二节)现代性张扬与民族性回归——30—4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激荡
一、民族主义——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被自我确认和不断强化之后产生的心理自豪感,并上升成为政治层面的民族情结,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精神产物。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由于启蒙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封建君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遭到冲击,现代交通缩短了时空距离,成为民族主义形成的现在条件。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这个词来表达“民族主义”的意蕴,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一词意味着包含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是一种历史与时代交融的产物,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历史进程,现代民族理论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产生的现代性、公民性以及建构性。卡尔顿JH海恩斯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一种现代混和和夸大。他把近代欧洲出现的“民族主义”分为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民族主义、政治行动的民族主义和作为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四大类型。参见[美]卡尔顿?海恩斯《民族主义论集》,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6年,第6页。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建设的进程是一种现代现象,正是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和政治的结合,民族主义的出现才有了原动力。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是将自己的集体主权组成能表达政治愿望的国家的公民所构成的团体”。EJHobsbawn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1990p19转引自李明明《当民族主义遇上超国家主义》,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6期。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现代文化出版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催生了民众的民族意识,“被印刷品所连接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语言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以爱国主义为基本形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矛盾张力,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核心内涵,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产生过强大的推进。较为明晰的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军事入侵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也输入了现代的科学文化思想,给古老的中国展示了世界文明的另一面——以科学理性为根底的现代文明成果,使闭关锁国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加剧了民族主义情感的形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尊心遭受重创的同时,也催生了“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民族情绪。在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参照下,一些具有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反观和自省,看清了古老的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差距,产生了亡国保种的民族危机意识。较早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并把眼光投向世界的知识分子当数冯桂芬,他说中国其时“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校庐抗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王韬在游历欧洲之后,更是对西方世界有了全面的了解,在东西文明的比照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存在的严重痼疾:“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王韬《弢园文新编》,朱维铮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页。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作为早期的文化改良主义者,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梁启超《新民议?叙论》,《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4页。,开始将国家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对西方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受到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的影响,第一次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来反思现代国家形成中民族主义的巨大作用:“今日欧洲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所赐?”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20页。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柢)源泉也。”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1号。这是对民族精神的倡导,也是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准确解读。
章太炎作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另一位奠基人,其理论更具有反满排满的种族主义特点。他认为,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要建立全新的中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达到反满排满的目的。章太炎的反满民族主义更多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所谓排满者,岂徒曰子为爱新觉罗氏,吾为姬氏、姜氏,而惧子之殽乱我血胤耶?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而已。故所挟以相争者,惟日讨国人,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术,此则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以此始也,亦必以终。”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2页。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正式标志着中国政治革命的现代转型,即由传统的政权更迭向着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变,以“民族解放”为口号的民族主义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的主潮,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变革是一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文化革命。在一群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进下,西方现代化的多种因素渗透到古老的东方民族土壤中,急速地改造着中国的历史面貌。尽管抱残守缺的晚清统治者们极力想要维持现状,处处以祖先遗训反对维新运动倡导的历史变革,但中国青年一旦呼吸到现代文明的新鲜空气,便再也按捺不住追求自由生活的热情,中国社会的政体变革便水到渠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快速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孙中山革命策略的胜利,一方面也是中国历史整体性变革的内在驱动使然,西方现代文明所激发的民族意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价值的强大动力。此后,中国政治革命的倡导者始终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将政治建设与民族主义的口号联系在一起。20年代国民党对封建军阀发起的“北伐革命”,30年代以统一中国为宗旨的“中原大战”,均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石,占据政治建构中的理论制高点,从而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与辉煌,将中国的政体朝着现代民族政治方向推进。
二、启蒙与救亡: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学的现代主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甲午战争让晚清帝国再遭重创,成为东方后起帝国日本的鱼腩,中国人古老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开始走上变法自强的民族复兴之路。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产生于晚清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是以入侵的西方“他者”为参照而生成的,以后每当民族危机加深之时,这种意识便会被不同程度地激发出来。中国知识分子心怀爱国主义梦想,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唤醒民族意识,改变中华民族长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和民生艰难的历史现状。作家在新文学创作中自觉参与了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将文学活动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融为一体,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和民族主义色彩。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民族意识,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传统文化的深刻浸染,形成了深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二是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激情澎湃的民族解放意识。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激荡,贯穿于他们全部的文学活动中,形成中国作家独特的启蒙主义意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早期作家,从传统文化的历史通道中走来,深刻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肩上承担的历史重负,始终将个人的文学活动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对民族苦难的忧思,另一方面还参与到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的建设中,表达对民族解放的诉求。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他以启蒙主义为观照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审视和探察其保守与腐朽的内在本质,以极为忧愤的情感表达着重建民族文化的忧思,期待以文艺唤醒国民意识,实现民族解放。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中满腔激情地歌唱新生的中国是一位充满朝气的“女郎”,歌唱她“华美”、“新鲜”、“净朗”,在他面对军阀混战的现实真相时,甚至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以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参与到政治革命的大潮中,表达着对民族解放的急切渴望,体现了新文学作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从而形成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与民族精神解放相融合的人文主义主题。早期新文学作家的选择对后来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坚持不懈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特有的以民族解放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特质,这是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相互融合的巨大收获。“就一个独特的现代意义而言,民族主义的到来与下层阶级受到政治的洗礼有密切关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从晚清的梁启超到现代的鲁迅,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始终纠结着民族主义的历史情怀,将民族解放视为整个生命的最高目标,最终引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走上民族解放的历史征程。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全面走上民族解放道路的辉煌而悲壮的历史事件。西方列强的外力刺痛,一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伤痛,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人文化自省和民族解放的“助燃剂”,促使国人努力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蹂躏,走上现代文明的富强之路。“反帝”作为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要旨,与“反封建”同时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双重目标,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民族解放的又一重要使命。从五四运动开始,这一政治主题和历史使命便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不断生发,无论是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都希望借反帝的旗帜来吸引更多的青年参与到政治革命的建构中,民族主义由此成为敏感和热点的话题。1931年9月“东北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陆续爆发抗日浪潮。1932年初,“淞沪战争”爆发,更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抗战情绪;1935年,《何梅协议》签订,北平成为不设防城市,表明民族抗战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各界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于1936年10月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主题由此发生根本改变,以救亡为目标的反帝抗日和民族解放的政治主题成为中国文学活动的又一个重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