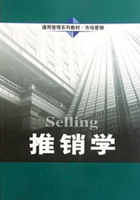我记得,那一天,在惨白桀骜的夏日下,你微笑着对我说:“我已经交了志愿了。我选择了复旦的计算机系。”
我在阳光下,仰头看着你,我的眼中流转的是泪,洋溢着的,是怒。
我听到我自己在心中呐喊我想问:“我呢?那我呢?你可曾考虑到我?”我想问你,你想让我怎么样,只是,我不能。因为我,我不喜欢这样。于是,我咬咬牙说:“你知道的,我要去北大。”
“那很好啊。”你还是一脸的微笑。
于是,我的泪,缓缓的滑过我的脸,我说:“好。是很好。”我逃也似的跑开。
我不知道,你在作决定的时候,是否曾考虑到我?如果你可以放弃计算机,你也可以选择北大,只是,我和计算机,难道,真的是计算机比较重要?又或者,你根本未曾考虑过我,根本这一切就是无从比较的!
八月的天,惨白的光,我有些恍惚。
这样的情景,是我不曾预料的。
在我的想象中,即使是这样的结果,你,你也应该抱住我,对我说:“我们只是分开四年,何况还有假期,你应该相信我的。我相信你会等我。”
然后,我会哭着笑着对你说:“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然后,空气中,会有玫瑰的芬芳和淡淡的哀伤。
只是,你还是没有。你什么都没有说,你只是平静的向我诉说一个事实。而我,只是路人甲,或者路人乙。
刹那间,我只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卑微。我在卑微中不能自已,我一路狂奔。
一点一点的液体,滴落到我的杯中,泛起一点点小小的涟漪。我的心,微微的,在灯光的飘摇中有一点点的颤动。
我想到那个夏天,在那后来的日子里,我是怎样的守着不曾响起的电话,我是怎样,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着,喜悦,然后,失望。
然后,我终于失望地愤怒,我拨通了电话,对你说:“我们分手吧。”
我的心在这边跳跃,我在这边期待着你焦急地询问我为什么,我期待着你从城市的那一端来到我身边,然后关切的问我,你这是怎么了。或者,哪怕是斥责,斥责,你究竟在做什么?我只希望,你知道我的存在,我只希望,你会在乎我的感觉。
可是,你只是在电话的那边,淡淡地说:“好吧。”
我惶惶然的在镜子里,看到一张绝望的,不知所措的脸,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夏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故事。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很委屈。
我依旧期待着去学校,在学校里和你讨论一道化学题,然后,牵手走过长长的林荫道,只是,这一切,仿佛已经都是梦幻。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前,一点一点的模糊起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那么的不真实。
终于忍不住,我倒在桌子上,用发丝,去掩我的脸。
3 相遇James
等到我抬起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孩子,在我对面,冲着我微微地笑。我有些局促的对他说一声Hi。
这是一张看起来有些冷漠的脸,很典型的北方人的脸,有些宽,眉有些粗。他的目光,是柔和的。他对我说:“你是,北大的?”
不意想是这样的开头,于是我说:“是啊。你呢?”
“蓝旗营工学院。”他笑着说。
原来是清华。我在桌子的这一端开始笑。这个名字实在取得很好。
然后,他从身边的书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个通讯录,递给我。我接过来,沉吟了一下,我留下了院系和名字,交还给他。
他仿佛是不经意的翻了翻,然后他对我说:“留个E-mail吧。”然后,依旧交还给我。
于是,我又接过来,继续地写。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一个陌生人那么多关于我的信息,我只是觉得,我愿意,于是,我就写。然后,我还是想到那一张带着些许孩子气的笑脸,我想,如果他在这里,他坐在我的身边,会不会有一些神色的改变?我这样想,嘴角露出一丝笑,于是,我继续写,给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我坐在那里,有一些得意,也有一些愉悦。我喝了一口牛奶,觉得很惬意。
我咀嚼着我的惬意,然后,我看到对面的男生递过来一张纸,上面有姓名、电话、住址还有Mobile,大概因为我还在大一,周围用Mobile的人不多。于是,我看了看他的名字,James,很简单的音节。我拿着那张纸,念出了声,James。
然后,我看到对面的他在冲我微笑,一种宽厚的笑,他对我说:“Annie。”
我看到的手表指向了十一点,我站起来,和他说再见,女生楼,有着十一点关门的优良传统。
于是,他说:“我送你?”
我摇摇头。
然后我听到他说:“那么晚了,小心一些。”
我有一些感动,我说,谢谢。
我微笑着,走进夜色。我心里想,十八岁的最后一天,还有一个多小时。
十九岁的生日,我微笑的,看着镜子里的脸。一夜之间,来不及有所改变,只是,心里,却多了一点沉重。我十九岁了,不复是当年豆蔻枝头的小女生。
转头,我看着床前小小的年历,我看到一个三和一个四。是了,我的生日是三和四的组合。
三和四你可以念做生和世。三三四四是生生世世。一三一四是一生一世。仿佛我生来就一直渴望着生生世世的永久,渴望着三生石上的旧精魂绕过了孟婆汤的蛊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一眼,就可以认出了,原来是你呀。即使不能生生世世,那么,或许一生一世也已经足够。在芸芸众生中,选出了唯一的一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只是三和四,你也可以念作生和死。那么,三三四四是生生死死,一三一四是一生一死。很出尘的禅意。省却了缠绵,人的心就这样的沉静下来,原来一切只是轮回的生和死呀。可是我不喜欢,即使是经卷,我也要读出缱绻。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说的荡气回肠。
我对着日历微笑,想着,该怎样过自己的一天,这有着三和四的一天。
我看到宿舍里,已经没有人。是有课的,我也曾听到闹钟响,只是不愿醒。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呀。这样的放纵,大约也不算过分的。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我坐在床上,想,一直地想。就这样的,过了我的上午。
4 师兄秦杲
我不想就这样继续我的下午,我想找一个人聊聊天,于是,我拨了一个号码,是我的一个师兄,我们从一个高中走入北大。他在物理系,大三,他的名字叫秦杲。他有自己很显著的标志,他有一头很长很乱的头发,和一束很浪漫的胡子,飘飘然的,掩过了颈。他总是带着洞察一切的笑,当他识破了冠冕堂皇背后的东西时,他会一直一直地笑,哭一般的笑,笑得人心里发毛。但是,他对我,是极好的。他总是对我说,Annie,你想想,你再想想。然后,他会叹一口气,说,算了,你不明白的。在他眼里,我仿佛是一个很弱智的小孩。
他从不上课,但是也没有不及格,虽然都是接近不及格。他从不在上午起床,偶尔也会错过了食堂晚餐的时间。他会在夜色中,走的很远,他骑着车子,在北京的街道转悠,他去逛胡同,也混入过天上人间。深夜里,他会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有一些事,有时候,却也没事。有时候他会说,Annie,给我打过来,我电话卡快用完了。
我喜欢这个师兄,我喜欢他在阅尽世事的世故中隐藏的俏皮和真诚。走进北大以来,他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会很自然的把一切问题都丢给他,因为我相信,他能够做好。
家园这个时候没有太多人,三五成群的,有人在这里开会,四人的小桌是天然的会议桌。
我和秦杲面对面的坐下来,他问我:“做什么?”
忽然不想告诉他今天是什么日子,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甚至,他会说,哎,你真无聊。所以我说:“没什么,找你聊聊。”
他开始皱着眉头念叨,他说,“看你神清气爽,不像是有什么麻烦事,小姑娘你今天怎么了?难道是风花雪月过了头,找老夫炫耀?”
我说,“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
然后,他看看窗外,诡谲的笑,他说,“虽然已经立了春,但是北方的春天还没到,油菜花还没开呢,你怎么了?”
我开始装作生气,我转过头去,看着身边的墙。
哎,他叹一口气,说,“那么早叫我起来,就是为了来发呆?”然后他问:“你那个小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不经意的,我又看到了那一张微笑的,带点孩子气的脸,可是,他不是小朋友。我对秦杲强调这一点。
“怎么不是?你们两个都是小朋友。”
秦杲把身子往后面的椅子靠,很惬意的样子,他眯起了眼。然后,他慢慢地说:“我问你,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
我开始变得愤怒,我挑衅地看着他的眼,我说,“当然!”
我回忆着那一天,我要北上,我的父母为我提了一个一个的箱子。我在车站里,彷徨。我是在期待什么,但是,我知道这种期待空洞的可笑。但是,我相信魔法的光辉,所以,我只在用心的期待。
等待,进站,检票。
一切,是不紧不慢的过程,而奇迹也最终没有发生。我不能说失望,因为,也知道,这是奢求,不敢当真。放好了一切,我坐在火车的窗前,看着窗外,那是我熟悉的故乡。我用眼睛触摸着这一切,我想记住它。然后,我看到了一张脸,那一张微笑的,带点孩子气的脸,他正靠在柱子上,依然冲着我,微笑。
我的心,就这样忽而的紧起来,我愣在那里,反复地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恍惚已经让我出现了幻觉。然后,我看到那张脸,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我还看到他向我挥手。
霎时间,我有跳下火车飞奔过去的冲动,只是,瞬间的,车开了,他依然站在那里,微笑的,挥手。而我,开始慢慢的前移,越来越快,那张脸,最终消失不见了。我把手握成了拳,但还是止不住,串串的泪。
因为是离别,有了借口,泪就流得坦然。
我看到有一双手,在我眼前挥动,这是秦杲的手,他开始笑,用那种讥诮的味道,他说,“怎么了?又开始白日梦?”
我转过头,依旧不看他。
秦杲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声音说:“这是你的心结。其实你以后会知道,走过去了,会觉得也不过如此。都是你自己看得太重。”
“好了。”秦杲饶有兴致地转换一个话题,“那么,让我来听听,郑铎溱,他可有Chance(机会)?”
“这是不可能的。”我微笑着,然后加上两个字,“绝对。”
“为什么呢?不够高不够帅,不够卓尔不群,不够有钱?”
“不是。没那么多不够。”我平静地说,带一点笑,“只有一点。他不够天蝎,我爱的男人,是天蝎座的。”
“天蝎?”秦杲开始笑,一种很奇怪的笑,他说,“你的解释够有趣,不过,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不够天蝎?或者,天蝎座的男子,是什么样的?”
“天蝎座的男子,会有一种很霸道的专情,他的脸上会有神秘的微笑。”
“原来你的小朋友是天蝎座的。”秦杲嘀咕着说,然后,他眨着眼睛,问,“难道郑铎溱还不够深情?”
可是,难道这就是深情么?难道,难道只有深情,就够了吗?这一切只是追风逐月,还是深情呢?我有些嗤之以鼻,我微笑。
秦杲肃然地说:“我知道,你现在觉得一切很可笑。因为,对你而言,有人对你好,这太正常。只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是深情,什么是热情。这,很不一样。”
我有些茫然,然后我去看窗外,白茫茫的一片,昨天有雪,今日,是雪霁天晴,天和地却依旧是白,冷然地看着世间变换。
深情和热情?有什么区别呢?
想起进入北大这一年来,生活糜烂的有些荒唐。
通常,自习的时候,会有人过来对我说:“同学,能看看你的书吗?”然后,他会在书里,留下小纸条。或者,更简明的,会有人拿了笔和纸,站到我面前,问我:“同学,可以交一个朋友吗?”又或者,在离开座位不久,会看到桌上又多了一些纸。
走在路上,会有人很自然的走到你身边,然后说:“呀,你很像英语系的那个女生呀。”当然,有时候是英语系,有时候是国关,有时候是中文。
曾记得,在水房,有人一个劲地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浙江。他忙不迭的点头说,老乡啊。浙江哪里?我说,绍兴。他还是忙不迭的点头,说,老乡啊。于是我问,你家在绍兴哪里?于是,他说,我家在四川。
也有些莫名的花,和莫名的小礼品。静静的,躺在楼长那里。我去接过来,放在一边,然后叹息。
不是不兴奋的,有时候,也会觉得好玩和得意。只是走马观花的匆匆,没留下什么印象,我会微笑着说不,或者,有时候,也不用说不,因为,他们可能也不曾记得做了什么。每当我在说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飞旋着那一张微笑的,带一点孩子气的脸。我总是想,他会知道吗?他知道了,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很不争气的,总是想着在他面前证明什么,但是,当然的,他从来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说这些的空间。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通常的,不喜欢让自己太清醒。
我会想象一个他吃醋的场景,正如以往我生日的时候,他会夺走别的男生送给我的玫瑰。然后,然后我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会轻笑着,得意的扬起头,然后,对他说一句,我爱你。
是的,我真的爱你,这些日子,如果,我会对着一个男生微笑,那一定是因为,他有着和你一样的眼神或者是微笑。
双鱼座的女子,总喜欢沉湎在幻想中。如果现实会让我流泪,我就会在幻想中让自己微笑。
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麻烦,当有锲而不舍的男生,在楼下徘徊的时候,我会拉过秦杲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男朋友。
于是,他们会惊讶的,望着我和秦杲,脸上写满明珠暗投的愤怒,鲜花牛……的不解。
秦杲总能够把这个角色扮演的很好,他会说,谢谢你们对她的错爱。现在,我们想去未名湖边走走,你去吗?
他一本正经的说,他的拖鞋噼噼啪啪的响,他的胡子,在那里飘呀飘,我看到小男生的脸,慢慢地黯然下去。
然后,我和秦杲在楼下,在没有人的地方,笑出了泪。
只是,只是郑铎溱知道,秦杲绝对不是我的男朋友,虽然,我在很多时候,都会听他的话。然后,他就一直一直的求着秦杲,让他放一条生路。秦杲总是笑着,不置可否。
“Hi,Hi,小朋友。我发现你越来越会发呆,越来越像我了。”秦杲在一边不满的敲着桌子,警告。
他说,跟你说话呢,不要这样心不在焉。
然后,他说:“郑铎溱的事情,很抱歉,我帮不了。如果,你实在不想给他chance。请你务必要态度坚决一些。不要做得太暧昧。”
只是,只是如何才叫,态度坚决呢?他未曾对我表示过什么,他也未曾有过什么出格的行为,我能够拒绝什么?如果这一切都披上了乡情乡谊的面纱,他不曾揭开,我又如何能够着急的将它掀开?
我为难。于是,我皱着眉,不解的望着秦杲。
“比如,你可以不让他为你做一些小事啊。慢慢地,他就明白了啊。”
“可是,可是他曾说过,如果能帮我打水,他就很开心。”我小声地说,带着一些羞赧,我回忆着当时郑铎溱真诚地,祈求的眼,我的心有一些柔软,我说,“我不忍心拒绝,我不忍心让他失去这样的小小的幸福。”
“当——”秦杲做一个晕厥状,然后他说,“不忍拒绝是吗?那好啊,你就会因为不忍心拒绝,让他牵你的手,然后走进教堂。”
“秦杲!”我嗔怪的。
“Annie,你真的以为这就是他的幸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智商有问题。”
秦杲用手指在桌上敲出节拍:“你以为男人就应该是这样当圣人?人家是有所求的,Annie。这只是一个途径和过程,因为路没有被堵住,所以他会开心,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路上了,他就能够满意。谁喜欢长途跋涉呢?即使喜欢,也是因为目的地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