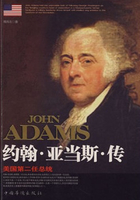1 走不出的回忆
那是十八岁的最后一天。
那一天,不由自主地,拨着那个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记的电话号码,只是,拿起了电话,却绝望地发现,它会在第一时间跳出来,牵引我的指尖。
嘟嘟的微响,是激越的鼓点。如果声音也是有颜色的,它是一种迷乱的斑斓,如果声音也是有意象的,我看到一个女子,白衣白裙,在黑的夜里,赤足奔跑。
鼓点,停了下来。
遥远的那端,有着遥远而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哪位?”
有一点懒洋洋的,带一点童音的稚嫩,有些傲慢有些天真也有些冷,他在那端问我:“哪位?”
仿佛舞台上,激烈的飞旋后的一个造型,定定的,我没了语言。我惶惶的按下电话,我看到那白衣白裙的女子,开始在夜里,凄美的,笑。撒下一地的月光。
我以为我可以的,我以为我是勇敢的。只是霎那间,我又开始了怯懦,或者,可以说是犹豫。那个声音,我已经习惯了在回忆中定格,可是,当它又真真切切地来到身边,我却已经不习惯。因为不习惯,所以我逃避,虽然,是我拨了那个号码。
北方的春天,暖气依然轰轰烈烈,如同窗外纷飞的雪一般轰轰烈烈。
手脚冰凉。站在暖气管前,我抱紧自己,却还是感觉冰冷。
有种熟悉的液体在眼中弥漫开来,无声无息。窗外,成排的大树像做错事的孩子,不吭声,树隙间闪烁着点点纷飞的雪,晶莹的,一闪一闪,讥诮着同样默然呆立的我。
早应该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我为什么,还是这样愚蠢地难以面对?我应该笑着,然后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Hi,你还记得吗?这是我十八岁的最后一天。你说过,要给我一个惊喜。”
只是,只是这一切早在年少的记忆中泛了黄。淡淡的,飞散在江南四月的天。
留不住的,是时光。
点点滴滴的光阴,从眉宇间溜走。时光,是飞舞的精灵,你不在意的时候,她就这样的,悄悄溜走,却窃笑着,种下了断肠的种子,等着你来收。等到你,终于有一天,你终于开始在意时光的流转,她就这样让你肝肠寸断。
“Annie,电话。”虹萦递给我电话,打断了我的回忆。
“冰沁?你好啊。嗯,公演?天啊,我忘了……好的。”
匆匆忙忙的,我将我的回忆甩在身后,我换了鞋子往外走,居然忘了,今天有公演!
因为喜欢一个词“戏梦人生”,所以,我喜欢话剧。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岁。我听导演和我说戏,仿佛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我喜欢那种夸张的宣泄,我喜欢追光打在身上的味道,我喜欢那重重的色彩打在脸上,让自己神采飞扬。我在舞台上肆意的哭和笑,我总是很轻易的,就把自己感动了,然后,我就想和那个世界融为一体。
只是到了中学,就很少有时间能够登上舞台,学业和爱好,当你不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必然,会有人来帮你做出选择。
可是,越是不能,却越是想念。仿佛只有假身于舞台,才有了诗意的栖居。Drama(戏剧),仿佛是我的Paradise(乐园)。现在,我要回到我的Paradise,它现在的名字叫北大剧社。
匆匆赶到办公楼礼堂,一群人在那里忙乱,正在换服装和化妆。我看到冰沁已经换了一身天蓝色的长裙,佩着深蓝的项链和耳环,在人群中,显得光彩照人。
她正仰着头,由一个姑娘给她上妆。不认识化妆的姑娘,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米色的职业装,看着,是上班族。
杨柳看到我进来,匆匆的走过来,指着冰沁对我说:“等她化完了,让那个人给你化。”
我点点头,杨柳风也似的走开。
这是一个小个子的精干女生,是我们的社长,也是我们这次公演剧目《仲夏夜之梦》的导演。她一向雷厉风行,仿佛千军万马中的汗血宝马。如果不是她,这个剧目根本不可能在办公楼上演,因为,据说,在办公楼上演剧社的话剧,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很佩服她,却不大喜欢她。她太凌厉,凌厉的让人有些透不过气。
我去洗手间换了衣服,是一条粉色罩着白纱的长裙,只在霎那间,我看到我身上有了童话的意蕴。
然后,回到那里,走到冰沁身边,那个姑娘笑着一转头,对我说:“等一下,马上就好。”嘴上说着,手却没有停。
冰沁正在上眼影,是紫色系的。她的皮肤本来就很好,但平日里,微微显得苍白些,少了些血色,但只需要淡淡的粉底,淡淡的胭脂,她的鹅蛋脸,就完美得无懈可击了。
她有着鲜明的希腊式五官,所以她就是雅典女郎赫米亚。她将要演绎一个典雅的、紫色的雅典女郎。
上完最后一笔唇彩,冰沁站起来,冲我眨眨眼,眼波流淌,对着我介绍:“雅芳公司的小姐。”
坐下来,上妆,选了粉色系。粉色的眼影和唇彩。眼线,在眼尾的部位略微的往上挑,清纯中带出些许的妩媚。最后,应该有些闪粉,带出些迷幻。化妆的姑娘一边为我加闪粉,一边不失时机夸着我的皮肤,然后问我用不用“雅芳”。
挤挤嚷嚷的,第一幕的演员开始往外走。因为我只出现在第二幕,所以,我只是坐着,然后,等他们走了,才提着裙子,走到台下,仰望着高高的舞台。
我看到,忒休斯是英俊的王子。希波吕忒黑色的短裙短靴,冷艳而高贵。
然后,我看到冰沁的赫米娅,手起手落,是美丽的画。我听到海丽娜赞叹着赫米娅:“狄米特律斯爱着你的美丽——幸福的美丽啊!你的眼睛是两颗明星,你甜蜜的声音比之小麦青青、山楂蓓蕾的时节送入牧人耳中的云雀之歌还要动听。疾病是能染人的。唉!要是美貌也能传染的话,美丽的赫米娅,我但愿染上你的美丽,我要用我的耳朵捕获你的声音,用我的眼睛捕获你的睇视,用我的舌头捕获你那柔美的旋律……啊!教给我怎样流转眼波,用怎么一种魔力操纵着狄米特律斯的心?”
这个赞美,如果是献给冰沁的,却也不奇怪。她的确美丽得耀眼,一种很鲜明冷艳。不知道已经有多少男孩子为了她而黯然神伤。我曾听说,有一段时间,每天,她的车无论停在哪里,车筐里都会有一封信,以玫瑰为缄。当我向冰沁求证这个浪漫故事的时候,她只是微笑着说:“无聊。”
是的,我喜欢冰沁这样高挑的,冷艳的女子,我觉得知性的女子,大抵应该如此,可惜我却有了一张太幼稚的脸。
换幕,去演绎粉色的小仙女,做仙后的侍从,她在仙后出现之前,在台前,可爱地奔忙:“越过了溪谷和山陵,穿过了荆棘和丛薮,越过了围场和园庭,穿过了激流和爝火:我在各地漂游流浪,轻快得像是月亮光;我给仙后奔走服务……”
然后,她会叉着腰,歪着头,用童话中的语调说:“要是我没有把你认错,你大概便是名叫罗宾好人儿的狡猾的、淘气的精灵了。你就是一贯喜欢吓唬乡村的女郎,在人家的牛乳上揭去了乳脂,使那气喘吁吁的主妇整天也搅不出奶油来……”
剩下的,就只是簇拥的场面。我的戏,不多。我是刚刚加入社团的新人。但是,扮演这样一个可爱的小仙女,真的是一点也不难。没有太多的形体语言,也没有太多的表情,导演说,小仙女,只要演出单纯和美丽。可是你太美了!
仅仅是美丽吗?我有的是单纯去挥霍,只是,我不喜欢。我的懒洋洋让我有些漫不经心,一边说着台词,一边想起杨柳对我说过,不要小看了每一个角色,纵然是小丫环,李嘉欣照样风情万种。有些情趣。
是一个喜剧,当然是无情人也成为有情人,有情人终成眷属,靠了精灵的力量。谢幕,相机的闪光在眼前不停地闪亮,在一群不认识的人面前,我微笑着,重复着自己的姓名和院系,觉得头脑很混乱,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何至于!
好容易抽身,在洗手间,看到杨柳。我对她说恭喜。
杨柳笑着,带一点艳羡,是居高临下的恭维。她说:“Annie,刚才央视的几个编导说你很有前途,还有几个问我要了你的联系方式。加油。”
前途?我笑。演艺圈吗?冰沁也曾跟我开过这样的玩笑,只是,这样的纷扰,我,不愿意的。
走出洗手间,看到冰沁和余宏相拥而来,这一对璧人,都是高挑的身材,鲜明的五官,只是,余宏的眼神不似冰沁的清冷,他的眼神很温暖,甚至,温暖的有些暧昧。暧昧的笑伴着他走近,他问我:“Annie,和我们一起去Friday(星期五西餐厅)?”
我摇头,看他们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喧闹着,人都走了,我回到舞台,舞台上只有我自己。
我穿着仙子的衣服,走在舞台上,却没有仙子的感觉。因为,没有灯光,没有观众,最关键的,是没有感觉。
戏梦人生,剧终人散的时候,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茫。
只剩下了时间,依旧在走,依旧是黑。
回到宿舍,把仙子的羽衣放在柜子里,我在床上坐下来,有一点累。于是,我脱了鞋子,翻身上了床,我在床上,抱着自己的小腿,枕着膝盖,缩成了一团,这是我最喜欢的动作,是婴儿在母亲怀里的姿势,真的让人感觉很温暖。
我在脑海里回望我已经走过的十八年。我习惯在每个年纪的最后一天这样梳理自己,生日,总是喧闹的,那是别人的;而生日的前一天,总是静谧的,是属于自己的。
我静静地,回忆着曾经的喜怒哀乐。我看到,我的脑海里也有一个舞台,我在那里,哭或者笑,只是,这出剧目,时间长得有点可笑。
我擅长遗忘,但是我的剧目里,却总是有那么一张脸,带一点满不在乎的笑。
我记得那时候,他总是用手撑住前后的两张桌子,然后,俯下身,对着我微笑。
我记得那时候,他总是习惯微笑着将我画着问号的卷子塞进他的书包,然后在清晨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记得那时候,他总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和我一道走过校园长长的林荫道,然后微笑着和我说,再见。
我记得那时候,他总是微笑着对我说,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还有呢?
我想起了去年的那个七月,日光冷得像冰线。
考完了高考的最后一门,疲惫的人都回了家。
他忽然的,拉住我的手,问:“让我亲亲你,好吗?”他的眼光中,少了一点不羁,有着深深的,深深的Blue(忧郁)。
他说的很平静,带着一点哀伤。
我在惊讶中睁大了眼,我望着他,不知所措。
他望着我,用一种很柔和的眼光,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一种柔和的,宁静的,请求的眼光,然后,他慢慢的低下头去,他说:“可是,可是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啊。”
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平静,但我能听出一种微弱的绝望。我的泪,于是,就这样一串一串地流下来,滴在他的手上,也滴在我的手上,是冰凉的。
他深深地吸一口气,跳下了桌子,不再看我,他说:“走吧,我们回家吧。”
七月的日光,打在地上,闪亮的白。他走在我的前面,大步的,一直没有转身,我在他的斜后方,踏着他的影子,忍住我的泪。
到了学校门口,他停下来,冲着我笑,有着往日的漫不经心和傲慢,他戏谑地拍拍我的脑袋说:“你哭起来,没有笑好看。”
于是,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开始微笑,我知道这个样子很古怪,因为我看到他开始不停的笑,笑得捂住了肚子。在冰冷的七月的日光下,他的笑,像凌厉的风,而且,是白色的风,卷着冰刀和沙砾。
然后,他对我说再见,我也说再见。
走出校门,他往左,我往右。
我不记得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对我说了我爱你。
然而我记得,你最后一次对我说,我爱你,是在什么时候。
我记得那一天的星光,那是七月九日的夜晚,天鹅绒般的黑色天上,星光点点,璀璨如情人的眼。
我和你走在江边的公园,你说你没有想到我会主动来约你,是的。我向来是一个矜持的女孩子,只是,那天的下午,我满脑子飞旋的,是你最后的笑,声声抽在我的心上,每一声,都是心碎的节拍。我不忍,所以,我终于拨通了你家的电话。
在那样的星光下,你拥抱了我,你对我说,我爱你。
然后,你颤抖的唇寻觅到同样是颤抖的我的唇,你的泪,流在我的脸上,我的泪,滴在你的面颊。三年,我们相识三年,却是第一次接触彼此的唇。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轮流地拿着年级的第一,我们在师长面前恪守着好孩子的种种条约,我们做过的最不乖的事情只是逃了一晚的自习,去街边吃一份冰激凌。
而现在,居然是高考,成就了我们的初吻。是第一次,却没有慌乱也来不及羞涩,只有难以名状的无助,或者,可以叫做无奈。终于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
是电话铃,刺耳的,声声紧逼。
跳下床,拿起了听筒,我问道:“Hello?”
“Annie?吃饭吗?”那边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我想象得出电话那端那张带些许谄媚的脸。我知道他是我高中的学长,亦是北大的学生。大四,生物,郑铎溱。
我有一些不屑,却依然是婉转:“对不起,我还不饿。”
“不饿就不吃了吗?那可不好啊。一定要吃饭的啊。不然,胃会不好,还有可能会长胖啊,你知不知道?不信吗?那是因为如果你一顿饭不吃,下一顿饭一定会吃得比以往多,那样热量积累起来,就容易胖了。真的啊……”
絮絮叨叨,感觉不到温暖,却有些怜悯,我想,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只是说:“我过一会儿,自己去吃。”
“这样,要不我给你买过来?你想吃什么?”
依然是锲而不舍,我想象着那一张热切的脸,想象着他可能会有的落寞,我叹一口气,于是说:“不用麻烦了。我等一下要出去。”
“去哪里?要我送你吗?你打水了吗?我帮你打水吧?”
一声紧似一声,带着焦灼。
我拿着电话,怔在那里,我想,如果,如果他现在也在北大,他会怎么样说,可是,他会说吗?我想,他或许会就这样的推开我的门,然后,依然是漫不经心的笑,然后,径自的拿起水壶就往外走,正如当年,他习惯径自的拿走我的试卷和作业。我抬眼,门后的镜子,照出我一脸的茫然。
“Annie?好不好?好?那就这样了。你等我。”
不知不觉间,听筒中已经传来嘟嘟的忙音。原来他,已经挂了电话,依稀记得他说,就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就这样,只是我也不在乎。我于是,就依然回到我的床。我想,今天,我要做什么呢?去哪里?
我在床上冥想,有人敲门,我说请进。
是熟悉的脸,平凡,带一点的质朴,不高,有一点瘦弱。衣服,依旧是深色的运动服,头发很短,在很短的头发下,他的眼睛,满是笑意,他对我说:“还没打水吧?”
我茫然的点头,我望着他,我很想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只是,他尚且没有对我说什么,我又能够说什么?于是,我只是平静的望着他,不带喜,亦不带忧。
他欣欣然的,一把抱起屋内所有的水壶,勉强的,用脚踢开了门,走出门去。
那一种喜悦,让我觉得心伤。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这能够让他快乐,那么也无妨。只是有些事情,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我静静的,看着他,看他卖力的将一个一个满满的水壶排列整齐,我对他说:“谢谢。”
他冲我笑,咧着嘴,憨厚的。
不敢说其他的,我说:“我想休息了。”然后我跟他说再见。
想了很多方法,比如,去看电影,比如,去吃东西,比如,去跳舞。最终,还是决定去雕塑时光,那里有着昏黄的光还有昏黄的书,适合收留所有的情绪。
2 复旦与北大的距离
推开门,很静谧的世界,连喧哗,也是静谧的。
我选一个角落,坐下来,点了牛奶,然后,我走到对面的书架,选书。我想了想,拿起了一叠的漫画。是日本的少女漫画,在这个夜晚,我想让自己轻松一点。
在奶香的氤氲中,我看到漫画中的少女,睁着一双大眼睛,说:“十年?分开十年?怎么可能,又不是在演少女漫画!”
我觉得有趣,剧中剧外,连带着不真实。
离别,离别的滋味是什么呢?是静夜里的泪水,是不经意之间想起的一张笑脸?或者,是锥心的痛沉淀下来的辛酸的浪漫?
我坐在那里。有一些发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