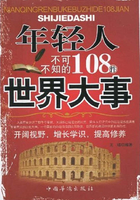雷沃米尔①在他的著 作中有一卷专门叙 述一种称为筑巢蜂的石蜂。我想在这儿重新讲讲它的故事,以作补充。我主要谈一些这位著名观察者所完全忽略的东西。首先我想说一说我和这种膜翅目昆虫相识的过程。
那大概是 1843 年的事,当时我刚刚开始我的教师生涯。从沃克吕兹师范学校毕业几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卡班特拉去教中学附小。我当时 18 岁,接到通知后带着毕业证书和幼稚的满腔热忱就去了。这所学校虽然有着高级小学的头衔,事实上却十分怪异。它像个宽绰的地窖,因为背靠临街的喷泉而显得十分潮湿。为了透进一些光亮,在合适的季节,会把教室的门敞开,墙上有一扇十分狭窄的像监狱一样的铁窗,菱形玻璃镶在铅网格上。四周墙上钉着的木板就是板凳 ;教室里有一把椅子,已经没有了草垫,还有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
早上和晚上,只要钟声一响,近 50 个调皮的小孩子就被送到这儿来了。因为这些孩子还读不懂《罗马史简编》和《历史简编》,所以像当时人们所说的,要专心致志地“好好学几年法语”。罗莎②笔下的那些废物玫瑰都到我这来学写字。这些孩子有年龄小一些的,也有年龄稍大的,他们乱哄哄地集中在这儿,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愚弄这个跟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年龄一样大,甚至还没有他们大的老师。
对于年纪最小的孩子,我教他们读音节 ;对稍大一点的孩子,我就教他们正确握笔,并让他们在膝盖上背写单词 ;对于再大一些的孩子,我则给他们讲解分数以及直角三角形弦的奥秘。而为了得到这群顽皮学生的尊敬,为了针对每个人的能力布置作业,为了让他们全神贯注,为了使他们在这墙壁潮湿的、阴森得令人压抑的教室里不感到厌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话,唯一可利用的工具就是粉笔。
在这些班级里,只要不是用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写的东西,孩子们全都不屑一顾。现在的物理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可在当时是怎么教授这门学科的呢?我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所中学里重要的教学任务是由×××神甫担任的,他是个有名的人物,不想亲自照管绿豌豆和肥肉的事,就把厨房后勤工作完全交付给了他的一个亲戚,自己则全身心地教授物理。
我们来听他一堂课吧。这是一节关于晴雨表①的课。巧合的是学校有一个晴雨表,但是十分破旧,落满了灰尘,挂在墙上一个所有人都触摸不到的高度上。晴雨表的板上刻着几个粗大的字母,写着“风暴”“下雨”“晴天”。
“晴雨表嘛,”这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神甫对他的学生们说,很奇怪,他竟然用“你”称呼他的学生,他说 :“晴雨表是告诉我们天气是晴还是阴的,你看板上写着的‘晴’‘雨’这些字,巴斯蒂安,你看到了吗 ?”
“看到了。”最顽皮捣蛋的巴斯蒂安回答道。他已经浏览了一遍课本,对晴雨表比神甫还了解。
“晴雨表是由一个拱形玻璃管组成的,管里装着水银,水银柱会根据天气情况上升或下降。这管的小支管是开着的,另一个,另一个..
哎,我们干脆亲眼看看吧。你,巴斯蒂安,你个子高,站在椅子上瞧瞧,那根长管子是开着的还是闭着的,我忘了。”
巴斯蒂安站在椅子上,使劲儿地踮起脚尖,用手指拍了拍长管柱的顶部。然后咧开嘴喜不自胜地笑了起来,嘴唇上长出了一层绒绒的小胡须。
“是的,”巴斯蒂安说,“是的,就是这样。长管的上部是开着的。
我能摸到凹陷的地方。”
接着,巴斯蒂安为了把他骗人的鬼话说得有声有色,继续用食指在管的上部捣鼓着。知道他鬼把戏的那些同学都竭力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神甫一本正经地说 :“好了,下来吧,巴斯蒂安。先生们,现在在你们的笔记本上写上‘晴雨表的长管是开着的’,不然你们会忘掉的,连我都会记不清楚。”
物理课就是这样教的。不过,事情有了转机,他们有了一个老师,一个至少还知道晴雨表的长管是闭着的老师。我亲自找来了几张桌子,让我的学生们可以有桌子写字而不必趴在膝盖上乱写乱画 ;我这个班级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最后只好分成两个班。后来我有了一个助手,我让他专门负责教最小的学生,这样,混乱的状态才有所缓解。
在教学内容方面,到田野里教几何,是老师和学生都特别喜欢的课。学校里没有任何教具,可既然我能拿到 700 法郎这么高的薪水就不能浪费了,量地的带子和标杆、卡片和水准器、直角器和指南针,全部是我掏钱买来的。只有一台不如巴掌大却要 100 个苏的小型测角器是学校提供的。没有三脚架,我就找人做。总之,我已经把各种教学器材都配备齐全了。
5 月到了,我们每周都会有一次离开阴森森的教室,到田野里去上课。这真是一个令人无比快乐的日子。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扛起那三支一束、三支一束的标杆,他们以此为荣耀,因为那是象征着渊博学识的几何杆,经过城市时,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其实,当我谨之又谨、慎之又慎地扛着那台最精密、最昂贵、价值 100 个苏的量角器时,也会不由得产生某种自豪感。我们准备测量的是一处尚未开垦的平原,遍地是卵石,当地人称之为“秃地”。那里没有绿篱和灌木丛,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监视我的学生 ;还具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我不必担心有绿杏子分散我的学生们的注意力。这个平原十分辽阔,只有盛开着的百里香和圆溜溜的石子儿。在那个空旷的场地上,我可以设置出各种各样的多边形;也可以用任何方式把梯形和三角形结合起来。在那儿,要想测量平时走不到的距离,就像走 0.5 米路那么容易 ;就连一座破旧的房子或鸽子棚都可以展示出它们的垂直线,从而让量角器有了用武之地。
第一次做这样的活动时,我就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我派一个学生到远处去插标杆,可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很多次,每次弯下身子,又直立起来,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然后又弯下,连对齐标杆和记号的事儿都忘到脑后了。另一个负责收测杆的学生忘了收铁叉,却拣回来一块卵石。第三个学生不去测量角度却搓起了一块泥巴。我还发现,大多数学生都舔着一根麦秸。多边形安安静静地摆在那儿,对角线也没有画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
我走过去一看,全都明白了。学生们从小就喜欢四处搜索,仔细观察,老师不知道的事儿他们早就知道了。在这块秃地的石子上,有一种大黑蜂正在筑窝,窝里有蜜,我的测量员们打开蜂窝用麦秸把蜂房里的蜜洗劫一空。他们的做法让我知道,蜂蜜虽然很黏稠,却是可以吃的,连我也吃出滋味了,于是我跟着他们一起寻找起蜂窝了。过一会儿再量多边形吧。就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了雷沃米尔的筑巢蜂,可我对这种昆虫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谁描写过它的历史。
这是一种美丽的膜翅目昆虫,一对翅膀呈深紫色,穿着一袭黑绒衣服,在阳光普照的百里香丛中,它正在卵石上建造着粗陋的窝。它的蜜替代了枯燥乏味的指南针和直角器,给孩子们带来了乐趣,这让我印象深刻,于是我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它的情况。我的学生们教给我的,只是用一根麦秸把蜜从蜂房里掏出来。很巧的是,书店里正卖一本关于昆虫的名著 :德 · 卡斯特诺、布朗夏尔、吕卡合写的《节肢动物自然史》①。
书中图文并茂,令人爱不释手。可是,咳,太贵了!啊!价钱真贵!就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来说,我那 700 法郎的丰厚收入是根本无法两者兼顾的,我在这方面多花了一些,就必然要在那方面省下来。不管是谁,凡是靠科学谋生的人都只能这样平衡生活。这一天,我狠狠地挥霍了一次,我把一个月的薪金都拿来买了这本书。经过这笔大开销后,我要精打细算才能弥补上。
我一口气把书读完,就像俗话说的“狼吞虎咽”。我从书里知道了那种黑蜂的名字,并第一次知道了关于昆虫习性的细节,我还发现了雷沃米尔、于贝尔、杜福尔这些在我看来无比荣耀和敬重的名字。而当我第 100 遍翻阅这本书时,内心隐约有一个声音轻声对我说 :“你也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昆虫历史学家。”啊,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幻想,现实是怎样的呢!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喜忧参半的回忆放到一边,回到我们黑蜂的丰功伟绩上来吧。
Chalicodolne,原意是用石子、混凝土、灰浆造成的房子,用这个名称代指膜翅目昆虫,是因为它们造窝的建筑材料与人类的建房材料十分相似。这种表达方式,除了那些不懂希腊语精髓的人会觉得奇怪之外,真是太恰如其分了。这些昆虫的杰作是用泥水匠的工艺建造的,只不过它们的技能比较低劣,更擅长打垒构筑物而不是砌石工程。因为在当时的科学分类对它还没有准确的定位,所以雷沃米尔在写作许多文章时也对它知之甚少,就用它的建筑物给它命名,把这些垒土的建筑者称为筑巢蜂。这简直太绝妙了,只用一个词就把这种昆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这种蜂在我们家乡有两种 :一种是高墙石蜂,雷沃米尔已用出色的语言介绍了它的历史 ;另一种是西西里石蜂。后者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埃特拉地区所特有的,不过,在希腊、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地中海地区,特别是沃克吕兹省也能见到这种蜂。在 5 月份的沃克吕兹,它是最常见的一种膜翅目昆虫。高墙石蜂雌雄性的颜色不同,一般情况下,一个观察新手看到它们从同一个窝里出来时会十分困惑不解,起初甚至会以为它们是不同类的昆虫。雌蜂身披黑绒衣服,长着一对深紫色的翅膀;雄蜂身上披的不是黑绒,而是娇艳欲滴的铁红色绒毛。
西西里石蜂个子小得多,雌雄两性的颜色差异不大,它们的服饰相同,只是混杂着不同的棕色、深红色和灰色。此外,它们的翅膀末端在深色的底色上略微呈现出淡紫色,跟前一种石蜂那丰富的紫红色有些接近。这两种石蜂都是在接近 5 月初的时候开始工作的。
雷沃米尔告诉我们,生活在北方的高墙石蜂,通常在阳光普照的、没有涂抹泥灰的墙上筑窝。因为一旦泥灰脱落,蜂房就会岌岌可危,所以它只把窝建在牢固的基础上,建在坦露的岩石上。我在法国南部也看到过石蜂采取类似的措施,我们这儿的石蜂大多不会利用砌墙的石块而把窝建在另一种基础上,这其中原因我一直想不明白。它最喜欢的支座是一种拳头大小的圆卵石,就是冰川一泻而下时覆盖了罗讷河谷台地的卵石。膜翅目昆虫这么选择也许是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卵石 :一切不太高的高原,一切长着百里香植物的干旱的土地上,全都堆满了黏结着红土的卵石。在河谷中,石蜂还可以利用那些被巨流冲击下来的石子。比如在离奥朗日附近,石蜂最喜欢的是埃格河冲积地,因为当河水退去时,河床上会铺满一层圆石头。如果实在找不到卵石,筑巢蜂就随便把窝砌在一块石头上,比如田边的或围墙上的。
西西里石蜂的选择范围更广泛,它特别把家安在屋檐的瓦片下。
在屋顶的飞檐下,春天一到,它们就一群群地赶来筑窝,砌好的窝代代相传,并且逐年扩大,直至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我曾见过一个建在大棚瓦面下的窝,有 5 ~ 6 平方米那么大。正在筑窝的一窝窝蜂四处乱飞,一边干活儿,一边嗡嗡乱叫,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高墙石蜂也喜欢在阳台下面废弃的窗洞里筑窝,假如是百叶窗就更好了,便于它们出入。这是群英聚集的地方,成百上千的工人在那儿劳作。假如西西里石蜂只有孤零零的一只(这很常见),它就会把窝随便筑在某个角落里,只要那儿地基牢固,并且足够温暖就可以。至于地基的材质,它们根本不介意。我曾看到西西里石蜂有的把窝建在了光秃秃的石头上,有的建在了护窗板上,有的甚至建在了棚子的方格玻璃上。对它们来说,唯一不合适的地方就是我们房屋的泥灰墙。西西里石蜂跟高墙石蜂一样审慎,在它们看来,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把窝建在不牢固的支座上,因为那样蜂房就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西西里石蜂总是变换筑窝的根基,至于它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它的房屋是用泥浆建造的,十分沉重,应该以岩石为根基才可靠,可它却建在了一根树枝上,悬挂在半空中。无论什么灌木,篱笆的小灌木、英国山楂花、石榴树、铜钱树,它都可以用来做底座,而这些底座通常离地一人高。如果把窝建在绿色橡树或者榆树上,那就更高了。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它们挑选像麦秸一般粗的树枝,然后在这细小的基础上用泥浆建造房屋,这泥浆跟它们在阳台下或者屋顶飞檐处的建筑材料一样。筑完的窝是一团泥,树枝则从中横穿而过。一只蜂造的窝有杏子那么大,而当几只蜂一起筑窝时就会有拳头那么大 ;但后一种情况并不常见。
这两种石蜂使用的建筑材料完全相同 :在石灰质黏土中添加一点儿沙,用口水粘住。石蜂不愿在潮湿的地方造窝,尽管潮湿的地方更便于工程的建造,并且可以节省很多搅拌泥浆的唾液。它也不用新鲜泥土来造房,这就像我们的建筑工人拒绝裂开的石膏和受潮的熟石灰一样,因为这种材 料的水分饱和度较高,牢固得不够好。
它们需要的是干土粉,这种土粉能够快速吸收唾液,因为唾液里富含蛋白质,所以这土粉就像某种速凝水泥一样,像我们用生石灰和蛋清做出来的油灰。
在人来人往的石灰质卵石路上,经过行人的踩踏和车轮的碾压,路面变得十分平整,好像只铺了一整块石板似的,这是西西里石蜂最钟爱的采石场。石蜂的窝不论是建在篱笆中的一根树枝上,还是在农家屋顶的飞檐下,它都会到附近的小径、路边、公路上寻找建筑材料,从不会因为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牲口的打扰而丢下工作。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下,路面泛着白光,可石蜂仍然在热情洋溢地工作着。在专门从事建筑作业的农场和充当沙浆搅拌场的公路之间,泥蜂嗡嗡地叫着,往往返返,连续不断,你来我往。工人们就像一溜烟似地在空中快速地飞来飞去。飞走的石蜂带着像射兔子的铅砂那么大的沙粒离开,飞来的立即停到最硬最干的地方。它们全身颤动,用大颚刨啄,用前腿扒拉,把采来的泥沙放在牙齿间搅动,用唾液搅和成一团匀称的沙浆。
石蜂是多么热爱劳动啊,它宁愿冒着被行人踩死的危险,也不愿放弃它的工作。
高墙石蜂与西西里石蜂截然不同,它喜欢孤独,喜欢在离群索居的地方筑屋,很少到熙熙攘攘的路上,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离它们的筑窝地点太远了吧。只要在附近能找到适合筑窝的卵石以及含有许多砾石的干土,就足够了。
石蜂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筑一个新窝,也会充分利用旧蜂房,把旧窝修理翻新一遍。我们先来看看前一种情况。
选好卵石后,高墙石蜂用嘴衔起一团沙浆放在卵石上,做成一个圆垫子。它用前腿,尤其是它的首选工具—大颚用来加工材料,一点儿一点儿吐出来的唾液使这材料保持着很好的可塑性。为了巩固黏土建筑物,石蜂镶上了一颗颗扁豆大小的带棱角的砾石,但是仅镶在外面的软土块上。接下来,它以这第一层石子为基础,一层层垒上去,直至蜂房达到它所要求的 2 ~ 3 厘米的高度。
我们从事砌石作业时是先把石头垒起来,然后用石灰粘住。石蜂的杰作与我们的建筑物不相上下。为了节省劳动力和沙浆,膜翅目昆虫使用体积庞大的卵石为材料,这对于它来说无异于琢石。它细致地一个一个挑选。这些石头又坚又硬,几乎都有棱角,它把它们彼此咬合拼接在一起,互相支撑,构成了一个建筑物牢固的框架。一层一层沙浆毫不马虎地浇在上面,使得卵石十分平整。这样,蜂窝从外观上看,十分粗劣,天然石头凹凸不平、参差不齐 ;可是内部要求精细,以防止伤害幼虫娇嫩的皮肤,因此它涂上一层纯浆的泥灰。此外,内部的涂层也是马马虎虎的,用抹刀随便抹一下而已。所以当幼虫吃光了蜜浆时,必须自己造个茧,将自己住所那粗糙的内壁挂上一层光滑的丝质壁毯。
相反,条蜂和隧蜂的幼虫不结茧,所以它们把蜂窝内壁涂抹得十分细致,就像经过精磨细琢那么光滑。
窝的形状因支座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但轴线几乎都是竖直的,并且洞口都朝天,这样,液体的蜜汁才不会流出来。如果建在横的平面上,形状就会像个圆形小塔 ;如果建在垂直或者倾斜的平面上,它就像半个一分为二的顶针,而那个作为支座的卵石就把窝的墙壁堵得密不透风。
蜂房建好后,石蜂就开始储备食物了。蜂房附近的各种花,特别是点缀在 5 月间形成的冲积平原上的金灿灿的染色木花,为它提供了甘甜的蜜汁和花粉。它回到窝里,嗉囊里充满了蜜,黄色的腹部下面沾满了花粉。它先是把头伸进去,过一会儿,浑身一抖,蜜浆全部吐出来了。嗉囊清空之后,它就从蜂房出来了,旋即又钻了进去,不过这次是倒着进去的。现在,它正用两条后腿刷着肚子的下部,把身上的花粉刷下来。紧接着,它又飞出来,先把头伸入蜂房。这次它是要用大颚当勺,把蜜浆搅拌均匀。这种搅拌作业不是每次采蜜回来都要做的,而是一次比一次间隔得久,只有当材料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时才进行。
当粮食装满了半间蜂房时,也就储备够了,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在蜜浆的表面产卵,然后把蜂房封闭起来。石蜂说干就干。围墙是一个纯蜜浆的盖子,从周边到中心逐步造起来。我发现这项工作最多两天就干完了,除非这期间天气不好,下雨或者多云都会阻断它工作。然后石蜂背靠着第一个蜂房,开始建造第二个蜂房,并以同样的方式储备粮食。第三个蜂房、第四个..一个接着一个,储备好食物、产下卵、把蜂房封住,然后再盖下一个蜂房。工作只要开始了就会不停地进行下去,直至完全做完为止。但是石蜂总是把前一个蜂房的建筑、备粮、产卵和封闭四项作业全都完成后,才开始建筑下一个蜂房。
高墙石蜂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在选好的卵石上筑窝,它似乎并不喜欢与别的石蜂为邻,所以在同一块石头上很少有毗邻而筑的蜂房,最多也只有 6 ~ 10 个。那么,一只石蜂的窝里是不是最多只有 8 只幼虫呢?或者说,这只石蜂将来会到别的卵石上为更多的子女筑窝吗?如果它想产卵,这块石头有足够大的基座可供它再筑新蜂房;这儿有十分宽绰的地方让它盖新房,它不必另寻他处,不必离开这块对它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指掌的卵石。因此我认为,石蜂的家庭人口不多,完全可以安置在同一块石头上,至少在它筑新蜂窝时是这样的。
一块卵石外层筑有 8 ~ 10 个蜂房组成的蜂窝群,十分牢固;但是蜂窝的墙壁和外盖的厚度最多只有 2 毫米,当气候恶劣时,似乎不足以保护幼虫。蜂窝筑在露天的石头上,没有任何遮挡。在炎炎夏日里,蜂窝的每个蜂房都成了闷热的烘箱;到了秋天,冰凉的雨水渗入又会让蜂窝慢慢腐烂;然后冬天的严寒将使蜂窝没被秋雨侵蚀的部分一块块地剥落。即使是水泥十分坚硬,能经得起所有这些因素的摧残吗?
即使能经受住,那隐藏在薄薄洞墙里的幼虫能经受得住夏天的炎热和冬天的严寒吗?
虽然石蜂并没有进行过这些逻辑推理,但它的行动是十分明智的。
所有蜂房筑完以后,它在整个蜂窝上用一种防水防热的材料砌了一个厚厚的罩子,这样既防止了潮湿、热浪,又抵挡了严寒。这种材料就是用唾液搅拌泥土而成的灰浆,但这一次灰浆里没有掺杂小石子。石蜂把一小团一小团灰浆用镘刀一下一下地涂抹在蜂房外层,蜂房完全罩在了这矿物盖子里。涂好罩子的蜂窝就像一个粗劣的圆穹形建筑物,大约有半个橙子大。表面看去,人们会以为这只是一团泥,假如把它摔在一块石头上,蜂窝会裂开并且立即变干。从外部看,一点也看不出里面有什么东西,根本不像蜂房,也看不出任何施工的迹象。在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人眼中,这只不过是不经意间遇到的一个土疙瘩。
这个大罩子跟我们的水硬性水泥一样,很快就会变干,于是,蜂窝俨然成了一块硬石头。如果没有足够锋利坚韧的刀,是一点也破坏不了这个建筑物的。最后必须指出,蜂房最后的外观跟原来的样子简直毫不相干,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认为,最初用石子铺面建成的那个宛如标致小塔的蜂房,与最终这个像一团泥一样的圆穹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建筑。但是如果刮掉外面的这层水泥层,我们就会发现,里面的那些蜂房和蜂房的细石层完全能辨认出来。
高墙石蜂更喜欢利用那些损坏不严重的旧窝,而不是十分喜欢在陌生的卵石上建造新窝。圆穹状的窝建造得十分牢固,所以多少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只是里面凿了一些圆洞,那就是上一代幼虫居住的房间。这就是它最理想的住所,它只要稍加修补一番就可以了,既省时又省力。因此高墙石蜂总寻找这样的旧窝。只有在找不到旧窝的时候,它才决心建造新窝。
从同一个圆穹形的窝里走出来很多居民,它们是兄弟姐妹,红棕色的雄蜂和黑色的雌蜂,都是同一个石蜂的后代。雄蜂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什么活儿都不干,它回到土房子里来只是讨好女士们,根本不在乎被抛弃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它们想要的是花蕊中的花蜜,而不是需要在大颚中咀嚼的灰浆。一个家庭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的肩头。这所房屋,这个旧窝遗产,将归它们中的谁所有呢?它们是姐妹,享有平等的遗产继承权。我们的司法摆脱了上古的束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能会判定长子享有继承权。可是关于所有制,石蜂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理解,它们认为权利是归第一个占有者的。
所以在产卵的时候,石蜂遇到一个适合它的窝就会强占下来,在那儿定居;而在它之后到来的泥蜂,不论是它的邻居还是姐妹,都别想跟它抢,否则就是自讨没趣。因为在它的穷追猛打下,后来者很快就会被赶走。圆穹上的那些蜂房半张着嘴,就像一口口井似的。它现在只要一间房就够了,可是石蜂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其余的蜂房以后可以用来装别的卵;所以它格外谨慎、一丝不苟地监视着所有的蜂房,一切不速之客都休想留下。所以,我从未见过两只筑巢蜂同在一块卵石上劳作的情景。
现在石蜂要做的工作很简单,它只需检查旧蜂窝的内部,找出需要修补的地方就可以了。它把挂在墙壁上残碎的茧片扯下来,把上一代居民戳破穹顶穿出蜂窝时扒拉下来的土屑清扫出去,把损坏的地方涂上泥灰,把洞口修补一番,这就是全部工程。做完这些以后就是储备粮食、产卵和封闭蜂房了。当所有的蜂房像这样一个个装好粮食、产完卵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只需再对整个蜂窝的灰浆圆罩子进行一番修理,就一切工作都圆满结束了。
西西里石蜂不喜欢孤独的生活,需要和很多同伴在一起。它们常常是几百只,甚至几千只一起,在草料棚的瓦片或屋顶的飞檐下定居。
这可不是有着共同利益、一致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群居;只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罢了,大家其实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总而言之,这是一群毫无章法的劳动者,只是因为数目众多、劳动热情较高,才使得它们看上去像一窝蜂。它们所使用的灰浆与高墙泥蜂的一样,都是既坚固又防水,只是更细腻一些,没有掺杂石子。最初,它们使用的是旧窝,把所有旧房间修补一新,然后储备好粮食,密封起来。但是旧窝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西西里石蜂每年都以急剧的速度增长着,灰浆圆罩下的住房日益短缺。于是,它们根据产卵的需要,在旧居的表面上建造起了新蜂房。这些新蜂房呈水平或者接近水平横卧排列,挨挨挤挤在一起,毫无秩序可言。每个建筑者可以随意选择建筑地点,只要不妨碍邻居就行;不然的话,受到干扰的石蜂会大喊大叫提醒它注意秩序。因此各所蜂房都是在一个大工地上随意堆起来的,工地的布局毫无整体性。蜂房就像一个沿着轴线切开一半的顶针,它的一部分围墙由相邻的蜂房或旧窝的表面构成。蜂房外表粗劣,露出彼此重叠、有许多结节的砌缝,这就是一层层的灰浆。蜂房内部,墙壁虽然平整但并不光滑,幼虫将来要用茧来克服墙面粗糙的缺点。
就像前面提 到的高墙石蜂那 样, 西 西里石蜂 每建 好 一个蜂房,就会立即储备粮食然后把 蜂窝封闭起来。5 月份的大部分时间, 它们都 在做着 这样的工作。 最后, 所有的卵都产下来了, 石蜂们不管这些卵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会联合起来给这个蜂房群做个遮盖物。于是,一个厚厚的灰浆层弥补了所有的缝隙,把全部蜂房都遮盖住了。最后,这个蜂窝的形状就像一块干土板,很有规则地隆起,中间部 分是 蜂窝最初的核心, 稍微有些厚; 边 缘处 是一 些新 蜂房,比较薄。蜂窝的长度不一,这是因劳动者的数目,也就是第一个窝建造的年龄而定。有的窝还没有巴 掌大,有的则占据了屋顶飞檐的大部分,有几平方米大。
西西里石蜂单独劳作的情况也很常见,它们在废弃的窗户外板上、石头上、篱笆的枝丫上筑窝的方式跟高墙石蜂一样。比如,当它们在枝丫上建窝时,会先用泥灰把蜂房的地基牢牢地粘在细窄的支座上,然后搭一个塔形建筑物。完成第一个蜂房备粮、密封的工作后,下一个新蜂房就紧接着筑起来了。这时,蜂房的支座就不仅是枝丫,还有已经建好的工程。6 ~ 10 个蜂房就这样一个挨一个地聚集在一处。最后,一整块灰浆罩子把所有的蜂房连同建筑的枝丫都罩了起来。于是,蜂窝的支撑点就坚不可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