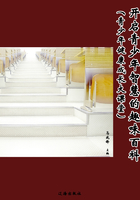砂泥蜂在白天已经过去大半的时候才开始挖井,挖好后用一块石板当盖子盖在井口上,然后它就抛下它的住所,到花丛中徜徉去了。可是,虽然它之前对挖掘的地点并不熟悉,并且它通常同时有好几个窝,可第二天却能带着毛虫返回到它前一天挖好的洞里。虽然泥蜂的洞口已被沙土堵塞,跟黄沙混为一团了,但泥蜂还是会抱着猎物准确无误地停落在自家门口。我无论用眼睛搜寻还是凭印象寻找,都找不到洞口的位置 ;可是昆虫的眼力和记忆却总是屡试不爽。看来昆虫身上有某种东西比单纯的记忆更有用,那就是一种对地点的直觉力,我们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能力,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暂且称之为记性吧。不知道的东西是不可能有名称的。为了尽可能把昆虫的心理弄明白一些,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将在下面进行说明。
我的第一个实验对象是捕捉方喙象的栎棘节腹泥蜂。在上午将近10 点钟的时候,我在同一个斜坡上的同一个蜂群里抓来了 12 只雌节腹泥蜂,当时它们有的正在挖掘,有的正在往洞里运粮食。我把每个俘虏都单独放在一个封闭的纸袋里,然后统一装在一个盒子里。我走到离窝大约 3 公里的地方,把栎棘节腹泥蜂放走,为了易于辨认,我用麦秸蘸着一种不会褪色的颜料,在它们的胸部中间点了一个白点。
这些膜翅目昆虫被放出来以后,分散着飞到了四面八方,这儿、那儿都有,但是刚飞出几步远,就在草茎上歇息起来,用前腿揉揉眼睛,好像已经很久不见天日而被阳光刺到了眼睛。不一会儿,它们又先后起飞了,可是竟然一致地往南飞去,那正是它们家的方向。5 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它们的洞穴旁边,它们的窝是建造在一起的。我刚走到那儿,就看到两只腹部画着白点的节腹泥蜂正在窝里忙碌。不一会儿,第三只画着记号的节腹泥蜂从田野里飞来了,它腿上抱着一只象虫,随后,第四只也飞来了。我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里,就看到 12 只节腹泥蜂中的 4 只回到了自己的家,这足以说明问题了。我认为不必继续等下去了,因为已经返回的这 4 只会做的事,其他的也会做,况且,说不定它们已经这么做了呢。因此可以推测,另外 8 只正在路上捕猎,或者已经钻进洞里去了。实验的结果就是,我的节腹泥蜂在封闭的纸盒里被我带到了 2 公里之外的地方,方向和路途对它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可它们却能顺利返回,至少我亲眼看到它们的一部分平安到家了。
我不知道节腹泥蜂狩猎的范围有多大,也许方圆 2 公里以内都是它们熟悉的区域。或者,我带它们走的路还不够远,而它们恰好凭借以往的了解返回了。看来,我必须再做一次实验,这一次要让它们走得更远,而且带它们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点出发。
我从上一次做实验的那个蜂群中又取来了 9 只雌节腹泥蜂,其中有 3 只是参加了第一次实验的。我还是把每只泥蜂都关在一个纸袋里,然后把这些纸袋放到一个漆黑的盒子里。我的出发地是距离它们的洞穴大约 3 公里的邻城卡班特拉。我不像第一次那样去田野里,而是要到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的街道上放飞这些泥蜂。节腹泥蜂是生活在乡下的昆虫,从没来过城市。因为此时天色已晚,我把实验推迟到第二天,我的俘虏们也在牢室里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快 8 点的时候,为了与头一天画一个白色记号的昆虫区别开,我在这些节腹泥蜂的胸部各画上了两个白点,然后来到大街上,把它们一个一个放飞了。重获自由的节腹泥蜂,每一只都先从一排排门楼的间隙垂直往上飞,似乎要用最快的速度脱离这交错纵横的街道,飞到视野辽阔的高处,它们到达屋顶以后,立刻奋力一跃,疾速往南飞去。我是从南边把它们带到这里的,它们的家就在南边。我把 9 个俘虏,一个一个地释放了,可是我惊奇地发现,这些身处异地的昆虫每一只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飞行的方向。几小时后,我又来到了它们的洞穴口。我看到几只头一天做实验的节腹泥蜂,因为从它胸部的一个白点就能辨认出来,可我刚刚释放的那些昆虫却一个也没见到。它们找不到家了吗?是在捕猎,还是正躲在巷道里平复这场实验带给它的紧张情绪呢?我不得而知。第二天,我又去观察。这一次,我发现了 5 只胸部画有两个白点的节腹泥蜂,它们正积极地工作,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3 公里的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炊烟缭绕的烟囱,这一切对于这些地地道道的乡巴佬来说是如此新奇,却阻挡不了它们回家的步伐。
把鸽子从窝里取出来,送到很远的地方,它也能迅速返回窝里。
节腹泥蜂被运到了 3 公里之外的地方,也能顺利返回。如果将动物的体积与飞行路程的远近相比,它比鸽子要强多少倍啊!昆虫的体积只有1 立方厘米,而鸽子的体积完全有 10 立方厘米,甚至更大。鸽子的体积是膜翅目昆虫的 1000 倍,所以与昆虫相比,它应该从 3000 公里处,也就是法国三个从最北到最南的距离之外返回。我不知道哪只信鸽曾完成过这样的壮举。但是翅膀的力量并不是可以用距离的远近来衡量的,高超的本能更不是。这里不能用体积比来考虑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种昆虫与鸽子是名副其实的对手,而不能确定谁比谁更强。
如果鸽子和节腹泥蜂被人为原因弄得颠沛流离,来到了一个它们从未到过也分辨不出方向的地方时,它们能否凭借记性的指引分别返回鸽棚和地洞里呢?它们是以记性为指南,每当飞到一定的高度,就从那里以某种方式辨别出方向,然后往远在天边的家的方向展翅高飞吗?当它们第一次到达某个地方时,是不是这种记性给了它们高空中的指引呢?很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对于陌生的东西,头脑是不可能有记忆的。膜翅目昆虫和鸽子不知道它们身在何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引它们飞行,它们是被放在漆黑的密封的纸盒或箱子里运走的。它们完全不知道地点,也分辨不出方向,可是它们顺利返回了。由此可以断定,指引它们的是一种比单纯的记性还要高明的东西,那就是一种专项本领,一种对地形的直觉。这种对地形的直觉力,我们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因为我们身上没有与它相似的东西。
我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这种本领在它狭窄的职能范围内是多么的灵敏和准确,但是一旦超出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化,它又是那么的局促和愚钝。这也是本能所具有的亘古不变的双重性。
一只为给幼虫捕食而四处奔波的泥蜂离开了洞穴,不一会儿带着猎物返回了。泥蜂在出发前,倒退着把洞口的沙土扒过来堵住入口 ;在黄沙漫漫的沙地上,根本看不出这入口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异样 ;可这对于这种膜翅目昆虫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了,至于它找到洞门的办法,我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
让我们用恶作剧的手法改变一下现场,难为难为膜翅目昆虫吧。
我拿来一块平板石头把洞口盖住了。不一会儿,膜翅目昆虫来了。在它外出这段时间家门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似乎并没有使它产生任何怀疑,而是毫不犹豫地奔向了石板,想通过挖掘进入洞里去,但是它选择挖掘的地点不是在石块上面,而是在与洞口对应的那个部位。挖了一会儿以后,它意识到这个障碍物十分坚硬,便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它围着石头左看看右看看,索性钻到了石头底下,往一个准确的通往窝的方向挖了起来。
看来这块平板石头根本奈何不了这个足智多谋的膜翅目昆虫,我们还是另想一个办法吧 ! 见它很快就要挖到洞了,我便阻止了它,用手绢把它赶到了远处。膜翅目昆虫受到惊吓后,久久没有返回,我恰好有足够的时间设下埋伏。现在采用什么材料呢?在进行临时实验的时候,必须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东西。在不远处的路上有一些牲口的粪便,还十分新鲜。我用路边的一个木片作工具,把粪便挑了过来,一块块地摆放好、弄碎,然后撒在洞口周围,厚度至少有法寸,面积约0.25 平方米。膜翅目昆虫一定从没见过这样的门面。无论是材料的色泽、性质,还是臭臭的气味,都会让膜翅目昆虫上当的。它会接受自己门前的这些粪便层和这个味道吗?会的。它来了,在高空中对这番奇怪的场景进行了一番侦查后,它落下来,踩在粪便层的中央,在对着入口处一边挖一边扒起来。它钻进了充满粗纤维的粪团中,一直钻到了最底部的沙土层,在那儿它立刻找到了洞口。而我再次把它抓住并扔到了远处。
虽然膜翅目昆虫的窝已经被遮掩得面目全非了,可它还是能够准确地找到,这不正说明了它并不是单纯靠眼睛寻找和靠记性指引吗?那么还有什么呢?是嗅觉吗?这很值得怀疑,因为粪便的臭味丝毫也没有影响膜翅目昆虫敏锐的洞察力。不过我们还是改用别的气味来试试吧。
在我随身携带的昆虫学实验工具中,正好有一小瓶乙醚。我把之前铺下的粪便层扫掉,换上一层青苔,青苔铺得不厚但面积很大,我一看到膜翅目昆虫返回来就把抱乙醚洒在了青苔上。乙醚的气味太强烈了,以至于刚开始时昆虫不敢靠近。可过了不一会儿,膜翅目昆虫还是扑向了散发着强烈乙醚气味的青苔 ;它穿过了障碍物,钻进了窝里。乙醚的气味跟粪便的气味都没能阻止昆虫,这说明它一定有某种比嗅觉更灵敏的东西指引着它。
人们通常认为,指引昆虫的某种感官一定位于它的触角中。我已经描述了膜翅目昆虫寻找洞穴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它似乎并没因为把触角这些器官取消掉而受到妨碍。我们再做一个可靠的实验充分地确认一下。
我抓来了一只泥蜂,把它的触角连根剪断后立刻放走了它。泥蜂可能被我捏得像被针刺一样疼,所以惊恐万状,迅速逃亡了。这一次我等了很久,以为它不会回来了。但它还是出现了,还是准确无误地直扑向那个被我第四次改头换面的洞口,它的窝已经被我用一颗核桃大的卵石像马赛克那样盖住了。对泥蜂来说,我的工程虽然远远超过了布列塔尼①的拱形建筑物,超过了卡纳克的史前期遗留下来的巨石林②,却无法让这个身体有了残缺的昆虫上当。在被马赛克掩盖的洞口旁,这只被剪断触角的膜翅目昆虫跟正常昆虫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一样,很容易就找到了入口。这一次,我让这位执著的母亲安安稳稳地回到它的窝里。
洞口连续四次被改得面目全非,颜色、气味、材料的改变以及身体的疼痛,这一切都难不倒膜翅目昆虫,它甚至都不曾对洞口的位置产生过任何怀疑。我束手无策了,我想,如果昆虫不是具有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特殊功能的指引,在我用恶作剧混淆它的视觉、味觉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一次次回到家里呢?
几天后,一次成功的实验,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我把一个泥蜂的窝完全打开,但并没有完全捣毁它的原样。这窝埋得不深,几乎是水平放置的,而且挖在一个不太硬的沙土中,这使得我操作起来比较容易。我用刀刃把沙一点儿一点儿地刮掉,直到把它的屋顶彻底刮平,于是这个地下住所俨然成了一条或直或弯的渠道样的小沟,大约有 20 厘米长,洞口的一端可自由进出,另一端则是闭合的凹陷,幼虫就藏在那儿,躺在它的食物中。
现在它的遮蔽所完全暴露在苍穹之下,沐浴在阳光之中了。当幼虫母亲返回时,它会怎么做呢?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把问题一个个分解开吧。要进行观察可能相当麻烦,我见到的情况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母亲返回就是为了给幼虫送食物,可要想找到幼虫,首先要找到洞门。
在我看来,幼虫和洞门这两个问题值得单独观察。于是我把幼虫和它的食物拿走了,渠道的尽头空空如也了。做完这些准备以后,只需要耐心等待了。
膜翅目昆虫终于回来了,它径直奔向那个已经被我摧毁得只剩巷道的家。我看到它努力地在地上挖掘着、打扫着,弄得沙土飞扬。它如此百折不挠,并不是要挖一条新的巷道,而是在寻找一扇活动的围墙,然后用头一拱,把围墙拱倒,它就可以进去了。可是它遇到的不是活动的东西,而是未经翻动过的土地,十分坚硬。土地的坚硬度终于使它警觉起来,于是它开始在地面上巡查起来,不过它并没有走远,而是一直在洞口原来的位置附近寻找,最远也就走出几法寸而已。然后它又返回那个已经探测、打扫了 20 多次的地点,继续进行探测、打扫,可就是不肯离开那条狭窄的半径,因为它固执地认为洞门就在那儿。我用草根轻轻地把它拨弄走了好几次,可它并不上当,每次都立刻返回原来的地点。过了很久,它看到了那条渠道,这似乎稍微引起它的注意,但它没有放在心上。泥蜂往那儿走了几步,不断地扒着,随后又返回了入口处。我见它有两三次走到渠道的尽头处,在幼虫藏身的凹陷处漫不经心地扒几下,可是紧接着又迅速返回到入口处继续寻找。面对它的执著,我都有些不耐烦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百折不挠的膜翅目昆虫还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洞口所在地寻找着。
如果它见到幼虫时会怎么样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继续用同一只泥蜂做实验也许得不到想象中的最好的效果 :一再的徒劳无功的努力更加坚定了昆虫继续寻找的决心,我觉得它已经陷入一种固定思维中,而正是这种思维使得它对某些事实百思不解,而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我需要一只新的没受过刺激的实验对象,这样它才能完全被最初的某种冲动所指引。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把它的窝完全打开了,但我没有破坏它原来的样子,幼虫仍然待在原来的地方,食物也还在原处,除了没有了房顶以外,房间里的一切都完好如初。好了,面对这露天的小屋,放眼望去,一切细节都尽收眼底 :前庭、巷道、位于尽头处的卧室,以及幼虫和它那成堆的双翅目昆虫 ;房屋成了一道小沟,在小沟的尽头处,幼虫在炽热的阳光照耀下烦躁地扭动着。可是幼虫母亲的行为表现跟前面的那只一模一样。它停在原来的洞口所在地,在那儿不停地挖掘,清扫沙土 ;它在几法寸长的半径范围内尝试了几下后,总是会回到原地。它根本不到巷道里搜索,也不担心正饱受煎熬的幼虫。幼虫的表皮十分娇嫩,从温暖潮湿的地下突然暴露在了烈日之下,此时它正在已经咀嚼过的双翅目昆虫堆上扭动着身子,可它的母亲却对它置之不理。对于幼虫母亲来说,这跟随处可见的沙粒、土块、干泥巴等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位费尽千辛万苦要找到婴儿摇篮的母亲,这位温柔而执著的母亲,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它已经习以为常的洞门,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它所关心的。这母亲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寻找熟悉的通道上了。可是这条路已经畅通无阻了,没什么可以阻挡它 ;幼虫正在它的前方不远处苦苦挣扎着,那正是它竭力寻找的对象啊。它只要轻轻一跃就能来到这不幸者的跟前,那不幸者正在等待它的救援呢。它为什么不径直跑到它疼爱的婴儿身旁呢?它只需要给它挖一个新窝,就可以立即把婴儿藏到地下。可是它没有这么做,孩子就在它的眼前忍受着太阳的炙烤,而母亲却固执地寻找一条已经消失了的通道。
在动物的情感中,母爱是最强烈、最能激发才智的,可是看到这位母亲如此顽固不化,我的吃惊程度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如果不是对节腹泥蜂、大头泥蜂以及各个种类的泥蜂反复做过这样的实验,我肯定不会相信眼前看到的事。
欣慰的是,这位母亲犹豫了这么久以后,终于走进了那条已经沦为小沟的过道里。它往前走几步,又往后退几步,然后再往前走,十分漫不经心,并且不停地东扫一下,西扫一下。也许是它那模糊的记忆和双翅目昆虫堆散发出的香气,把它引到了躺在巷道尽头处的幼虫身边。现在,母子终于团聚了。在经过长时间焦灼不安的分别后,在这特殊的相聚时刻,它们之间有没有更深切的关怀或情感的抒发呢?母子之间会如何表达感情呢?如果有人认为理所当然会发生这一切,那么,我下面的实验会令您彻底打消这个想法的。泥蜂根本没认出那是它的幼虫,而是把它当做了一种纯粹的障碍物,认为它毫无价值,甚至有些碍手碍脚。它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了,可是它从幼虫身上踩过了,竟然心狠手辣地践踏它。当它想在房间的尽头处进行一番搜索时,就会粗鲁地蹬一脚,把幼虫踢到后面去 ;它推搡着幼虫,想把幼虫踢翻,赶走。当一块大卵石阻碍它工作时,它就是这么做的。当幼虫遭受如此粗暴的对待时,它想自卫。我曾看到它抓住母亲的一只腿用大颚咬起来,就像咬它的双翅目昆虫的腿一样。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幼虫最终张开了凶狠的大颚,母亲惊恐万状,扑打着翅膀,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逃走了。这种儿子咬母亲,甚至想吃掉母亲的违背伦理的情景是很少见的,这是由某种特殊原因引起的,观察者不应该制造这种事端。
观察者经常看到的,是膜翅目昆虫对子女极度的冷漠,以及对待幼虫这个障碍物的粗暴和蔑视。当它用耙在过道尽头进行了一番探索后(这只不过是一会儿的事),泥蜂就又回到心爱的洞口所在地去了,继续那徒劳无功的寻找。至于幼虫,它在被母亲一脚踢倒的地方挣扎着、扭动着。它最终会这样死去,而不会得到母亲的任何救助。母亲找不到它印象中那条熟悉的通道,竟连自己的婴儿也不认识了。如果我们第二天再到那儿就会发现,在沟的尽头处,幼虫被太阳烤干了,已经成了小蝇的美味,而它原本是把蝇当食物的。
这就是受本能支配的各种行为之间的联系,这些行为按照固定的顺序前后呼应着,即使是发生最严重的意外也更改不了。泥蜂到底要找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幼虫。但是它要走到幼虫面前,就要先进窝,而要进窝,就必须找到门。虽然在幼虫母亲面前,巷道已经敞开了,并且畅通无阻,它储备的食物、它的幼虫安然无恙地待在那儿,可它仍然固执寻找的就是这扇门。在此时此刻,沦为废墟的房屋、身处险境的幼虫,它都视而不见;对它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印象中的那条穿过流沙的通道;如果找不到这条通道,房屋和幼儿再怎么危险它也毫不在意!它的行为就像一系列按固定顺序连续响起的回声,只有前一个回声响起了,后一个回声才会响起。这并不是因为有障碍物阻挡了它,而是因为房间一直是大开着的;是因为它没有完成习惯性行为的第一步,所以下面的行为也就无法继续;第一个回声不响起,所有的回声都不会响起。智慧与本能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啊!看到房间的残墙断瓦,这位母亲如果受到智慧的指引,就会直接扑向它的孩子;可是因为它受到本能的支配,所以一直执拗地停在洞口最初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