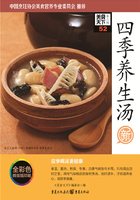现在的中国人,有着充裕的物质生活,然而,精神世界的贫瘠与荒凉,教育文化的粗放与快餐化,娱乐走向低俗与审丑,使有着优良传统和丰厚积淀的民族精神日益贫瘠,日渐委靡,精神文化生态严重失衡。
我们缺少的是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一种虔诚的宗教情感。
问题并不在于信仰基督还是真主,是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或者是马列主义,总之,人是要有追求、有精神寄托的,否则,锦衣玉食,也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
为此,我要向甘地——裸露上身的游僧,致敬!
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精神的崇高与不朽。
有人说,这个时代,不去疯狂解构,就会被解构疯狂。可见解构主义的时髦与盛行。
起源于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上世纪后期进入国门后,很快分流,而且泾渭分明:一边,是精神清流,即学者们的认真研究与思考;另一边,为世俗浊浪,是文化玩主进行的实用主义重组。后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解构主义“解构”为百变魔棒,并以此对其他事物随意解构。最初,这种玩法还比较克制,即便恶搞,也还懂得有所选择。而近年来,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成分复杂,质量走低,逐渐有些“疯狂老鼠”进入状态的味道,把媚俗娱乐当做解构的最高境界而将其推向极端,对文化范畴的大事小情开始了全面围剿扫荡,冷拼热炒,花样迭出,直搞得思想文化舞台充斥着新、奇、特、怪、赖,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跨入全民“玩”文化的世界前沿,热闹非凡。
解构主义在中国竟有如此奇特的演绎发展与创新,估计德里达本人都会对之大跌眼镜,自愧弗如。
与此同时,伴随上世纪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狂热革命的曲终落幕,人们出于各自的不同理解,共同把西方的启蒙运动旧话重提,期望能从中理出一条通向“罗马”的康庄大道。于是,人们或严肃或调侃,或正道或旁门的为卢梭、孟德斯鸠,为伏尔泰、狄德罗,为洛克、边沁等等,口诛笔伐,争执不休,打破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泾渭格局,学术探讨与解构恶搞混在一起,直搅得天地昏黄。
本来,学术之争自有其积极意义,不必非要压倒谁、战胜谁。古今中外形而上的争论,很难真正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胜出者挂头牌,也不过是“各领风骚数百年”,其余或作陪衬,辅助补充;或被挂置暂存,此后如有需要,检索出来应时应季地加以改造包装,仍能派上用场。
我一直相信,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不欣赏对各色思想学说“满门抄斩”的过激做法,所以,不具备当战斗员的资格,只能远远观战,顺便说些不痛不痒的外行话,卡拉OK一把。
以前读卢梭,一种很触动很复杂的感觉。后来,对他的抽象人性论,以及孔孟的唯心性善论、荀子的唯物性恶论,都各有取舍。再后来,对法国以及欧洲文化感兴趣,看到拿破仑的“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权威性结论,深以为然。我想,这不仅是由于说话的“人”,占据了权力的制高点,更因为所说的“话”,占据了历史发展的思想制高点。卢梭带给当世与后世巨大深远的影响,岂止于法国?岂止于欧洲?而是全世界。他是思想史上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我不想把卢梭的诸多“业绩”从别处粘贴复制到这里,哪儿都可以找到,也不认为卢梭的理论无懈可击。恰恰相反,我对他的一些思想学说存有异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只想说,研究分析人和事物,既不能脱离基础地去“高空作业”,也不能背离现实地去“真空作业”,更不能任性偏激地胡乱指责。
例如,有一篇文章,标题:《揭开卢梭的伪善面目》。
仅这样感性化的题目,如此的吸引眼球,如此的具有冲击力,就让我有理由把它当做恶搞名人的戏作。读过之后,觉得假如是简单的恶搞,倒不必较真,完全可以一笑作罢,麻烦的是它的夹生制作,貌似学术,又很随意而不负责,从人性角度,不够宽容厚道;从学术角度,不够客观冷静。
卢梭留给人类的,是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代表、作为“自由奠基人”那些震撼心灵与历史的思想成果,是在旧王朝行将灭亡人们陷入思想混乱时,他带给人们的精神向往和力量,他是“支撑法兰西智慧宫殿的栋梁”,他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然人本的天性哲学,不仅颠覆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也冲击扫荡了现实的弊端与黑暗,他的民主主义为近代的民主运动,实在称得上是导扶先路,以启山林,开创先河,他的教育思想,对其后的康德、杜威、巴泽多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卢梭们的价值意义在于他们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并通过这些具有先进性的思想,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让接力到我们手中的人类社会是“这个样子”——既不是完美无瑕也不是彻底糟糕,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
作者使用的材料,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许多来源于卢梭自己的《忏悔录》。问题是分析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究竟是什么?首先需要明确,有关卢梭的生活隐私、感情纠葛,那是作为“人”的错误。何况,卢梭的“恶”似乎不存在着揭露不揭露的问题,它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已经几百年。更何况,我们不能用完美的神的标准去要求人,不能因为卢梭的道德哲学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理性哲学更具有“道德魅力”,就去要求他本人必须成为道德完人。最为主要的是,卢梭对于我们,更多的是哲学意义,是思想意义,而从来就不是道德楷模,也从来没有谁会认为他的生活行为具有示范意义和价值。这就如同我们对黄健翔,不能因为他把足球解说得好就指责他为什么不能把球踢好一样。
分析研究卢梭的知与行的矛盾、他的精神冲突与人格分裂、他的思想行为表象与深层本质之间的关系,对深入探讨人——这种行为思想的聚合物的复杂多面性,具有很大的人类学价值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卢梭的罪恶,具有标本功能。但是,对卢梭等人的批判,应该剔除对他个人的感性指责;评论者本身,应该避免一种带有个人化色彩的情绪宣泄。我相信,作者不会把“搞臭卢梭”作为唯一目的,因为,即使提供警世作用,卢梭也并不那么典型。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研究分析,应该立足于心理诊断的病理意义,立足于建构健康人格的社会意义,它应该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黑色幽默:把美好的事物践踏毁灭给人看,再重复一次“焚琴煮鹤”。
不管卢梭做过什么丑陋的事情,有过怎样的阴暗心理,他的《忏悔录》,都表现了作为真实复杂的人的勇气与磊落。谁敢说自己的一生,灵魂深处从来没有丝毫阴暗的存在和罪恶的涌动?没有说出来,并不等于不存在。任何人,都有若干甚至更多“不可为外人道也”的暧昧和隐私。假如,我说,那些整天惦记着揭开别人面目的人,自己的面目是否愿意先被揭开?显然,这与上述对黄健翔的指责,同样匪夷所思,同样肤浅偏颇。
应当承认,卢梭这一类属于社会的公众人物,在公众的关注评判下,不具备常人应有的私有性、个人化,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们只是概念人,被彻底“符号”化了。因此,对他们的批评底线和尺度与普通人有很大不同。
即便如此,我们有些学术批评,也还是缺少了一些客观从容和优雅,缺少应有的智慧和宽容,缺少对他人的基本尊重,而是多了些痞气、江湖气、浮躁气,多了一些非此即彼的极端性,也多了一些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怨气、怒气。进一步说,就算是嫉恶如仇,那也要想想,是气血之怒,还是理义之怒。前者不可多有,后者不可略无。
罪眼看世界,必定满眼罪恶;极端思维视野下,没有正常。
做学术研究,或是玩文化,都需要深厚文化的强大支撑,否则,就难免捉襟见肘,露出几分底蕴不足的丐帮味道,气盛而格调卑微。
再者说,研究,就是研究,不是打架,是不是先把态度放平?
巴赫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从伦理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的社会存在,把对美学、文艺学的探讨而形成的“对话主义理论”,推广辐射到广大的社会学领域,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万物)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这是我一直信奉的经典。
语言是什么?教科书上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哲学家说,语言是思想的媒介和表达;神学家认为,语言是灵魂的载体;诗人则说,语言是感情的音符;艺术家以为,语言是美的衣裳。
《圣经·旧约·创世纪》开篇写道:神创造了天与地。大地一片混沌,神曰“光”,于是有了光;再于是有了连续七天的开创万物。这是说,先有了神的语言,而后才有了生成的万物。
《约恩传》以及《来自约恩的福音书》则用“万物由语言生成”对语言进行了超文本的概括描述。
于是,下列公式成为相当权威的理论:
语言=神。语言,生成万物。
当然,作为无神论的人们,可以模糊神与人的界限。马克思他老人家就明确指出:神,即人,而且,是劳动的人。
由此逻辑演绎出:语言即人。
换句话说,语言,就是人自己。这相当于文学即人学,风格即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当然,人有个性;人世间有百态。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中,有神性,也有邪恶。况且,天使与魔鬼的语言是相伴而生的,是通行互换的。那么,语言自然随同人一起而变得破碎、诡异、混乱复杂而充满矛盾。
巴赫金就是据此扩展延伸他的研究,把关于语言、作家、作品,人与自己、人与他人的“对话”关系,置放于更加广大的时空领域,创立并丰富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得出世界万物是“对话关系”的宏大理论,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而我只是关心语言表情达意的直接作用。我坚持认为:语言,是内心完整而完美的系统表达,是抽象思维情感的具象。一句话,“言为心声”,语言就是心灵的外表。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位大师的主张,要以“沉默”对抗语言。说很多情况下,由于“引进了情境变量”,语言既是滞后的,又是虚假与反向的,还是苍白无力的;认为“人,只有在沉默的状态下,才是最真实的、最自由的;只有行为中的表达,才是本质的、无限的”。
我陷入深度迷惑,认为这虽不无道理,却是一种片面性的、带有夸张性的真实。
然而,今天早晨,在央视3套的节目里,看到一场“全国舞蹈大赛”的精选实况转播。我突然感到,语言,其功能作用确实有限;非语言的魅力确实强大,简直神奇美妙到超语言,甚至超感应。它是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世间万物的另一种非语言的绝妙“对话”。
华尔兹的妙曼舒缓、矜持高贵,这是尽人皆知的。那种优雅尊贵,让人体会到生命的神圣与尊严,典妙非常。我,不知用什么词语去描述台上的舞姿,也不知怎样形容内心的感受。我的眼前,是一只只美丽的白天鹅,悠然而舒展;是一匹匹健美的红鬃马,奔腾而飘逸。他们像风吹仙袂飘飘举的飞天嫦娥,像临波照影的惊鸿一瞥,转身时妩媚妖娆,回眸间摄人魂魄。静若处子,闲庭信步而潇洒从容;动似蛟龙,上下翻飞而舞动生风。高扬的头,颀长的颈,柔韧的腰,用肢体结构出一幅幅情韵兼容、神形并妙的炫彩图景,经典唯美。
桑巴舞热辣的南美风情,是年轻人的时尚新宠,却也可以使任何年龄段的男男女女激动痴狂。橄榄色的背景与蜜色皮肤交相辉映,组合成沙滩的主调。舞蹈者健美强壮的身姿,带有印第安人的狂野和丛林精灵化合后的怪异与神秘;转腰抬腿,提臀扭胯,极具张力,动感十足而又风情万种。桑巴舞有浓烈的烟草烈酒的强刺激,释放着原始的激情:自由、热烈、奔放,夸张出摧枯拉朽般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探戈,是一种节律感十足的舞蹈。舞蹈者像是在欧洲城堡的广场上接受检阅的皇家卫队的士兵,凛然不可冒犯;又像一个个剑拔弩张的决战武士,相搏于生死存亡的角斗场;更像一对对相斥相吸的性情男女,挣扎在爱恨情仇的伊甸园。舞台上流动着的,是刀光血影,电闪雷鸣;是绵绵情话,呐喊狂呼。刚劲柔美,激荡起伏,在推拉转送间,在悲喜嗔怨中,尽情张扬,任意驰骋,使生命之花、灵魂之光,一度度华彩绽放。
舞蹈,这种非语言的艺术,表达的是恒久不灭的人文主题。它像一袭心灵的狂飙,一泓感情的清泉,一扫现实的乏味、平庸和阴郁,于冷漠的无常中,带给人们一束来自于天堂的明媚佛光。
在整个观看的过程里,我彻底地失语!对语言彻底地绝望!也彻底地陷入惶惑!由此,我相信,语言的有声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强大、更无限的精神情感的神秘存在。
美国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说“其实,我并不想写(说)什么,我想握着别人的手,直接沟通”。
莎士比亚这样的语言大师也曾说“不说,才是最高境界”。
人与人之间,既有语言的对话和交流,也有无言的表达与解读。
只是,语言的欺骗与歧义,同语言的作用同样有限;而无言的费解与误读,也同无言的多向性一样——无极。
问题的关键是:读懂!
更为关键的是:相信!
出色的领导,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和比较全面的个人素质、一定的工作能力之外,还应有较高的领导艺术。领导艺术方面的专著积案盈箧、洋洋浩繁,但是,我以为领导艺术之要还是“知人善任”和“平衡有术”。
事必躬亲的领导,未必是好领导。最高的领导艺术,与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同理,即“无为而治”。宰相之责,“非以一人之才为天下用,而是以天下之才为天下用”(宋·曾巩)。善于用人,必先识人、知人。识人知人要有慧眼。至于用人,那还要有气度和胸怀。知人善任,才能聚集人才,才有可能“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唐·魏征《谏太宗广思疏》)。
至于平衡有术,就比较复杂了。所谓平衡,就是掌握分寸,把握好尺度。领导最常遇到、最难掌握、最能衡量出水平高低的,不外乎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只讲原则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但是,不讲原则的领导,也肯定不是好领导。严格地说,只讲原则,凡事都按规定,查条文,遵先例,照章办事,那还要领导做什么?机器操作岂不更准确方便?然而,如果完全不讲原则,处处灵活,那恐怕就天下大乱了。所以,其难点,不在于原则,也不在于灵活,而在于高度的原则与最大限度的灵活的完美结合与统一。正如真理与谬误有时仅仅一步之遥一样,原则与灵活之间也并不是关山迢迢。它们相依相生,互为补充,互为因果,有时,泾渭分明,有时难分你我。过于原则,流于生硬、教条,容易激化矛盾,走向极端;过于灵活,又会丧失原则,造成损失、带来被动或引起混乱与麻烦,还难免滑头之嫌。上乘之境是把握二者最佳临界点,所谓差一分则不足、多一分则过矣,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这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功夫。它集人格、胸襟、学识、修养、能力、经验之大成,是对事物有深刻了解认识领悟之后的一种自然把握,只可意会,难以力及。
汉代东方朔曾经这样描述处世胜境: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道,即客观规律;游,自由灵活;优,佳境也。不拘泥,不逾越,把握有度,收放自如,以期臻于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