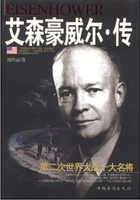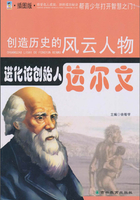战乱期间学术机关的迁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迁徙地址的选择固然不容易——因为既要考虑到新址是否安全,又要考虑到是否有足够的房屋放置图书资料和安排工作人员的办公生活场所。图书资料的运输、工作人员的运送亦非易事。当时搬运的图书资料等有上千箱,仅文物一项就有150吨重。加上大西南交通很不便利,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史语所的图书、文物、资料都是无价之宝,如何妥善保管,避免损失,也是一件重要而又难办的事情。据当事者回忆说,史语所刚迁到南溪李庄时,当地群众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机构,他们见到人类学组的人头骨及其他骨骼化石,惊异万端,到了晚上,经常有人站在附近的山头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当时兵荒马乱,时有土匪出没,故研究所的安全乃是一大问题。为了避实就虚,掩人耳目,傅斯年让人把“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另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他亲自召开会议讨论治安保卫问题,提议每个人床头上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马上鸣锣报警,虽然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阵,但也引起了对安全问题的警觉。
史语所迁李庄后的6年中,最令傅斯年感到头痛的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均迁至重庆,前往四川避难的人极多,所以当地生活物质严重短缺。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他经常要和地方政府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求告他人。他曾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不少求助的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说: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凤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
据傅乐成、屈万里等人回忆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便靠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他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在那战乱的年代里,史语所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关键还在于傅斯年注重选拔、培养学术人才。傅斯年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胆识和魄力,不管生活多么困难,环境如何动荡,他仍一如既往,把人才选拔培养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选拔人才务求德才兼备,所谓“德”是指学术品德,即不慕权势、不求富贵,热爱历史学、语言学,具有为学术而奋斗终生的精神。所谓“才”,是指具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和敏锐的分析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潜力、有培养前途。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他千方百计地网致,不符合这两个条件,无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和靠山,抑或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也拒之门外。
而今驰名海内外的学者中,不少是他于战乱期间选拔培养成才的。如严耕望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曾跟随钱穆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后受安徽学院之聘前往任教,旋因战乱滞留重庆。素闻史语所具有全国一流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条件,他便萌生了入史语所继续读书的念头,但苦于无人推荐。后来有人告诉他:“傅孟真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若果欣赏,就可能成功。”严耕望抱着无可奈何、姑且一试的心境,于7月中旬写了一个申请书,连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给了傅斯年。想不到时过不久就收到傅斯年寄来的快信,信中说:照论文的程度可作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作助理员。这着实使严耕望喜出望外。此后,严耕望学习更加刻苦认真,加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有名师指导,不久他就写出了许多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论著,终于成为颇有成就的知名学者。
傅斯年在声声警报中主持王利器的入学考试,更堪称学林佳话。王利器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在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中,该论文得了满分。听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他急忙前去应考。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本科合办,研究所则仍由各校自行办理。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由于王利器住在僻远的山区,等赶到重庆时已误了考期。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傅斯年。傅斯年看了他的《风俗通义校注》后,决定对他单独进行考试,首场考试科目是英语。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敌机时常轰炸重庆。一场英语没考完,警报就响了7次,他们也往防空洞中跑了7次。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傅斯年告诉王利器,“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读。”王利器选择了李庄,直接跟随傅斯年作研究生。后来王利器也成为知名的文史专家。
傅斯年提出历史学、语言学“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主张“建立科学的东方学”,同时他强调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他在选拔人才、录取研究生的时候十分注重考察他们的外语水平。前面提到王利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场便是英语。另据杨志玖先生回忆说,他在1939年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时候,傅斯年“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事后还特别对杨说“你的英文还可以。”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定出一个总体的研究方向,但对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说,则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学术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对此傅斯年从不强行干涉。李方桂留学回国后进入了史语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崭新的留学生”。对于这样一个青年学者,傅斯年也是放开手脚,让他自由发展。李方桂后来回忆说:
我想做什么事情,傅先生从来不曾回拒过,只要我想做些什么研究,他无不赞成,这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往往办事的人总是要你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你所要做的事情。从这两件事看,一是他能认识人,二是他能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这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
对于在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采取了“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的培养模式,即要求学生学业基础扎实,学术研究能力强,但具体的研究方向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自由选取。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到李庄之前,所址设在昆明的青云街靛花巷,当时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住在乡下,他经常到靛花巷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有时也到研究室询问同学们的学习进度。他规定史语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大家轮流担任报告人,读研究生的学生也不例外。王利器就曾做过一个题为《“家”、“人”对文》的报告,颇得傅斯年的赞赏和大家的好评。王利器是傅斯年直接带的研究生,当时傅斯年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先秦民族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明史,但王利器读本科的时候作的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偏重于古籍的校勘注解,在史语所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又对《吕氏春秋》产生了兴趣,傅斯年尊重他的学术兴趣,指导他以《吕氏春秋》为题目,采用注疏体写论文,最终完成《吕氏春秋比义》的长篇论文。
劳干先生说,傅斯年对史语所历史组的学者们的学习和研究都进行过帮助和指导。他说: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全体同人的工作中,差不多都得到(他)很好的启示。尤其新进的同人作好的论文,几乎每一个字他都加以指示,使他再向谨严去做。
傅斯年身高体胖,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不过他的体质却不怎么强壮,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他便常常患病。胡适1937年写信给他,说:“一个山东大汉,遍身是小病,娇弱的禁不起风,如何是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工作压力比从前更大。他部署史语所的迁徙:选择迁徙地址、安排运输、解决工作人员的给养,组织学术研究,处理日常事务,辗转奔波,终日忙碌。后来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内各机关的迁徙及日常事务,均须考虑安排,更使他忙中加忙。此期间,他开始参与政治,先是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参议会”,后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常出席国民参政会。1941年的二三月间,50天内竟开了5个会,会期最长的达10天。这年的年初,他就觉得两眼不舒服,但仍可上山走路。2月18日,请眼科大夫检查,未发现异常,大夫建议他到内科复查。但由于会议太多,所以一直拖延,以后觉得眼睛更不舒服,至3月下旬,身体亦觉不适。入医院检查,不禁大吃一惊,血压高至194—140水银柱,左眼有一毛细血管破裂。医生皆认为情况危急,朋友也为他担心。没有办法,只好住院治疗。3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而后又在家静养了两个月,至9月份,便可外出小走。到了l0月,其母突然病逝。傅斯年以自己久卧病榻、未能尽心看视母亲,负疚痛心。丧葬等事,劳顿异常,其间又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且为中研院及史语所事务操心忙碌,年底自重庆赴李庄,冬天逆水行船困难,过了5天方才到达。后来一量血压,比前更高。医生劝其休养2年,但他只休息了2周,使又出面主持研究所工作,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种穷、愁、忙的环境,使他的病情一直不能彻底好转。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与贡献
根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宗旨,傅斯年很快为各组选定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他担任所长的20年里,各组在这些课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历史组把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校勘《明实录》作为工作的重点。清内阁大库档案是指清朝政府存放在内阁大库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册簿等。内阁大库原编为6号,礼、乐、射、御4号所藏全是明末至清代的档案,书、数2号除收藏赋役书、命书、朱批谕旨、乡试录、殿试卷外,还藏有明朝文渊阁旧籍及各省府县志。宣统元年(1909年),库房损坏,这些档案书籍被临时搬放于文华阁两庑和大库外边的庭院里。露天堆放非长久之计,于是主管学部事务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将其中书籍捡出,成立“学部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档案部分被视为无用之物,经内阁会议讨论后,拟予以焚毁。学部参事罗振玉奉命接受书籍,发现批准焚毁的档案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是建议学部设法予以保存。获准后分别存放于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后楼里。辛亥革命后将这批档案材料划归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于1917年全部移放于午门端门洞中,当事者时或盗窃之。后来教育部曾两次派人进行“整理”,将一些比较整齐的材料翻捡出来,其余的则胡乱堆放,使之更加残破散乱,被盗窃之现象亦更为严重。
1922年,历史博物馆方面经费短缺,于是在这批档案上打起了主意。把它们装进了8千个麻袋里,总计重量15万斤,以“烂字纸”之价格,计4千大洋,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该纸店又改用芦席捆扎成包,准备运至定兴、唐山两地重新造纸,同时从中挑出一些较为整齐的案卷,拿到市场上出售。罗振玉闻讯后,急以三倍之价赎回。将已运往定兴的部分重新运回北京,运至唐山的部分改运到天津存放。他曾雇人对某些案卷进行了整理,编印成《史料丛刊初编》10册。以私人之力,全面进行整理绝无可能,长期存放,其财力实亦难及。罗氏计无所出,只好转售他人。据传外国人有欲出重金购买者。1924年,李盛铎以1.6万元价格购得,乃于北平、天津分别赁屋存放。1927年,李氏因房租价高难以支付,且所租房屋漏雨,损及书册,乃急欲转卖。当时平津学人虽知这批材料价值甚大,但均以价格太高且难以保存整理而未敢购买,时日本人又生觊觎之心,且已染指于兹。
1928年春,著名考古学家马衡致函傅斯年,建议其购买这批档案。当时傅斯年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时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专门讲了有关史料搜集整理的问题。他将史料分作“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两大类,指出在史学方面后人要想超过前人,首先“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他也提到历史档案问题,说《明史》是间接史料,而明档案则是直接史料。如今大批的历史档案摆在面前,这对于以搜集新史料为己任的傅斯年来说,自然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接到马衡的信后,马上找中山大学校务委员长(校长)戴季陶、校务委员朱家骅商议,二人都说应该买下,但数万大洋的款项难于筹措。迁延至9月,一次,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三人聚餐,又谈及此事。胡、陈均嘱傅斯年,务必设法买下。当时中央研究院已经独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秘书长(是年11月以后改称总干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工作就绪,正待宣告成立,傅斯年以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已成定议。于是傅斯年决定求助于中央研究院。9月11日,他写信给院长蔡元培,该信全文如下: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八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麻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按:实为一万六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按:马衡字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今春叔平先生致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按:指戴季陶)、骝(按:指朱骝先,即朱家骅)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买去之议。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