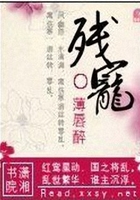事实全都摆在眼前,接下来进行归类就可以了。我们已经知道,像土蜂那样的猎手会专门捕食那些神经器官高度集中的昆虫。例如节腹泥蜂,是专门捕食象虫和吉丁的。这些猎杀者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捕食活动的,因此没有遇到土蜂在地下捕食时所遇到的困难。它们可以自由施展捕食技艺,并用眼睛指挥操作;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困难也会有,它们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就会遇到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
鞘翅目昆虫浑身披着一层刀枪不入的铠甲,只有暴露的关节才有可能被螫针蜇到。虽然可以刺到它们脚上的关节,但无济于事,针戳上去只会让局部有些发痒,根本不可能驯服猎物,而且这种类似挑衅的举动反而会使猎物勃然大怒。在它的颈部关节戳针也是不可取的,那样会损伤它的脑部神经,加速猎物的死亡和腐烂。因此,最佳而且唯一能攻击的位置只剩下胸腹之间的关节了。
必须从胸腹之间的关节出击,一招制敌,将金龟对未来的饲育造成的危险的挣扎彻底排除。一个非常满意的麻醉效果,必须选中一个主要的神经节,至少那三个胸腔的神经节集中地连在一起。于是,象虫和吉丁虽然全身武装,却因为它们的身体结构便成了土蜂的首选。
但是,如果猎物的皮肤没有良好的防护措施,阻挡不了螫针,那么就不一定要有一个集中的神经系统了,因为土蜂熟悉猎物的解剖构造,它清楚地知道神经中枢位于什么地方,它便可以挨个地蜇刺这些地方,把所有必要的关节全都蜇刺。砂泥蜂猎杀毛虫以及飞蝗泥蜂对待蝗虫、距螽和蟋蟀,所用的手段都是这样。
土蜂猎物的皮肤是柔软的,螫针可以穿透它们身体的任何部位。
砂泥蜂猎杀毛虫的那种战术会在这里重演吗?不会的,因为受地下环境的约束,它们无法施行这样复杂的手术。现在,唯一可行的是运用麻醉戴有铠甲的昆虫的战术,螫针只能一招制敌,将外科手术的规模缩减到最小程度,这是地下手术所迫使的。因此,土蜂在地下寻找并麻醉食物,猎物必须是神经集中的那种,就像节腹泥蜂的象虫和吉丁那样,这也是金龟子的幼虫为什么能成为它们的食物的理由。
在找到满意的食物之前;在找到几乎就是通过数学计算出的那一个精确的点,螫针可以在插入就能瞬间造成持久麻木的那一点之前;在掌握能长久食用新鲜猎物的技艺之前,总而言之,在具备这三种成功要素之前,土蜂又在做些什么呢?
进化论者达尔文会这样告诉你:它们在犹豫着,搜寻着,尝试着。
在漫长的盲目探索之后,最终会找到最好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将让它们的后代繁衍下去。目的和手段的绝妙配合,是从一个偶然的结果中得来的。
偶然!当我听到有人引用它来解释像土蜂的本能这样复杂事物的起源时,我只好耸耸肩—这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辞。他们有时还解释说,一开始,昆虫在漫无目的地摸索。为了养育好后代,根据幼虫的胃口,它普遍撒网,力所能及地捕捉所有可以食用的猎物;它试试这个,尝尝那个,这样碰运气式地试了无数个世纪,最终才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食物。于是渐渐形成了习惯,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本能。
算了吧,古代土蜂的猎物与现代的不同就把它看做是一个真理,如果土蜂家族曾经以另一种猎物为食并繁荣不止,后代应当没有理由更改食谱。况且,昆虫不会因为吃厌了某种食物而随意给自己换换口味的。既然已经能让自己很好地活下来并繁衍下去,吃这种猎物就会成为习惯,而今天显现的本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起初的食物不适应它,家族就会陷入饥荒之中,根本来不及尝试就会遭受灭门之灾,没有正确的猎食方式,它们是不会留下子孙后代的。
为了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物种的初始—土蜂的祖先是一种没定型的生物,它们的习性、形状会根据环境、地域、气候条件而改变不定,然后,自然将它们分成各种小的种族,最后,每一种都按照今天的这种特征定型。祖先说可以让进化论显得更合理,只要有解释不清的事,搬出祖先的概念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其实,所谓的祖先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生物,没有人见到,也无法见到,它给人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用祖先来推断昆虫的未知世界,犹如用另一个更黑的黑暗来照亮黑暗,用一堆乌云来遮住阳光。可信的理由找起来要比祖先难得多,那就试着看看土蜂的祖先吧。
土蜂的祖先会做些什么呢?既然它是万能的,那它用在什么地方都是合适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在它的系谱里,有一种喜欢挖掘沙土和腐殖土,感谢老天,它们会在这里遇上金匠花金龟、蛀犀金龟和鳃角金龟的幼虫,这些是饲育后代的美餐。一步一步地,这些还没有最终定型的膜翅目昆虫有了地下工作所要的强健体魄;一步一步地,它们掌握了刺杀它那胖胖的邻居的聪明技巧;一步一步地,它们掌握了吃掉猎物但并不将它杀死的技术;一步步地让食物变得更丰盛,最后,丰盛的食物成就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强壮的土蜂。跨越这个过程,整个种族和它们的本能也就成型了。
这就是慢慢进化的步骤,缓慢而又不能令人相信的步骤,土蜂必须从第一步开始,每步都要成功才能形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们不再坚持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是认定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中出现了一些有利的条件,而且,随着这种危机四伏的饲育技艺的日臻成熟,这些有利的条件会一代更比一代多。所有的细微变化都是朝向一个目标,相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成型的整体,于是,古代的祖先变成了当今的土蜂。
尽管遭受到最务实的研究者的摒弃,尽管对它的结论是怀疑大于肯定,但一个含糊不清的说辞戏弄了几个世纪的谜和生物的未知,一种源于我们惰性的理论建立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以严谨和实践为日常准则,而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理,事情就会面目一新;放长眼光,我们会发现事情不像我们看得那么简单。从大局出发,的确是一项具有很高价值的工作,只有它才能带来真理。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一种建立在基础薄弱、适应范围狭窄这种条件下的普遍化。
当没有基础时,最容易犯这样错误的是孩子。对他们来说,不论是大还是小,长羽毛的就是鸟,爬行的就是蛇。对世界缺乏认知,他们就做最高级的普遍化,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看到多彩的世界,所以把事物简单化了。随后,他们会知道麻雀并非灰雀,朱顶雀并不是翠雀,随着他们的观察能力的提高,他们会一天一天地个性化。他们最先看到的只是相似,现在他们看到了相异,但是,他们总无法避免一些不合适的归类。
长大成人后,我的那个园丁在动物学上犯的错误,常会在他们身上出现,这是十有八九会发生的事。法维埃原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兵,现在是我的园丁。太难为他了,生活中数数比阅读更重要,但他数数都只是数个大概。在随我周游四方后,他思路开阔了,见识也广了,因此当我们谈到动物时,他会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在他看来,蝙蝠是一种长翅膀的老鼠;杜鹃是一种呆头呆脑的鹰;蜗牛上了年纪失去了壳后就变成了鼻涕虫;他还会把夜鹰看成一种喜欢喝奶的老蛤蟆,披上羽毛是为了到羊圈喝羊奶。法维埃是一个随心所欲、信马由缰的变形论者,他会胡乱地给动物联姻。他相信自己对一切的判断:这个来源于那个。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说:你看看它们多像啊。
当我们听到他说我们的男祖先会被雌猴的体形所吸引,我们能指责他的大不敬吗?当有人慎重地对我们说,科学已经充分证明,人是从一种冥顽不化的猕猴变来的,我们可以抛弃他关于夜鹰是披上羽毛的老蛤蟆的变形论吗?在这两种进化中,法维埃的说法似乎更让我接受。
大作曲家费利西安 · 戴维的兄弟是个画家,我们是好朋友。一天,在谈及人体结构时,他对我说:“是的,我的朋友,人具有猪的内部器官以及猴子的外表。”在这个忌讳称猴的时代,我把这句俏皮话送给那些希望人从野猪变过来的人。在戴维的眼里,内部器官的相似决定亲缘关系,人具有猪的内部器官—人是由猪变来的。
创造祖先的人看的只是器官的相似,不会考虑到才能上的区别。
他们只要参照骨骼、皮毛、翅脉、触角,就可以利用想象绘制出我们体系中所要求的系谱树。因为简单地讲,动物都是通过一根消化管形成的。一部机器的优劣不在于它有什么样的齿轮,而在于其成品的性质。客栈里马车夫手里的烤肉叉和布雷盖马表用的齿轮工作原理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认为这两种机械有联姻关系吗?我们会将一个在炉膛前翻动羊腿的,另一个以秒计算时间的东西混淆吗?
同样,动物能力的相同比器官相似更有说服力,特别是精神上的能力,这是最高级的特征。众所周知,猩猩与人类在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比较一下彼此的能力,差别是多么巨大呀!我们没有必要提到帕斯卡尔口中脆弱的芦苇人,芦苇人只是因为脆弱才被压倒,但他还是高于压倒他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人为自己制造了工具,工具可以使人的力量和灵敏度增长百倍;人也懂得如何取火,而使用火是人类进步的标志。运用工具和使用火的能力,虽然很简单,但要比脊椎骨和臼齿数目更能成为人类的特征。
进化论者对我们说,人一开始只是用四条腿走路的弱小野兽,后来有两条后腿褪去体毛并直立起来,他们还满怀得意地向我们演示浓密的体毛消失的过程。也许重要的不是来阐述哪些毛失去了、哪些毛留下来了,而要说明最初的人是如何获得工具和火的。能力获得的过程比毛的褪去过程更有研究意义,而所以忽视它是因为人们很难弄明白能力获得的过程。看一看进化论者是如何诡辩的,当它牵强地把本能拉进他的模式中时,他就变得前言不搭后语了。他们可以随意推断体毛的颜色、尾巴的长短、耳朵是低垂的还是直立的……进化论者心里清楚,这就是他的致命弱点。本能背离了他,并使他的理论大厦彻底垮塌。
土蜂给了我们不错的启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牵涉人类的起源。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土蜂祖先在历经一次次的试验后,才把花金龟的幼虫当做自己的食物。这个想象出的祖先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分成许多支,其中一支挖掘着腐殖土,在生活在土堆中的众多昆虫中选择了金匠花金龟作为食物,因此有了双带土蜂;而另一支也挖掘土堆,但是选择了蛀犀金龟作为食物,因此有了花园土蜂;而第三支在沙土上生活时,发现了鳃角金龟,因此有了沙地土蜂。除了这三支,毫无疑问还要外加其他支流才能形成整个土蜂的类群。各类群的习性在我看来大体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出至少三种我熟悉的物种。从单个的祖先到演化成不同种类的蜂群,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其中每一个困难都关系到进化的全局,如果其他困难得不到解决,克服其中的一个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样,难度就越来越大,为了成功,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实现每个条件的机会几乎都为零,如果只从数学上的概率来看,要整个实现是不可能的。
首先,花金龟的幼虫在昆虫界是非常特殊的、有限的,古代土蜂面对无数个昆虫的种类,只有花金龟的幼虫是它的正选,错选是无数个,这需要怎样的运气才能取得这种猎物呀!它又为什么单单选择那些神经系统集中、易受伤的幼虫做食物呢?
让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吧。金龟子的幼虫第一次遭遇攻击时肯定会反抗,并以自己的方式防卫,全身蜷缩起来,只留下一处螫针蜇过无关痛痒的地方。因此,土蜂新手一定要选准那个唯一的地方插入它那带毒的武器,而这地方还非常隐蔽。稍有差错,它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庞大的猎物在被毒针激怒之后,必然要将它碎尸万段。即使它能死里逃生,但必需的食粮没有了,它至少不会再按计划繁衍后代。金龟子的幼虫是土蜂家族的救星,所以第一次出击就要蜇中它的脑神经,尽管它的脑神经只有 0.5 毫米长。如果没有什么指引它,这样的手术该需要多好的运气才能成功啊!在猎物体表无数个这样的点中,一下子就选择对,那是多么难呀!
我们再进一步说。即使针戳到了一个致命的位置,使金龟子幼虫麻醉而不能动弹了,那该在什么地方产卵呢?前面、后面、侧面、背部还是腹部?不同的选择结果也大不一样,土蜂幼虫要在卵固定的那一点穿透食物的皮肤,入口一旦打开,它就会义无反顾地深入进去。如果进攻点选错了,幼虫可能会刺伤猎物的主要器官而吃不到新鲜的食物。
当我们把土蜂幼虫从母亲选的那一点挪开后,我们就会知道成功饲育是多么的困难。而猎物迅速腐烂后,土蜂也会随之死去。
我对解剖学和动物生理学没有细致的了解,我只得出大致的理由,细节常被我疏漏,所以我无法全面解释土蜂产卵选点的动机。我可以肯定的是,产卵的选点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在从土堆里挖出的样品中看,卵都是固定在腹部,在那个由消化物而呈现褐色斑点的地方,无一例外。
这一点真是太小了,在整个猎物身体上只有两三平方毫米的大小。
这一点对于饲育成功最有利,假如没有什么指引,雌蜂怎么会知道将它的卵始终附着在这一点呢?
还有一点就是,幼虫孵出来后,它要在定好的点上钻透金匠花金龟的肚皮,把颈部钻进猎物的内脏里。如果它随意乱咬,或只凭一时冲动和饥饿的迫使而选择进食的位置,那么被腐烂的食物毒死的下场就在所难免;保持新鲜的器官一旦受损,猎物就将一下子死去。所以它必须以一种谨慎的技艺享受这份美餐,吃完这一点才能品尝那一点,然后一次食用其他的点,这样井然有序地进食,直到吃完最后一口。随着金匠花金龟生命的终结,土蜂的进食也告终。如果土蜂幼虫是个新手,如果没有引导它的上颚就钻进猎物腹中,它哪会有什么运气吃这种会使它毙命的食物?这种运气能让它像一只贪婪的饿狼对待羊羔一样,把羊羔拖到一边慢条斯理地剖开,再把它撕成一片一片大快朵颐。
饲育必须同时满足 4 个条件,否则就不能完成,而每个都是从无数个错选一次抓住唯一的正选,实现的概率都几乎为零。如果土蜂没有掌握将螫针准确刺入猎物那唯一致命点的技术,它就不会捕获一只神经系统非常集中的金匠花金龟的幼虫。如果土蜂不懂得在哪个点固定虫卵,它就不会对进食的艺术了如指掌。就算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如果土蜂不掌握一边进食一边使食物保持新鲜的技术,那么一切也都无法进行下去。要么同时具备 4 个条件,要么彻底走向灭亡。
可以估算得出,这种维系着土蜂或者它祖先命运的概率是多少。4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构成了这种复杂事情的因子。就算这种巧合是一种偶然的结果,那么现在的土蜂又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探讨下去吧!
换个角度看,达尔文的理论也会与土蜂及其猎物产生矛盾。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土堆里,生活着 3 种金龟子幼虫:金匠花金龟、蛀犀金龟和鳃角金龟。它们的身体结构几乎是一样的,它们的食物也都是腐烂的蔬菜。
它们习性一致,在不断更新的地道中生存。虫茧都埋在腐土里,呈大大的卵形。环境、食物、活动方式、内部结构,一切都是如此的接近。但是,金匠花金龟的幼虫与它的同类们相比,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甚至在金龟类乃至在昆虫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它靠背部前行。
如果说结构上有细微的区别,那么这丝毫不影响研究者的分类,但是如果有一只腿脚健全的昆虫,却有意将腹部朝天地翻过来行走,并且永远只保持这一种奇怪的姿势行走,这就值得研究一下了。它是如何掌握这种奇怪的前进方式的?为什么它要刻意与其他昆虫不同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最新的科学解释是:为了适应环境。金匠花金龟幼虫的生活环境是土堆不断坍塌的地道,它必须蜷缩起来,贴着地道的隔板,支撑点一面是肚子、一面是背脊,通过这两个有力的杠杆才得以前进。就像疏通烟囱的工人,只有用背、腰、膝作支撑,才能钻进烟囱狭窄的管道里一样。腿的用途越来越小,几乎为零,逐渐变得无力,很可能像那些无用的器官一样消失;背部则不同,它是前进时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是就不断被强化,也因此长了许多强壮的褶子,还竖起一些钩子或毛;这样日复一日,金匠花金龟幼虫因为不行走而丧失了行走的能力,于是改用背部行走了。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更好地适应地下的生活。
乍一看这还算说得过去,但问题是,为什么蛀犀金龟、沙土里的鳃角龟、植物土里的缩绒鳃角金龟幼虫同样也生活在腐殖的土内,却没有为适应环境而掌握这种用背行走的能力呢?在它们的通道里,它们也像金匠花金龟开始那样按照疏通烟囱工人的方法,前进时用背脊为支柱,可它们并没有仰面朝天呀。难道它们不受环境的制约吗?如果仰面行走的原因是进化和环境造成的,那么我至少可以负责任地说,其他各种金龟也必须仰面行走;既然它们的结构相近,习性也应该一致。
我不太相信那些空洞的理论,因为它们无法解释在相同的情况下出现的两种不同结果。太可笑了,他们就是在痴人说梦。比方说,老虎皮上的黑纹,进化论者会把它看成是环境使然。他们会这样解释:阳光透过竹林,动物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便采用了环境的色彩,光线为野兽提供了正常的毛色,阴影则提供了那些黑纹。
就是这样,我这个不接受这种解释的人显得很难缠。如果这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我也没必要当真。但是,这不是玩笑,它是很正式、很严肃的科学话题。可叹!可叹!可叹!图塞内尔在他那个时代对自然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阴险的问题:“为什么鸭子的臀部有卷毛?”
据我所知,没有人能回答这个不怀好意的提问,那时还没有进化论,但今天可以一下子就解释清楚,这就像老虎的皮毛一样清楚明白,一样是有理由的。
幼稚的话已经够多了。金匠花金龟的幼虫用背行走,是因为它始终这样行走。环境不能造就昆虫,是昆虫生来适应环境的。对于这种简单而又老生常谈的哲学,我还要加上苏格拉底的一句哲言:“我知道得最清楚的东西,那就是我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