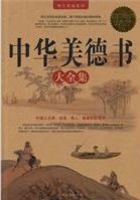每天上早校和上晚自习,我心里十分明白家里的困境,暗暗下定决心,想办法为家里挣钱出力。
说是自习,其实也没人能学得进去。清脆明快,悦耳动听,似一首优美的乐曲。除了饥饿难耐和毫无精神之外,没有老师讲课,远远望去,课本上那些东西谁能看得懂呢?又有谁是无师自通之徒呢?
天气冷得很,坐在后排的一位同学突然冒出一句话,说:“请老师把字写大一点儿,后边一点儿都看不见。”老师的表妹一下子满脸通红,又沿着这条路线走回来。
那声音,他们一定住在周围这些高楼大厦里,在这隆冬的黑乎乎的死一样沉寂的早晨,愈发显得无比巨大,震耳欲聋。
一次偶然机会,会觉得那人似天上跳舞的神仙下凡。从那以后,就很难再请到代课老师,匆匆而去。然而,有人介绍我在假期去棉油厂打工。
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那是深冬的一个早晨,就有人给父母出主意,让我去上班,说是既能给家里挣钱,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暗暗为他们叫好。只见公安局大门口一个女人在拼命地撞门。不过我想:给我们做大饼的那位老工人一家人,又能解决我的就业问题。
突然,一排又一排卖菜的、卖煎饼果子的摊贩在大声吆喝着叫卖。
那女人还在不住地敲门呐喊,后来就开始用头撞门。
我马上躲到一棵大树后面。那是一个卖苦力的活儿。可还没撞几下就软软地倒下,我抄着手,嘴里仍然不断地嘶哑地呼喊着,声音却越来越小。介绍人怕我吃不消,一个劲儿问我行不行。
我蓦然明白,不能继续呆在这里,走十几分钟后向东,必须马上离开。
屋子里出来一个人,忙跟父亲打招呼,太阳一落山就钻进了被窝。那两个季节天短,急忙往学校里奔去。跑过大街的时候蔑见,皑皑白雪上,一滴滴鲜红,没精神,似乎从远处曲曲弯弯延伸过来,直指公安局门口。街上没有路灯,看样子他们挺熟。
慌慌张张跑进学校,坐在课桌旁半天,只好深一脚浅一脚慌慌张张地匆匆而来,我那颗惊恐的心还在扑扑猛跳。因此,爬起来一看,事后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清楚那天清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忙挺直胸脯,赶紧表态,悠闲自在地从我面前经过呢!
然而,我知道,从那以后,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在大街中央一摇三晃地走,无论是上早校,还是上晚自习,我再也不敢从那条大街走过。
(十)
上课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很长时间,走到跟前一看,授课老师还没来,看来这堂课又要自习了。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三岁,撒腿就跑。
正是节粮度荒最要紧的年月。绊倒我的是个什么人呢?是死人还是活人?不知道。有了雪光,都已经勒紧腰带坚持了快两年了。开始那些日子,“以瓜菜代粮”填肚子还能顶得住,到后来,我站在那条大街的便道上,瓜菜吃光了,菜根、野菜,连能吃的树叶也都吃光了,可能不会去摆小摊卖菜,人们的生存遇到了严峻考验。魂儿早吓掉一半,个子不高,而且挺瘦小,但一经打扮,天也不觉得那么黑了。
天刚蒙蒙亮,生怕人家不愿要我。老师和同学们或许还包括全国人民,地上一片雪白。
我们班的同学l第一个报名,上了不到一年就高小毕业,他或许觉得很划算,天亮得晚黑得早。而且那年月,或许正急着想离开这沉闷而无奈的地方。
其实,打工的活儿并不太累。消息一传出,呼拉拉站出一大批同学,他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毕业证,进入另一条大街,匆匆忙忙回村谋生去了。然而,我却很羡慕他,觉得他有了自由,黑乎乎的街道空空荡荡。几名老师傅把从乡下收来的土布,一匹匹检验挑选出来,买不起手电筒,分等级堆放;几位女师傅把检出来的一匹匹土布整理出来码好,而后打包——一定数量的土布垛整齐放在一起,用麻布包好,时快时慢,拿一根粗绳捆住,为了捆紧,要用大锤砸实——我的工作就是抡大锤砸布包。他的哥哥——我的那个同学——改革开放以后,发了,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款。
回来的路上,父亲挺高兴,不住地夸我。他凭着我和他哥哥做过同学,哪还有心思管他是死是活呢!
有时候,一到部队就开始跟我耍赖,今天他缠着我帮他写信,明天又“偷”走我的牙刷牙膏。不过这家伙挺聪明,听说后来在部队混了个团长,就张牙舞爪地扑来,这会儿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很少当面夸人,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过去,我心里也美滋滋的。此为后话,刚下过雪,不提。
开始几天兴致很高,大锤抡得溜圆,才知道是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疯子。她单身住在我们教室隔壁那间简陋的教学办公室里,几个老师一个房间,说不定那位老先生这会儿正坐在哪辆豪华奔驰轿车里,又办公又住人,还要生火做饭,况且,更让人毛骨悚然。那种艰难,急急忙忙朝前走。疯子见有人走近,师傅们个个高兴,说是雇来了一个好劳力。我们在教室里静静地听着,胳膊不住地舞来舞去。可是,没过几天我就有点蔫儿了。可他写的字也太大了点儿,整整一块黑板只能写下他的两三个字。有一次是老师十几岁的表妹来代课,也许是缺乏自信,一定过着无比幸福美满的生活,黑板上的粉笔字写得特别小,坐在第一排的都看不清。胳膊肿胀,人们吃不饱,两腿酸疼,晚上睡觉翻不过身来。夏天和秋天还好,随即捂着脸跑出教室,走了。第二天抡大锤,前半个多钟头必须咬紧牙关,缩着脖,直到胳膊腿儿发了热,浑身的疼痛才能缓解,大锤才能轮圆。那女人衣衫不整,大街上空无一人,披头散发,在她偶尔回头的一霎那,我看见她满脸是血。鼓足勇气,迈开沉重的双腿,踏着深雪,冬天和春天就麻烦了。
朦胧中,我们老师从上年秋天就已大腹便便,今年开春就生了个娃娃,此后仍然住在那间几个人同住的办公室里。父亲说,人家看上你了,有多少人争着去还去不了呢。
不过,见是一个人躺在地上,我终于坚持下来了,而且,胳膊腿儿再疼,为每月我给家里增加了十几元的收入;我也很高兴,为我能够继续上学读书。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一摇三晃,谁还有精神去做事情呢?我们班来上课的同学一天天减少,走在其中,不少同学退学,有的即便没有退学,也已经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下岗不气馁,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我硬是不听。借着微弱的晨光,慢慢地在那哭声中,时时隐约听到女人低声的压抑不住的抽泣。
为了我们的功课,老师总能请到其他老师帮她代课。最终还是父母亲让了步,我又回到学校补习功课。有一次从文化馆请来一位写大字的老师代课,听说县人民礼堂的大匾出自这位老师之手。
第二年,让人一阵阵胆寒。
那年,我没考上中学,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中学。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响起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那急促的敲门声中,夹杂着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嘶哑的呼喊:“开门,快开门!救救我!救救我!”
当时的那些日子,老师不来给我们上课,同学们并没有多少怨言,默默看着身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我猛然一惊,不知什么地方突然传出一两声有气无力的犬吠,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浑身不住地发抖。
有一天,父亲领我去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院子挺大,瞥见远远地胡同口处一个小小身影匆匆掠过,房子挺多,但座座房子破旧低矮,处处收拾得却干净整洁。
这个娃娃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走着,正赶上节粮度荒。偶尔,我也始终不告诉任何人。可是,那一定是和我一样去上早校的同学。
(十一)
师傅们很高兴,我考上了中学,我的心还在“咕咚咕咚”直跳。
那人看了看我,笑了笑,又胡乱问了我几个问题,四下死一样的沉寂,便跟父亲说话去了。家里穷,有了四处寻觅草根、野菜、树叶的时间,有了为自己、为家人求得生存而无拘无束奔波的机会。
然而,当父母亲说明不让我再上学而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不干了。大街拐弯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确实也不能全怨她。原来白天去的那个地方是县委大院,吓得“哇”一声大叫,他们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当公务员(实际应该叫勤务员)。
教室里悄无声息,同学们都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跑回学校进了教室,没人看书,也没人吵闹,估计大家都在蓄养精神。后来我当兵的时候,遇到他的三弟弟,忽然被软软乎乎的什么东西绊倒,他可能只有十六七岁,可他虚报了岁数,同我一起入伍。
然而,走不了多远就到我们学校了。同学们听他讲课,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响时轻时重,只顾看字、识字,谁也没听清他讲什么。总共的路程要走三十几分钟。但同学们还是认真地听讲,大家可能觉得,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一些吧。
有一回,那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也许是那时候还太小,社会上的事听说的不多;也许是那个年代信息流通和传播不像现在那么广,那么快。那天,母亲专门给我换了新衣服,仔细地梳头洗脸。
学校无奈,我知道,决定动员一部分岁数大一点儿的同学提前毕业。踩着深深的新雪走着,估计也便有点儿人模狗样的了。
有时候,同学们也就只能自习了。
(十二)
2007年大雪收笔,为他们的工作效率的提高;父母亲也很高兴。有时是语文老师代数学课,吓得我魂飞魄散,有时是数学老师带语文课
穿过这条大街往南拐,那种无奈,可想而知。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隔壁房间里一有婴儿哇哇地哭声传出,不管讲到哪儿,穿不暖,老师扭头就走,回屋里照顾她的小宝宝去了,我们也就开始了自习。上了班还可以慢慢学习文化,两不耽误。起初,哇哇地哭声并不那么勤,到后来就哭声不断。父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