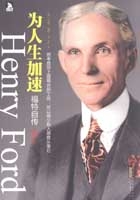还是在1921年初冬时节,陈独秀与当时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商议,提出了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的想法。办这样一所学校,既可以为党培养从事妇女运动的干部,又可以作为掩护地下活动的机构。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同意,并派李达兼任校长,具体筹办的事情由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负责。
王会悟与李达是1920年下半年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结为夫妻的,婚事由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一手操办。沈雁冰这个比他年龄小几岁的表姑母已经不是三年前湖郡女塾里那个热情激进、有些毛躁的女学生了,孔德沚当初就是从她那里学习到不少的新名词。五四运动给王会悟的思想带来很大震动,她毅然只身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几经周折后,在上海学联的介绍下,她进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会长黄兴的夫人徐宗汉那里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认识了来女界联合会联系工作的李达,两人情投意合,很快热恋起来。
王会悟后来加入了由陈独秀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一个准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筹建期间,王会悟协助李达为成立大会选择安排了会场和代表住宿地。在“一大”召开时,王会悟担负了为会议警卫放哨的任务,她及时发现会场附近的异常情况,使代表们迅速安全地撤出。此后,她又出主意,想出去嘉兴南湖租一条游船的办法,保证了“一大”顺利圆满地结束。王会悟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而且成为一个办事干练的革命者。
学校很快办起来了,叫作平民女校。开始学生不多,而且都是外地的,本地学生一个也没有。全校学生只有二三十人,文化程度又参差不齐,便设了高级、初级两个班和一个工作部。王会悟、高君曼在高级班作旁听生,同时兼初级班的教员。高级班学生有王剑虹、王一知、蒋冰之等六人,要学习英语。沈雁冰受李达之托兼平民女校的英语教学工作,教王剑虹等六人。王剑虹后来与瞿秋白结婚,蒋冰之即是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丁玲。
平民女校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沈雁冰每周三个晚上去教英语,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人都去讲课,沈泽民从日本回国后也在那里讲过课。学校的主课是妇女运动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因为学生不多,学校就想办法吸收青年女工,为她们办起夜校,教她们识字读书,讲授一些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如何团结斗争的革命道理。
孔德沚那时还在爱国女校学习,但她很羡慕平民女校的学生,因为受到周围亲友的影响,她也向往参加妇女运动的工作。平民女校成立不久,孔德沚在振华女校时最要好的同学张琴秋也来到上海,进了平民女校。张琴秋在这里结识了沈译民。
1923年春季的一天,沈雁冰认识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瞿秋白。他们是在上海大学一次教务会议上见面的。瞿秋白刚刚受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沈雁冰则在中文系、英文系兼职任课,讲授小说研究、希腊神话等课程。
这所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二所学校,并不是社会上那种正规大学,而是被称作“弄堂大学”的那一种,但是它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上海大学的开办有一点偶然性。原来这是一所叫做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私立学校,校长发财心切,打出名流、学者的招牌招揽学生。
他在报刊登出广告,宣传有多少著名学者在校任教,如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于是,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慕名而来,而且都是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开学上课后却不见广告上的那些名人授课,学生们知道上当受骗了,就团结起来与校方斗争,索要回已交的学费,并且赶走了校长。
学生们原本就是仰慕陈独秀等具有革命思想的名人而来,其中亦有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青年,于是,他们派代表找到共产党人,要求中共接办这所学校。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考虑,认为还是以国民党名义出面办学,有利于这所学校的发展,从各方筹款也方便,就让学生们派代表去请国民党中著名的人物于右任出面。
1922年,更名为上海大学的这所学校在闸北青云路青云里开办了。于右任担任校长,但只是挂名,实际办事、教学的教职人员全靠共产党人。学校设有社会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四个系,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担任管理学校行政事务的总务长。
沈雁冰虽然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但早就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
瞿秋白与郑振铎五四时期曾在北京一起办过一个周刊,郑振铎多次谈起瞿秋白的才气,文笔过人。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考察时写成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书稿,都是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发行的。从这两本书中,沈雁冰不但对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而且非常欣赏作者风趣幽默的文笔和善于描写的手法。他记得书稿是由陈独秀力荐来的,那时瞿秋白尚未回国。陈独秀称赞瞿秋白的文章是“贾生才调更无伦,文笔、风格都有过人之处”。沈雁冰则从两部书稿的书名恰是一副巧妙的对联,想象到瞿秋白一定是有一种文人风流潇洒的气质。可惜商务印书馆不喜欢“饿乡纪程”四个字,将书名改为《新俄国游记》,平淡乏味,落了俗套。
在校务会议上的这次见面,使沈雁冰得以结识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而瞿秋白对沈雁冰也毫不陌生,早就知道他为新文学的成长所付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战斗在领导革命文学运动的第一线。
瞿秋白的确文如其人,是个风趣幽默、性情洒脱的人,与沈雁冰的严谨、不苟言笑有很大不同。这一年秋天,两个人的好友郑振铎新婚大喜,新娘是高梦旦的小女儿高君箴。郑振铎决定举行一个新式婚礼。可直到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才发现他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
按照当时流行的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双方家长、介绍人、新郎新娘的图章。他立刻写了一封信,找人送到瞿秋白处,请秋白为他代刻一章。不料,送信人带回瞿秋白的一封信,信上手写了一张“秋白篆刻润格”:“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知道秋白素喜幽默,不是真的索要刻章的润格,恐怕是手头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刻章,便又转求沈雁冰代刻一枚。他知道沈雁冰也会篆刻,只是不及瞿秋白的技艺高。
沈雁冰连夜赶刻了一枚印章,第二天上午赶到郑振铎寓所,亲手交到郑振铎手里。过了一会儿,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大红纸包,上书“贺仪五十元”几个字。郑振铎遣走送包的人,口中正说着:“朋友之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沈雁冰已经替他把红纸包打开了,只见三枚印章:一枚是为郑振铎母亲刻的,另外两枚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新郎、新娘的两枚印章可以合为一对,上面分别刻着边款“长”“乐”二字。这真是寓意双关:郑、高两家都是福建省长乐县人,两个长乐人合为一家;新婚夫妻长乐,表示白头偕老的吉祥祝福。瞿秋白可谓奇思妙想。还不止于此。沈雁冰悉心在那里计算了一下: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50元整。秋白幽的这一默,实在出人意外。他与郑振铎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知篆刻水平不如秋白,沈雁冰让郑振铎将他刻的那枚印章收起,改用秋白刻的盖在结婚证书上。郑振铎、高君箴原不打算用章,只签字,见两枚印章刻得有趣,也用了秋白刻的章。
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赶来贺喜。郑振铎请他讲话,他也不推辞,但不说那些这样婚庆场合下人们常说起的祝福语、吉祥话,独出心裁,用了《红楼梦》上一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作题目,对着出席仪式的男女宾客,大讲一通男女恋爱要自由,妇女要争得解放的话。他讲话的语言亦庄亦谐,满堂宾客中,有人听得瞠目结舌,有人听后鼓掌欢呼。
沈雁冰、瞿秋白这些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不为养家糊口,而是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教课非常认真。沈雁冰所教学生中,丁玲、施蜇存、戴望舒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沈雁冰在中文系、英文系任课的课时虽然不多,但后来他撰写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小说研究ABC》、《神话研究》等著作,就是以此时教学中的研究、积累为基础成书的,足见其讲授的课程的份量和他为此花费的心血。
丁玲是在平民女校停办之后进入上海大学的。她后来回忆听沈雁冰讲课的感受时说:“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讲的《奥德赛》、《伊里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产生过许多幻想”。“我还读过沈先生《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不讲课外的闲话,也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们以为不打扰他最好。早在平民学校教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英译本时他也是这样。”丁玲走上文学道路受到沈雁冰很大影响,从她的回忆中也可以一见沈雁冰的性格特征。
1923年7月,中共中央将建党以后成立的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兼管江浙两省党务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沈雁冰当选为五位执行委员之一,邓中夏任委员长,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当时上海的党员分为四个小组,沈雁冰、张国焘、沈泽民、刘仁静等人在商务印书馆那一组(第二组)。这时,国共两党开始实现合作,在中央指示下,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上海及江浙地区与国民党合作,发动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进步力量参加革命的工作,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等八人为委员。
因为担负了这些党的工作,沈雁冰更忙了,有时甚至天天得开会,用他的话说,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