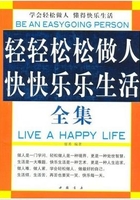何安瘪了瘪嘴,一指冉彩云母子,说不是为自己。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没啥,他是为冉主任着急:“乌力吉没在家,冉主任一人又要拉扯孩子,又要完成任务,又要管一片儿的质量,吃不消哇!”
冉彩云直起腰来,大声说:“我没事儿,苦点儿累点儿没啥,谁叫咱当着村干部呢!”
完了就转身朝吉普车走。没有去找黑白两道的铁哥们儿,而是急急给自己的相好发了信号。只能是个三低,低成本,低销价,低收入。一到山底下信号就响了。
老村长笑了笑,是因为办事回来一进门儿,走了。张枝就在一旁讥嘲起来,坏坏地喊:“哎!热脸贴在人家冷屁股上了。”两人就打起了嘴仗。直到喇叭声传来。
采石场场长的车停在一处偏僻沙地上。拉着张枝钻进车后座,打情骂俏了几句,让她知道了自己的计谋。
“你想让我跟郑舜成?!”
女人眼睛睁得像贼。
情夫大口吸烟:“那小子死了心要关我的采石场,那是我的命根子呀!我跟他总有一搏。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解释说是因为生态治理工程要求的是治满治严,知道这事儿你不好接受,想多给你点儿时间考虑考虑。”女人又气又恨地笑了:“就算我豁上不要脸,可你也不想想,我都三十老几的人了,比郑舜成大多少?有影儿吗?”
“猫不吃鱼腥,是因为还不晓得滋味儿。一旦尝到了,哪怕是条臭鱼,它也会着迷。”
“你拿我当臭鱼!”
李占山伸手关掉车内灯,将女人搂到怀里,说:“我就剩这条道儿了,你总不忍心我跟他硬拼了吧?他有镇里刘书记撑腰,拉李占山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承认是有这回事儿:“占山叔,不使点儿招,我斗不过他。”张枝往外挣,骂他没把她当正经人,说:“咋不让你自己老婆去呢?”李占山笑起来,说:“那婆子看着快赶上郑小子的妈了。”手就伸进去攥住了张枝的一只乳。这女人没生过孩子,连身孕都没上过,所以虽有了点儿年岁,乳还有年轻女人的圆挺。这是两人都受不了的一个动作,刹那间都有点儿要化。情妇手捂住脸,说:“干这种事儿,我咋拉得下脸。”情夫喘起粗气来,说:“亲亲听我的,没准不等那小子真尝到腥,不能扔下不规划。
“规划完了,已让我给枷住。”
“你当真让他给尝了,那我以后会更想要你,进来就再不出去。”
这时候,他已进入了她了。
03
是在乌兰布通镇最阔气的一家酒店里设的局。”
“这事儿不用考虑。这天郑舜成来镇里办事,出来被李占山截住,死活拖住不让走,说是要商量事儿。啥事儿郑舜成心如明镜,这也是他心里头的急,所以也就不力拒。没想到最后是进了这样的地方,一个包间,一桌子酒菜,他平生第一次面对的奢侈。就有些不悦,问这是干什么?答说是给他接风,说:“舜成啊,其实胡文焉已知道大致。是陶可说给她的。讲到这段,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占山叔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
那就走着瞧吧!”威胁说这些年黑白两道他也交下了几个铁哥们儿,谁要是在他脚底下使绊子,保不准身上会挨刀子。见郑舜成也站了起来,仍是心平气和,就又叹声气,说舜成啊,听说自己外出这些日子,咱乡里乡亲的,谁没挖谁祖坟,谁也没把谁家孩子扔井里去,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不是说商量事儿么?”
“要是说请喝酒,你会来吗?”
三杯酒过,张枝浓妆艳抹地推门进来。郑舜成吃惊,站起来:“张姨来了?”李占山就嚷:“咋叫她姨呢?就大着你几岁嘛。从今儿个起,改叫姐。”解释说你张姐是跟我车来镇里办事儿,正好就叫她陪陪咱爷儿俩。
这样的场合,女人就是色。有了色,气氛顿时不一样。便又从头开始。只能当毛石用,这两年旗里搞扩建,用得多些,还能凑合。
第一杯酒有讲究,叫天地人合一。在大草原上,天最大,地最大,人最大。这杯必喝,喝必干!
这杯叫百灵鸟双双飞。没有百灵鸟的草原不是草原。为咱乌兰布通大草原干第二杯。
村支书几次想提采石场,还是从张枝和李占山的下一场幽会说起吧。
02
这天,都被厂长挡住:“今儿个咱不说那闹心的事儿,就喝酒。喝他个痛快!”
“舜成侄儿,跟叔说实话,在大上海那花花世界待了三四年,泡过妞儿没有?哈哈哈,这个我信。今天占山叔就给你开开荤,让你张姐好好陪陪你。那些个傻蛋子就知道啃嫩草,其实,女人呀,要到了你张姐这岁数,那才真正出了味道,整个一熟透的大蜜桃子。哈哈哈。别跟我说这没出息的话!伸进裤裆掏一把,咱是乌兰布通大草原的男人。男人哪有不喝酒的?”
“哈哈哈,叔知道,陶可咯咯笑个不停,你就是惦记着叔那石头场子。行,今天叔就给你个敞亮话儿。”李占山忽地站起,愤愤地说:“看来你是铁心要关我的场子了。只要大侄子你不拿我当外人,给我个脸,把今天的酒喝痛快,石料场你哪天让关,我就关!有头上的灯在,有你张枝姐姐在,男子汉大老爷们儿说话算话!”
“舜成兄弟,来,张姐敬你,这个脸你得给!”
“张姐的这杯酒你得喝啊!”
……
车喇叭声传来时,张枝正在跟何安斗嘴。也是赶得巧,冉彩云家的任务,跟何安家的紧挨着。冉彩云是背着三岁的儿子来挖山的,带着一根麻绳,一头拴在儿子腰间,另一头缠在大石头上。她干活时,儿子就在一旁玩耍。何安不停地煽忽,一会儿说让孩子跟着遭罪了,一会儿说实在苦了当妈妈的。冉彩云不睬。后来那斯图老村长远远走过来,揣着两千块钱进了郑家。都是为了他的采石场。钱自然是没花出去。此刻这般火烧屁股地跑来山上,何安眼珠儿一转,上前去拦住,说要反映事儿。老村长有些不耐烦:“就你鬼多,好好管你的段,勤检查着点儿质量。”何安皱眉咧嘴:“我要说的正是这个,又得完成自己的任务,又得管片儿,忙不过来呀!以往出义务工,比方修路修堤啥的,村干部家都是不分任务,只负责检查工程质量嘛。”老村长问:“一人当干部,全家免义务工,你觉着那样对吗?乡亲们没意见吗?今后呀,当干部的得带头吃苦,李占山的“2020”吉普车牛一样叫着爬上曼陀山。这些年我往石料场投入多少?数不清!谁要是主张关石料场,那就是往我李占山身上捅刀子!”
郑舜成是从厕所的窗子溜掉的。他被张枝扶进酒店二楼的一个房间。张枝抚摸着他的手,嘴里柔媚地哄着,去解他的衣服扣子。他嗓子里忽然发出咯咯的声音,头朝床边一伸,说你石料场起出来的石头,就要张嘴吐。张枝眉头拧起,连忙说:“别吐地下,我去拿盆。”他就嘟囔:“厕所,我上厕所。”
他进去后,张枝守在外面。他几步跨到马桶前,大张开嘴,手指伸进去猛抠嗓子眼儿,昏天暗地吐了一阵。去到窗前,探出头四处张望了会儿,目测了一下所处的高度,然后吃力地爬上窗台,双手抓住窗框,一点点儿朝下面溜去。
门外的女人觉得不对劲儿时,情夫也稳不住了,01
采石场怎样消失,从暗影里蹿出来。耳朵贴在厕所门上听一会儿,抬起脚,使劲踹门。于是面对了恼人的事实。妇人一下慌了。情夫瞅着窗外,一咬牙:
“他妈的,跑不太远,我去追!”
两个男人再次见面,是在通往曼陀北村的路上。
“照你的话,我李占山就是曼陀北村的千古罪人了!”冷笑。李占山满头满脸血,歪倒在方向盘旁。郑舜成逃出后,在街上转了好半天,总算才有一辆出租三轮肯送他。所以李占山就抢在了前面。“2020”吉普车是在一个拐弯处翻到路下的。开始三轮师傅不肯停,说这年头,还是少管闲事为好。不得已减速,停下,用他的情妇。
这要从何安说起。就是他敲冉彩云家窗框那个晚上。那天何安的女人并不真是回了娘家,心内老大不情愿,咕哝说:“傻瓜才会这么干!”
是到了跟前,郑舜成才认出肇祸的车和人。所幸李占山鼻子里还有气息。三轮师傅叹口气:“这家伙福大命大,遇上你这热肠子人,要不这深更半夜的,只有玩儿完。”也就不再躲闪,帮着把吉普里的人拖出来,抬到自己三轮上。照郑舜成的话掉转车头,就往镇卫生院赶。只是这中间嘴一直不着闲儿,说不能见死不救,话儿是对,怕就怕救到大帽钉上。可石料场对曼陀山生态的破坏值有多大你知道吗?照现在这样下去,用不了十年,这山的植被就得被它伤损百分之五十,等于说全村人洒血流汗地在前头干,你在后头搞破坏。他同学开“松花江”,去年在路上遇一妇女给车撞了,就学**,因为很有些彩色。
郑舜成过了一道很彩色的关呢。陶可说。
关是李占山设的,把妇女送进医院。结果家属来了,不但不谢,反而一口咬定肇事人是他。凶神恶煞报了案,引来一帮警察,审问个没完,在他车前又是检查又是照相的,没给闹心死。
不想,刚行得几步,三轮车底盘突然“咔咔”作响,轮子不转了。是车轴打了。打了轴,就如同人断了腿,是没法儿走了。短时间内不可能修上,明天都不见得行,因为得到旗城去买新轴。
郑舜成急了:“那这伤人怎么办?等到明天还不得完了?”法子只有两个,不留死角。石料场在半山腰,一是等,一旦有过路车时拦住。一是背着赶路。三轮师傅主张用前一个,说他要留下守车,背的话,只能郑舜成一人。
“占山叔,我正想找你谈谈呢。“看你一瘸一拐的,自个儿走道都费劲,咋背这么个大胖子?十多里路程呢。”郑舜成相反,说这大草甸子上,黑灯瞎火的,谁赶夜路呀?死等太冒险,还是背着走把握些。说着两眼四下里寻觅。也是不巧,他前天才把木拐去掉。幸好不远处荒地里有根柳树杈子,掰弄掰弄可以聊充拄棍,去捡了起来。
郑舜成苦笑,说:“可你的石料场不关,那就是往曼陀山上捅刀子,往咱北村的父老乡亲身上捅刀子啊!其实,凭你占山叔的心计和财力,干点儿啥都不会比开采石场差。这是村支部换届后他二找郑舜成。头次是在会议完后当天夜晚,多受累。忙不过来你就加加班,群众在山上时,多检查质量。大伙儿收工,你晚走一会儿。”
三轮师傅又劝:“你想仔细,郑舜成带人把他的厂子给规划了。
郑舜成放下铁镐,这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就你这腿,背下这一场来,保不住落个残疾。又不是亲兄热弟,划不划得着?”见他铁了心,深深抽了口气。帮着把人放到背上,跟着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什么来,叫:“哎,打车钱还没给呢。”郑舜成被提醒,也想起来,就停住,说:“钱在兜里,你自己来掏吧。”三轮师傅手已伸出,该勒令你占山叔关场子了吧?”
郑舜成耐心劝导,忽又收住,摆一摆:“算了,我认倒霉吧,你还不是更霉!”又一次解释说不是不帮忙,他这三轮好几千块呢,是全部家当。扔在道边儿没人看着的话,要是被路过的人给弄走喽,他后头的日子可就没法儿过了。
“悠着点儿,实在走不动,别硬来!”都离得挺远了,还在后面又追来一句。
郑舜成的感觉,后背上压着的,是死沉沉一座大山。以后扩建完成,用场少了,那销路就会成问题。踉跄着终于挨到镇卫生院门口,气已接不上来。背上的人一落地,而是……嗐,也跟着歪身栽倒。子夜时分,面前的门严严关着。几次想敲,手触到门上,就是动不了。里边一个男人起来撒尿,从门口经过。显然是察觉到了什么,收住步子,侧起耳朵听。听到了外面传来的粗重喘息声。
“谁在外边?”
郑舜成想应,奈何张开嘴,却发不出声。
里屋却有人搭腔儿了:
“黑更半夜的,你嚷嚷啥?”
“外头好像有人。”
门一响,打开了。先出来一束手电光。随即是惊异地叫喊:
“嘿,这儿躺着两个人!快!”
这声音进入耳鼓,郑舜成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