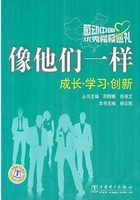二梅:“我们也在找他。他来过信吗?”
胡大娘:“没有。好几年没来信了!”
二梅:“那……前几年来过信吗?”
胡大娘:“来过,在俄什么……”
二梅:“俄国!他从俄国来过信?”
胡大娘从枕头里取出一张破烂不堪的信纸:“每次进城,我都请教书先生给我念上几遍。你认识字,也给我念念吧!”
二梅念信:“我的好妈妈,远在万里之外的儿子,天天在想您老人家。告诉您,我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姑娘叫卡佳……”
卡佳听见她的名字,像触电一般叫了起来:“啊!他在叫我!我是卡佳,我就是卡佳。妈妈!妈妈!我就是卡佳!我就是您的媳妇卡佳……”
她紧紧抱着胡大娘说着,喊着,哭着……
南京。老中医家,胡天福躺在床上,望着卡佳的照片。
老中医端了一碗莲子汤走来:“伤口不疼了吧?”
胡天福:“不疼了。谢谢你啊!”
老中医:“谢什么!都是民国时候的人了,你看,我这头上的辫子!”
胡天福:“剪了?”
老中医:“剪了!拖了二百六十八年的马尾巴,太长了!不剪,还走得动路吗?”
鲁迅拿着一份电报,笑嘻嘻地走来:“天福!电报!张学勤欢迎你到法国去治腿!”
胡天福看着电报,老中医一直在嘀咕:“治腿,就在中国治嘛!还到什么法国!”
鲁迅:“老先生,中国的医学还是不如人家西方。”
老中医急了:“哪一点不如人家?西方,它有中医吗?”
鲁迅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哈哈,中医,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西方怎么会有呢?”
老中医:“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姓中,不姓西,对不对?”
鲁迅:“对,可是……”
老中医:“别可是可是的!拿胡天福这条腿来说,如果让我来治,就不会被锯掉,你信不信?”
鲁迅:“我信。西医就知道开刀。”
老中医:“一刀下去,血哗哗往外流。他中了八颗子弹,动了八次手术!”
鲁迅:“不动手术,那子弹能取出来吗?”
老中医沉默了,连连点头:“这倒也是呀!”
鲁迅:“子弹取出来了,可他腿上的伤被耽误了,所以不得不锯掉!”
老中医:“可以不锯的!”
鲁迅:“是可以不锯,可已经锯掉了,怎么办?只有再把它安上。”
老中医:“安上?怎么安?”
鲁迅:“安假腿!”
老中医:“安假腿?乖乖,没听说过!”
鲁迅:“中医不行吧?”
老中医:“不行。”
鲁迅:“这就要向人家西方学习了,是不是?”
老中医点头:“是。”
鲁迅:“所以说,中西各有所长,要兼容并包才是。”
趁他们说话之际,胡天福已悄悄下床,收拾行装要走。
老中医突然发现,急忙制止:“你这是干什么?”
胡天福:“马上动身!”
老中医:“不行!至少还要调养一个月。”
胡天福:“大叔,你的心我领了!可我一天也待不下去啊!”
鲁迅:“老先生,你就让他走吧。就是他不走,我也要走了。”
老中医:“你去哪儿?跟他一起去法国?”
鲁迅:“不,我去北京。”
老中医:“去北京干什么?国民政府在南京!”
鲁迅:“南京政府已经解散了。”
老中医:“什么?解散了?不像话,太不像话!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混账王八蛋!他当上大总统,孙中山在他手下,还能有好日子过?唉,革命,革命,难道就是为了剪掉一条辫子吗?这能叫革命成功吗?”
鲁迅:“至少革命成功一半吧。”
老中医:“半途而废!可惜,可惜!痛心,痛心啊!你看看,外国军舰还在长江上横行无阻,这叫什么还我中华!”
胡天福:“大叔,您别生气,也别伤心。”
老中医:“眼看革命革成这个样子,我能不生气,能不伤心吗?我们老百姓盼呀,等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今天,盼到现在,可好!除了这条辫子没有了,其他一切还是老样子。孙中山走了,你们也走了,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中国完了!……完了!……”
老中医伏案痛哭起来。鲁迅和胡天福眼圈也红了……
南京。码头。汽笛声声,鲁迅和老中医把胡天福送上轮船。
老中医把一大包中草药放进舱里:“这是止疼的,这是活血的……”
鲁迅:“我已经给张学勤发了电报。他会到码头接你的。”
胡天福:“谢谢,谢谢!”
老中医眼泪汪汪地说:“别忘了给我打个电报,只说一个平安就行,我孤身一人,无儿无女!”
胡天福紧紧抓住他的膀子:“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儿子!”
老中医:“孩子,你爹……”
胡天福:“我爹早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保定。乡村。卡佳坐在炕边,一勺一勺地给胡大娘喂小米粥。
胡大娘望着卡佳的眼睛,不停地在笑,眼睛笑成一条缝。
卡佳被她笑得不好意思起来:“妈妈,你笑什么?”
胡大娘用手摸着卡佳的头发:“你头发是用金子做的吗?”
卡佳:“不是,只是颜色像黄金。”
胡大娘:“你的眼睛怎么这么蓝,像蓝天……天……”她指着窗外的天空。
卡佳点头:“你说我的眼睛像天一样蓝,是吗?”
胡大娘点头:“像天一样。”
卡佳:“因为你的儿子就是天,我的天,我的天!……”说着,她掉过头去,泪如雨下。
胡大娘也把眼睛闭上,泪水从她的眼眶里溢出。
山本、二梅在乡村小路上奔跑着。
山本冲在前边,二梅紧追不放。
山本破门而入,喊着:“大娘!大娘!……”
胡大娘霍地坐起,卡佳也惊呆了。
二梅喘息着,举着电报:“天福!……”
卡佳一把抢过电报,可看不懂上边的字:“什么?这上边写的什么?”
山本:“他活着!活着!”
卡佳抱着山本亲吻:“啊,他活着!活着!”
胡大娘完全傻了。
二梅:“大娘,天福哥还活着!”
胡大娘:“他在哪儿?在哪儿?”
二梅:“张学勤来电报,说天福哥要到巴黎。”
卡佳:“巴黎?走,马上走!”
胡大娘:“什么巴……巴……”
二梅:“巴黎,在法国……”
胡大娘:“他怎么不回家?”
二梅:“他要到法国治腿,治好腿,就回家。”
胡大娘:“我怕……看不见他了!……”说着,她又躺了下来,昏过去了。
卡佳伏在她身上,大声喊着:“妈妈!妈妈!妈妈!……”
几个子女站在炕边,无不为之动容。
卡佳在轮船上,望着大海;依万诺夫和瓦丽亚站在不远处,向她微笑。
胡天福也在海上,只是另一艘轮船。他躺在船舱里,看着卡佳的照片。
晚。轮船休息室传出胡琴声,有人在唱《空城计》。
胡天福拄着双拐倚在休息室门边静听着。
李四光从休息室走出,惊呼:“胡大哥!请里边坐!”
他扶着胡天福走进休息室,人们鼓掌欢迎。
晚。船上。休息室。
胡天福:“唱呀!怎么不唱了?我就喜欢《空城计》。”
李四光:“各位,我们请武昌起义的英雄胡天福先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好!”大家热烈鼓掌。
琴声又起。胡天福真的唱了起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轮船饭厅里,传出《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外国男女们正在翩翩起舞。
掌声又起。
胡天福笑道:“我不是英雄,是狗熊!”
人们大笑起来。
胡天福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不瞒大家,我是带着满身伤痕,从中国逃出来的。”
众惊呼:“怎么回事?”
“有人要抓你?”
胡天福:“暂时还没有,但要不了多久,革命党人就要被抓,被杀头。”
李四光:“胡大哥,你太悲观了吧!”
胡天福:“我不悲观,只是很伤心。四光,你呢,难道你不伤心?你曾经是国民政府实业司司长,怀着满腔热血,要在孙大总统领导下,实业救国,结果又如何呢?还不是跟我一样!”
李四光:“不一样,你是革命功臣,我是一介书生。在日本留学七年,回到湖北以后,原想教育救国,不料武昌起义爆发。孙大总统认为兴办实业是‘中国存亡的关键’,定要选我为实业司司长。没想到,革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中,我不得不辞职而去。”
胡天福:“也跟我一样,漂洋过海,另谋出路。可出路何在?”
李四光:“我的出路还是读书。”
胡天福:“读书能救国?”
李四光:“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恐怕是科学与民主。”
众响应:“对!”“要想救国,唯有科学与民主!”“我们出国留学,学的也是科学与民主!”
李四光:“今年有二三百人到欧美留学。我是第二次出国留学。”
李仪祉:“我也是。”
李四光:“那我们俩命运相同啰!”
李仪祉:“我在德国留学,武昌起义爆发,震惊世界。毕业考试我都放弃了,买了手枪、子弹,匆匆赶回国,找到我们陕西老乡于右任。他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副部长,马上要我去当官。”
胡天福:“什么官?”
李仪祉:“津浦铁路局局长。我说,不行,我要回陕西,为三秦父老效力。他就叫我回老家修铁路。我兴冲冲回到家乡,可袁世凯的军队比我走得快,内战爆发,经费无着,我在德国学到的一身本领,在泱泱华夏却无用武之地,只好第二次留学。”
胡天福:“还学修铁路?”
李仪祉:“我父亲常说,立身处世的原则是:要做大事,不做大官。我这次亲眼看到陕西干旱数月,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后悔没有在德国学水利。”
李四光:“那你到德国专攻水利?”
李仪祉:“是的,兴修水利是中国一件大事,我要为此贡献一切!你呢?”
李四光:“我在日本学的是造船。这次去英国想学采矿。”
熊庆来:“我也想学采矿。”
李四光:“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才二十岁,叫熊庆来,是云南蔡锷将军派遣到欧美的十三名留学生之一。在这条船上,总共有七十八名中国留学生,分别到欧洲七个国家。伦敦快到了。在我们分别的时候,让我们同声高呼:中国万岁!”
“中国万岁”的呼声在夜空中久久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