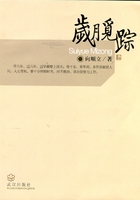1940年,新四军一来,五叔就带我去淮南津浦路东联合中学预备班,从此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在学校里,我的兴趣还是语文,十岁多就在墙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可以说,这是我文学创作的萌芽。记得,在诗的下边,我还写了几百字的说明,生怕别人看不懂似的。语文老师刘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已去世)看了哈哈大笑,说诗要别人去体会,自己不要去说明。从写诗开始,渐渐地,我的艺术细胞不断增生:唱歌、跳舞、演戏。最难忘的是,寒冬腊月,我们穿着短裤,在广场舞台上跳《铁路工人舞》《乌克兰舞》,跳完跑到台下,冻得瑟瑟发抖。邓子恢(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主任)一把将我拉住,坐在他的膝盖上,用棉大衣紧紧裹着我。好暖啊!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觉得热乎乎的。在淮南联中(方毅、张劲夫先后任校长)和“艺专”时,语文老师刘加林(原蔡畅秘书,“文革”中自杀)特别喜欢我,让我在苏联话剧《表》中演主角(偷表的男孩彼蒂加)。音乐老师孔健飞也非常器重我,又让我唱歌,又让我指挥。人们都说孔老师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何仿,一个是我。1942年秋,在八县青年运动会上,要我指挥一百多人的合唱团,可我长得又小又矮,等别人把我抱到凳子上,我这才拿起指挥棒。我连简谱都不会,更不用说五线谱了。而何仿(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确是一个音乐天才,六十年前他改编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已风靡世界。还有一位同学吕其明,也是一个音乐天才,他创作的《铁道游击队》和交响曲《红旗颂》已成了红色经典。我呢,一直爱好音乐,但只会欣赏,至今仍是“一窍不通”。就在我指挥孔老师创作的《精兵简政大合唱》之后不久,1942年底,因日本鬼子扫荡,财政困难,淮南中学停办,我们就被“精简”回家了。苦闷啊,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面临“向何处去”?在家没有饭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和牛睡在一起。一有空,我就看书,《三国》《水浒》《岳飞传》《隋唐演义》等等,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贪婪地一口气看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可是,食不果腹,饥肠辘辘,饭都没有吃的,还能读书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去当印刷工人,先是学徒,后成了师傅。1944年在《淮南日报》社,日夜加班,忘我劳动。这时,巧遇王榕(她和我姑妈一起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她时任报社通联部部长,介绍我看了许多书,尤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1945年4月,由王榕介绍,我怀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激情入了党。由于和记者、编辑、画家在一起,萌生了学新闻、当记者的强烈愿望。1946年春,一位工人画家和一个女大学生记者结婚,我觉得这事很新鲜,于是在《淮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可以说,这是我新闻写作的萌芽。不久,内战爆发,我们“北撤”到山东,在“华东军政大学”正式参军,穿上了新四军的草绿色军装。此时,我的梦想是当范长江那样的战地记者。不料,组织上要我去“延安大学”新闻系学习,我当然喜出望外。步行三千里,走了三个月,穿过三道封锁线,好不容易到了延安,可“延大”已转移到后方。中央组织部问我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到新华社吧!”在清凉山的窑洞里,两个多月就挨了敌机十几次轰炸。一天深夜,我们最后一批撤出延安,翻山越岭,走了几天,最后才知道要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范长江带领新华社二十多人,通过电台收听外国通讯社新闻,又向全国发布消息。我的任务是刻蜡纸,油印出版《参考消息》和《新闻简报》,每天送毛主席和中央纵队各单位阅读。凡是经新华社发出的稿件,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起草或修改的文章、评论、新闻原稿,都由我最后保存,直到1949年3月进北京才全部交出来,存进了中央档案馆。从文书、校对到秘书,两年多的时光使我学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可是,我毕竟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一下子就出国留洋,到了莫斯科大学。开始,上课听不懂,人家笑,跟着笑,却不知笑什么。下了课,苏联同学“一帮一”地帮我们补习,白天、晚上、夜里,几乎天天在啃书本。有人病了,有人垮了。一年学下来,头昏脑涨,疲惫不堪,十几门功课考试,虽然都得了五分,但究竟有多少收获呢?死记、硬背,教条式,填鸭式的教育,迫使我寻求出路。从小就很调皮的我忽然冒出了一个“鬼点子”,并大胆地提出:不上课!把上课的时间节省下来,一是自修,二是去报社实习。这一招,果然很灵,在苏联报社当记者,又采访,又写稿,回校再按老师的要求准备考试,不仅各门功课得五分,而且俄语水平、知识水平、写作水平迅速提高,新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了可以独立作战的记者,这真是事半功倍啊!在莫斯科大学五年,我几乎跑遍了苏联,为国内十几家报刊写稿。我不但用俄文写稿,甚至用俄文思考问题。一有空,就去看电影,使我大受其益。记得,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时,代表团晚上看电影,正好我在克里姆林宫,要我坐在宋庆龄和邓小平旁边当翻译。《静静的顿河》有很多土语,我边看边小声翻译,有一句话是“在……里”,我译成“在手套里革命”,邓小平哼了一声,我马上觉察译错了,改口说“戴着手套革命”,他点了点头。这一刹那,我记忆犹新。我在实践中认识到,学新闻、当记者,决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一定要多看、多想、多写,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写得越多,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很惭愧,我虽然被评为“高级记者”,但至今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为什么?因为“新闻”二字对我仍然陌生。从十岁多写了第一首诗开始,我的形象思维就越来越发达。在莫斯科,我写的几乎全是通讯,或者称报告文学。后来,在《中国青年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当记者,新闻也写得极少,不是我学不会,而是没有用心去学。这一点,我不如李克。文如其人,他说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他写的新闻简洁,通讯也很凝练。必须承认,我是记者,但不是“新闻记者”。不写或不会写新闻,怎么能叫“新闻记者”呢?早在1954年,当我第一次发现莫斯科有山东老人时,我就感到非常新奇。新闻敏感有,但没有写新闻,而是紧紧跟踪俄国华工,深入采访,写了好几篇通讯,介绍他们参加十月革命的故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无产者》。可以说,我是从记者过渡到作家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够格的,因为我的作品的风格,一看就知道带一点洋味,缺乏“中国气派”。我们这一代人在苏联文学特别是苏联电影的熏陶下长大,著名的战地记者兼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波列伏伊等人是我学习的榜样。可我是中国人,我的作品必须深深扎根在中国的民族的土壤上。当然,在创作上,我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一句话:我就是我。我从不去模仿别人,从“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焦裕禄),而要走自己的路。尽管如此,我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中国作家”,我是不完全的;正如作为“新闻记者”,我也是不完全的一样。除了客观(我的工作、经历、环境等),主观上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我的古文底子太薄,妨碍了我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如果我能像我的爷爷那样熟读四书、五经,刻苦学习古代诗词,把如此丰富、生动、精练、深刻、奇妙的汉语融会贯通,运用自如,那么,我的作品可能就会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了。从1946年在《淮南日报》发表我的第一篇稿子(至今还未找到)以来,过去了将近六十年,已经发表的文艺和新闻作品大概有几百万字,没有发表的作品还有不少。我对自己已经发表和没有发表的作品都很不满意,总感到有缺陷、有毛病,可我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反思、认真地总结一下。看了徐怀中老师(我称呼他“老师”完全出于一片赤诚)的信,我不只一次下决心“闭门思过”,找出写作上的“某些不足”及其原因。这次,就算是一个开头吧。希望更多的读者成为我的老师,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和指教。这不是客套,而是由衷之言。凡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怕批评、欢迎指教的人。尽管我已七十七岁高龄,但我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读书、看报,从不间断,每天都有收获。“学而后知不足。”越学习越感到,我这个在文学上还没有毕业的小学生,迫切地需要补课、学习、提高。这一点“自知之明”,始终像一根鞭子,抽打着我这条“老牛”,不停地向前;又像一缕阳光和一股清泉,温暖和滋润着我,使我这棵“老苗”常青。
回首往事,我又想起两个朋友,一是赵棣生,二是刘祖禹。小赵比我大七岁,直到他去世,新华社老人都叫他“小赵”。转战陕北时,我们在一个班。班长胡韦德(国际编辑),对我要求很严,几乎每次开会都批评我,说我夜行军休息时一躺到地上就睡,要受凉生病;或者边走边睡,要摔到山沟里。小赵总是护着我说:“小鬼太累了!”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经常夜里行军,白天伏在炕头刻蜡纸,还要校对、油印,实在忙不过来,小赵就主动帮我。他是国内稿件编辑,写得一手好字,我们俩共同刻写的《新闻简报》刊有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曾经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展台上。同睡一个炕的战友,那真是同志加兄弟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亲如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每次见面,他都毫不客气,对我各方面(包括工作、生活、创作等等)提出各种批评意见,总爱说:“不挨骂,长不大!”他越是骂我,我越是高兴!最后一次,他严厉地说:“小鬼呀,你不能再拼命了。要注意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去世前对我的诤言。他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骂了!……我多么想有这么一个老大哥骂我啊!幸好,刘祖禹还健在,他比我小两岁,但比我成熟很多。从1958年在《中国青年报》相识至今,特别是在“文革”以后,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其特点除了无话不谈,就是他经常“骂”我。我呢,一遇到“疑难杂症”,或者要作出重大决策时,必定要去找他,当面向他求教。他也像小赵一样,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毛病,给我以忠告。他正直无私,洞察力极强,往往一针见血。小赵看了剧本,在上边批注意见;刘祖禹不仅看剧本,而且还不断地帮我联系各方,出谋划策。对我的缺点,他最了解,批评也最尖锐。可以说,他是我的“诤友”,几乎是唯一的“诤友”了。我珍惜,我自豪!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如此,党也如此。人会犯错误,党也会犯错误。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要改,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中吸取氧气,逐步地健康成长起来的。1945年和1981年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就是共产党人勇于并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胡锦涛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之后第一站就到了西柏坡,重温毛主席“两个务必”和“三大作风”的教导,接着又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全党同志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扫帚”,扫掉我们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可是,不少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错误的态度,有的避重就轻,敷衍了事;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怀恨在心,打击报复。“三讲”也好,“保持先进性教育”也好,他们都顺利“过关”,甚至官越做越大,私心也越来越膨胀,大搞歪门邪道,以致走上犯罪的道路。200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近日痛批“小人得志,好人受气”的庸俗作风。他指出:庸俗作风是通向腐败的引桥。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从行为的庸俗化开始的。目前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中,有极少数人热衷于旧社会官场上的一套,有的到处找“靠山”,搞小团体;有的为了个人的升迁,搞五花八门的关系投入;有的散布流言蜚语,传播小道消息;更有甚者,玩弄阴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面对这些歪风邪气,有的同志却奉行好人主义,以不得罪人为最佳取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庸俗作风。庸俗作风的滋生蔓延必然造成歪风邪气上升,小人得志,好人受气,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看到这里,我的心激动得发抖,又一次想呼天唤地:天啊,太好了!太痛快了!“小人得志,好人受气”,实在太可怕了!太危险了!我身不由己,马上拿起笔来给白克明同志写了一封信:
克明同志:
您好!看到《报刊文摘》上,您痛批“小人得志,好人受气”庸俗作风一文,特向您欢呼致敬!您讲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发出了“正义的怒吼”!
……
紧接着,我联系实际讲了一些“家丑”。这些“家丑”,本来“不可”也决不想“外扬”,关起门来解决为好。可是,面对如此顽强的阻力,要想办成一件事,非冲破常规公开揭露不可。经常听人说:“做人难,做好人更难。”难在哪里?我看,难就难在一个“私”字。“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事业、理想、主义,扯淡!”“一切为了钱,有钱就有一切!”君不见,这样的“小人”到处都有,这样的“小人之心”,不是比比皆是么?“好事”遇到他,自然就办成了“坏事”;“好人”遇到他,自然也变成了“坏人”,那么,你还想做什么“好事”、做什么“好人”呢?或者,你就“退避三舍”、“惹不起,也躲得起”,甚至看破“红尘”,“难得糊涂”吧;或者,你就挺身而出,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怕一切,不顾一切,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坦诚地、尖锐地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结果呢,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挨了整,甚至含冤而死。这样惨痛的教训还少吗?所以,有人劝我:“批评建议,人家听了不高兴,事情办不成,还要给你‘穿小鞋’,何必自讨苦吃呢?”又有人劝我:“批评多了,影响团结,算了吧!”
听到这些好心人的劝告,我不想“辩护”,更不想反驳,只有苦笑,只有仰天长啸:天啊,老祖宗的教导难道都忘了吗?我这个“天天学”的老古董,又一次打开了领袖们的《选集》,现摘抄如下——
恩格斯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相互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
列宁说,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列宁又说,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一次又一次地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