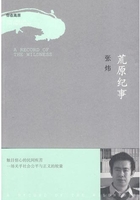最后,邓浩还是把张树平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刘子夕陪着汪静路去了。张树平坐在被告席上,看着一个很空的地方,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汪静路坐在原告席上一直看着他的侧面,该原告陈词的时候,她开口说话了:“我们白天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吃了晚饭,还喝了一瓶酒,他喝了,我也喝了。然后,然后我上了他的车,他送我回去,后来走到江边时,我借故让他把车停下。再然后,我引诱了他,借着酒精我引诱他和我做爱,接着,我们就在车里做爱。我是心甘情愿地和他发生了性关系。”
庭下鸦雀无声。
张树平夹在人群里走出了法庭,外面阳光很好,好像好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阳光了。他夹在人群里感觉自己仿佛不是阳间的,别人看不到他,也挨不到他,他从别人的身体中间穿过去了,别人也感觉不到。他木木地、飘飘地走出很长一段路了,猛然才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一回头,在他身后几米远的地方站着汪静路。
她静静地在那里笑着,看着他。
汪静路要搬走的那天又是个周末,梁惠敏不在,刘子夕帮着她收拾东西。楼下,张树平的车正等在那里。她已经和邓浩正式提出了分手,选择了张树平。她告诉刘子夕要搬走的时候,忽然流泪了,她说:“我无法和你解释的,因为你不会懂。”
刘子夕笑着说:“你不用说,我都知道的,其实,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汪静路泪流满面,伸手抱住了刘子夕,她说:“我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你。”
刘子夕说:“我们不是都认识半年多了吗?”
汪静路说:“可是那个时候,人在对面犹不识。”
刘子夕说:“没事的,有了男人以后也可以来这里玩啊!不能有了男人就把姐妹忘了。”
两个人伤感了一番,最后汪静路还是走了,她拿走了很少的东西,把能留下的全留给了刘子夕,她说:“你一个单身肯定用得着。”
刘子夕开玩笑:“你本来不过是打算在这个城市过渡几年的,没想到却嫁到这里来了。”
汪静路也笑:“是啊!人生真是无常,你怎么能想得到下一步你会怎么走。”
刘子夕说:“快走吧,快走吧!人家都在下面等急了。”
汪静路说:“没事,他脾气好。”
可终究还是走了。
刘子夕在门口目送她,一直到看不见她的影子了才关上门,一时竟伤感得不行。其实在这些合租的女友里,和汪静路算是交情最浅的,她只不过住了半年,若不是她临走前突然对她掏心掏肺地倾诉一番,也许,她们是到死都不会说话的了。可是,她们还是在分开前留恋了对方一番,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她也确实明白汪静路最后的选择,她真的懂她,看着她,就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只是,已经迟了。送走汪静路,感觉就像嫁出去了一个自家的姐妹,屋里倍感空旷寂寥,有些曲终人散的味道。
汪静路搬走后的这个春天,刘子夕和梁惠敏再次商量着要不要再找个女孩子住进来分担点房租。这时,房东又加了房租,两个女人自然是要抗议的:“凭什么搬走一个人了还要给我们加房租,看我们有钱还是怎么着的?”
房东冷笑:“不愿加钱就搬走啊!”
两个女人一赌气:“谁怕谁啊?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的房子要出租?我们还不想住了呢,就像住在足球场里一样,一点人味都没有,互相串个门都要走好几分钟的路,浪费姑娘的体力。”两个人便商量了一下,决定这次在网上拼个房子。
这是刘子夕第三次搬家了,反正不是第一次了,后面再多几次也无所谓了。刘子夕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这也是好事。房东限她们一个星期内搬走,刘子夕便匆忙找好了另一处房子,付了半年的定金。结果就在她们往外搬的同一天,她们的东西还没搬出去呢,人家要住进来的人已经等在楼下了,她们下楼人家上楼,简直是连一分钟都等不了。原来是小气的房东已经事先把房子租给了另一个愿意出钱的男人,怪不得那么拽呢。其实是变着法把她们往外赶,又不好明说是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要租下来。不仗义的房东。
两个人一边满头大汗灰头土脸地搬东西,同时想起了袁小玉。人家真是聪明绝顶啊,说不再搬家就不再搬家了,就她们两个傻子还这样一次次搬家,不知道要一直搬到猴年马月去,搬来搬去也没见她们落到比袁小玉更好的下场。不管人家嫁的是阿猫阿狗,总归是有个房子住了,就是蜗牛都有自己的房子住,她们连蜗牛也不如。
这次搬家和上次搬家的心境大不相同,上次是急于想躲开杜明明那屋子的,是连那屋子里的气息都闻不得的,是焦躁夹杂着悲伤和赌气的。这次是被迫的搬家,又受了房东的欺负,是气愤夹杂着无奈和落魄的。不管怎样,两个人只好再度迁徙,搬着大大小小的东西住进了一套两室一厅。每搬一次家东西就要多一次,就像松鼠储备过冬的食物一样,一点一滴地衔回自己的窝里,哪样看着都舍不得扔掉,只好统统搬走,其实也没一件是值钱的。
刘子夕的书多了点,搬家工人要求加钱,刘子夕看着这些纯靠力气吃饭的人们也觉得人家着实不容易,从那个六楼搬到这个四楼,容易吗?便多付了些钱。事后梁惠敏对刘子夕说:“你怎么多给他们钱呢?他们这是看你好说话讹你呢。”刘子夕没说话,想这女人也真是忒会算计了,好像对全天下都防备着一般。
她们搬去的那套屋子里的另一个房间已经住了两个女人。房子是刘子夕提前考察过的,旧是旧了点,但毕竟是市中心的房子,一出门什么都有。那一间房里有两张床,住着两个女人,像间大学宿舍。另一间只有一张床,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就是这样,因为时间紧迫,刘子夕还是咬着牙把那间房租了下来。二线城市里一千六的房租轮到四个人头上,每人只交四百,多省钱。
搬家那天是星期天,搬过去时那间屋里的另外两个女人都在,没上班。见她们往里搬,就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房门掩上了。然后两个女人就在那扇白色的门后无声无息着,没有一点要出来帮忙的意思。刘子夕和梁惠敏一边站在门口看着搬家公司的工人往里搬东西,一边气愤着:“这么冷漠?拽什么拽,都三十岁的老女人了,还挤在这么破的房子里不往外嫁,第一次搬过来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好像欠了她们多少钱似的。”因为交房租的时候要看身份证,刘子夕便知道对门这两个女人都是三十岁的单身女人。刘子夕和梁惠敏二十九,但毕竟,她们还在二开头的范围里打转。对女人来说,一岁之差就已经是天高水远了。她们可是上了三十的女人,以三打头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刘子夕想:住到这儿也好,每天看着两个三十岁的单身女人,自己总会心情舒畅一点,看吧,都三十岁了还没嫁出去。
那两个女人一个叫尤加燕,一个叫李凤,是大学同学,又在一个单位上班,简直好得交头换骨。一天晚上,刘子夕洗衣服时听见尤加燕在屋里对李凤说:“凤凤,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话的上面是不讲理的娇痴,下面却是深不见底的怨恨。正在洗衣服的刘子夕听着听着突然一阵心酸,这三十岁未嫁的女人也许都是和自己一样,从男人堆里一路厮杀过来,翻山越岭,越是苍茫越是虚弱看起来反而越是坚硬。到了一定年龄的单身女人,出于对岁月抵抗的本能,每个人都像吃多了防腐剂,竭力把自己的脸保存成了三十岁以内的标本,脸的下面,身体里却似雪崩一样无声无息的坍塌侵蚀的过程。虽然幸灾乐祸她们已经三十了,其实二十九岁的自己和她们又有什么不同?一岁之差,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却如此遥不可及,还相互残杀。
然而刘子夕这种独自的心酸并没有抵得住那两个女人对她们的不友好。她们在这房子里已经住了五年了,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久了简直也算得上是一种资历,女人无论有什么样的资历都会跋扈起来。除了她们那间卧室,客厅里、厨房里、卫生间里,到处充斥着她们琐碎的东西,像一层皮肤一样包裹着这破旧的两室一厅。要是不小心碰破了这层皮,流出了里面的血那就麻烦了,她们给她们摆脸色看,象征性地摔东西,以示警告:“我们的东西你们以后别碰。”为了避免碰她们的东西,刘子夕和梁惠敏从来不进厨房,一向在外面吃了饭再回来。虽说是四个人合租的房子,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本是公用的,可事实上,她们却觉得自己被逼进了那间小卧室,住在这屋子里简直像两个受气的小妾。
交的房租一样却还要受这种气,梁惠敏极力劝刘子夕不要和她们吵得不可收拾,却也是为她自己盘算。早在她们住那套三室一厅的时候,她弟弟就经常去找她,有时候不还在她们客厅的那张旧沙发上过夜嘛。虽说换了地方,其他还是按部就班,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她弟弟还是一定会来找她,还是免不了要过夜的。这里的客厅里也摆着一张旧沙发,不过是对面那两个女人的,要是和她们吵翻了,那就连睡睡这张旧沙发都开不了口了,后路全被截断了。
两个女人原先好歹也是一人一间屋子的,现在倒好,跑到一个屋子还不算,还跑到一张床上去了。刘子夕租这样的房子梁惠敏也没有反对,可见她也是心疼房租,如果愿意多出房租的话哪还用搬家啊。两个人在住进来之前其实也就是一碗汤的交情,只是这次搬家房东把两个人往外赶,使她们突然之间前所未有地团结了起来,并且顿生惺惺相惜之情。一方面是袁小玉嫁人了,抛下了她们两个单身;另一方面,两个人都是没房子住的人,又被赶了出来,都有些落魄的感觉。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下,两个人觉得靠在一起还是多少有些暖意的,就又住到了一起,就像一对旧式的夫妻,结了婚才开始了解对方。
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免不了要说话的,聊了几次后刘子夕才开始知道,梁惠敏和她弟弟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梁惠敏说她父母离了婚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父亲。母亲单位效益不好,早早办了内退,所以她弟弟读大学的学费基本上是她负担下来的。她弟弟大四考研没考上,毕业后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工作也不找,专职考研。梁惠敏自己没读研,所以极力支持弟弟,她每月工资的一大半都给了她弟弟,让他专心考研,结果她弟弟一考就考了两年。两年没有找工作,一直复习考研,隔一段时间就从郊区的学校赶过来向她要钱,因为赶不上车就要在他姐姐这里住一晚。原来刚一搬进来的时候梁惠敏就已经觊觎客厅里那张旧沙发了,所以她不能和对面的两个女人搞得太僵,不然她弟弟来了连个住处都没有。她弟弟是一定要来找她的,他怎么会不来?难怪她不愿多提及自己那个弟弟,原来,她是那个男人软体动物上的那层壳,她是空的、硬的,他就住在她的身体里。这也是个不容易的女人了,难怪那么会算计,什么本事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呢?要是有钱,谁都会让自己看起来又优雅又有教养,那点东西还不就是用钱砸出来的。
晚上两个女人就睡在那一张大床上,双人床上铺着两条花色不同的床单,像象棋棋盘上的楚河分界,两个人各自小心翼翼占领着自己半张床的地盘。第一天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刘子夕忍不住地凄惶,真是越活越悲怆,以前还起码是一间屋的地盘,现在倒好,只有半张床的地盘了。一张床上,身边睡的不是男人而是个女人感觉竟这么怪异,只想离旁边这个身体远些再远些,仿佛不小心碰到女人的身体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她想,一个女人闻到另一个女人身体上的气息的时候,会觉得身边的只是一堆带着温度的肉,底下是没有内容的,空空洞洞的一具身体,这感觉竟是有些恐怖的。更何况,身边的女人对自己来说既不是亲人也够不上闺密的级别,和这样一个半生不熟的女人竟睡在了一张床上,还真是得有些勇气的。梁惠敏大概也有同感,在自己的半张床上如烤饼一般翻过来翻过去。
这天不知道是夜里几点了,竟是满月,就在当空,月光照在半透明的纱窗上,被筛得千疮百孔,然后像雪花一样落在了她们的被子上、脸上。月光的寒凉让她们在一瞬间觉得自己像河底的石子,白天所有唧唧喳喳的浮在空中的愉悦突然停止了,一瞬间是苍凉的安静,那么深那么苍凉的安静。两个人看着月光的眼睛都有些潮湿起来,似乎与岁月深处那些最深最暗的东西迎面遇上了,清晰、残酷而荒凉。两个人都觉得在这月光下有些溺水的感觉,也是在那一瞬间,她们知道她们之间终于有了一点通道了,借着这一点通道,她们即使举着蜡烛也可以从这个身体到达那个身体里。
刘子夕先说话了:“就是早两年我都没有觉得有个房子是这样的重要,可是现在我想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不用再这么搬来搬去地租房子,看人眼色。”
梁惠敏说:“还是找男人吧!靠我们自己再过几十年都不知道。”
刘子夕说:“你说对面那两个比咱们还大,也不着急?”
女人总是喜欢用议论别的女人来转嫁自己的疼痛。
梁惠敏说:“她们好像都有男朋友呢,只是还没有结婚。我昨天下午回来得早了点,回来了对面暗着灯,我还以为里面没有人呢。忽然听见里面有女人说话,好像在吵架的样子,我听见她说:‘我跟着你几年了,我现在都三十岁的人了,落得一身是病,你还要我怎么样?’那男人静悄悄的,不说一句话,就只是那女人自己在黑屋子里唱独角戏,看来也不一定比咱们过得好。另一个好像已经快结婚了,好像找了个什么电视台的记者。”
刘子夕暗想:一身是病?那么凶悍跋扈的女人竟会一身是病?又想,搬进来这么长时间,她对对面房间里那两个女人都一无所知,梁惠敏却已经知道这么多,她和自己住了一年多又何曾试图了解过自己的什么。要不是因为袁小玉,她们也许至今都不会说一句话呢。不了解自己大约是因为对自己无所企图吧,那她对对面两个女人又有什么企图?讨好她们?和她们搞好关系?那自己呢?竟让人对自己连一点企图都没有?寒僻到这种地步的女人难怪没有男人,可是自己也不能一直就这样没有男人过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