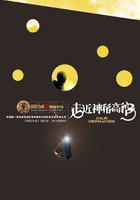他们在宾馆二楼咖啡厅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咖啡厅里坐着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女在低声聊天喝咖啡。音乐像水一样流淌着,服务生踩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马上被吸没了。角落里的灯光很暗,刘子夕仍然看不清他的脸,她有些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有意思,他们怎么会隔着半个地球相识呢?她以为他永远也不过是个幻象,但是他现在却真的就在她身边。他也不说话,无声地喝着咖啡,后来他问:“累了吧?”她点点头。他说:“去休息吧!”他们走了出去,来到前台,开好房间,他只开了一间,然后他们就进了那个房间。她只开了朦胧的壁灯,说:“我先去冲个澡。”她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匆忙躲进了卫生间。
出来时博士和衣躺在床上正看电视,她问了句:“你睡哪张床?”问完之后自己都觉得好笑,她就不再说话了,便坐到了床上看电视。博士进了卫生间,出来时只穿了条内裤。她努力不去往他身上看,努力地看着电视。但是,他坐到了她身边,他身上还带着水珠,他不说话,把一只手环在了她的腰间,再然后抱住了她。她没有挣扎,眼睛却还是看着电视的屏幕,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后来,他把她放在了床上,她看不到电视了,却仍然无比清晰地听着电视里的声音。他开始吻她,开始动手脱她身上的衣服。她极其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他一点点向下吻着,最后他试图进入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等待着。他在那儿动作了半天之后却颓然从她身体上滑了下去。他不动了,像一个被刚救上岸的溺水的人,一团湿漉漉的柔软。她睁开了眼睛:“你怎么了?”
他不说话。
她突然有些紧张起来:“你……”
“对不起。”
“你,一直就这样?”
“有几年了。”
“你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成这样,可能是我年轻求学那时候晚上总喜欢用手……我也看过医生,可是一直没什么效果。”
“那你为什么还说要结婚?”她听到自己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了,像一块布被撕裂的声音,有些恐怖。
“因为我需要一个归宿。”他说得有气无力,却是无比清晰。
“归宿?”是啊,他有什么错,她要的不也是一个归宿吗?可是,就是这样的归宿吗?他们谁在收留谁?
她侥幸地以为他能给她点什么,原来,对这个世界抱一次侥幸就要受一次惩罚。
他还在说,语气飞快而急促地说:“我可以很快给你办到绿卡,你可以不用上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那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想结婚也是真的。”
是的,这是一个真的想结婚的男人,而她也是一个真想结婚的女人。那么,就应该嫁给他吗?她怔怔地看着他,看得他有些害怕了,他黯然说:“当然,你可以自己考虑。”
杜明明听完刘子夕的倾诉之后,问了一句:“那你打算怎么样?”刘子夕说:“不怎么样,我不能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
两天后的晚上,杜明明突然对她说:“刘子夕,我们谈谈,好吗?”
刘子夕有些奇怪地紧张,她努力平静地说:“你说。”
杜明明不看她,说:“你已经想好了,不和博士结婚是吗?”
“是。”
“那……如果我和他结婚,你觉得有没有伤害你?”
……
“你知道的,我想结婚了,真的……”
“你们已经谈好了?”她突然觉得自己这句话有些讽刺。
“我找他谈了,说实话,他也不是爱你,他只是需要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去照顾他的生活,其实是个女人就可以做到……而我只是需要一个家。”
“你知道他有……病吗?”
“他和我说了。”
……
“那又怎么样?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结婚的男人,上床不上床我已经无所谓了,那有多少意思。再说了,也不一定治不好。”
“想好了?”
“是的。”
“什么时候和他走?”
“我会先和他过去,等到绿卡办下来再说别的。”
……
“刘子夕,我这样做有没有伤害你?”
突然,刘子夕声嘶力竭地说了句:“你走开。”
杜明明向外走去,突然又回头说:“我和石杨在一起已经两年了,还差一年就满三年了,本来我们签了合同的,满三年了房子就签到我名下了,可是还是前功尽弃了,我等不了了。你就先住着吧,要不你再找个女孩一起住,一个人太孤单了。”
孤单?
第二天趁刘子夕上班的时候,杜明明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收拾走了,那间屋子突然就空了,好像从没有人住过一样。杜明明在去美国之前给刘子夕打了一次电话,她说:“对不起,刘子夕,不要记恨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一去,去的是天堂还是地狱,也说不准哪天就又回来了,你自己要好好的。”又是这句“你要好好的”就像一句仪式性的道别,此后就是天各一方了。刘子夕只是听着,一句话都不说。
杜明明和博士如期走了,刘子夕没去送他们。
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子夕就从杜明明的那套房子里搬出来,把房子给石杨留下了,她重新找了一处房子。因为她的高中同学袁小玉从深圳回来了,要找个房子住,却是人生地不熟的。正好刘子夕急于从杜明明那套房子里搬出去,她不想每天和杜明明的影子住在一起,还时不时得见石杨的面,那个男人一直让她觉得有些恐惧。现在正好和袁小玉搭个伴,更何况,在哪儿还不都是租房。
最后找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有些大,但家里的家具和电器都很齐全,房子也是新的,因为离市中心比较远,所以房租倒也不贵。袁小玉说:“就这套吧!我再把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叫上,她也是一个人住,也没有男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住就划算了。”
不过当三个人真的搬进这三室一厅的房子时,还是大大惊讶了一番客厅的空旷浩大。这屋子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三间卧室一间比一间小,唯独客厅大得可以当足球场,加上租来的房子本身就没摆多少家具,所以即使在白天,走在客厅里都能听到自己脚步悠远清冷的回声,像广寒宫似的。地上铺的是白色的瓷砖,走在上面都能看到人影,就像走在一片浩大无边的水面上,一低头,自己清冽的倒影已触手可及,似乎伸手就能把自己捞出来。
三个女人下了班各回各的屋,偶尔也串串门,但也没有搬进来之前想象的那样,会不会像学生时代那样挤到一张床上去。串门的时候也是单向的,刘子夕只去袁小玉屋里,而另一个女孩子叫梁惠敏,因为不熟,她们俩见了面也就点个头。袁小玉则有时候去刘子夕屋里,有时候去梁惠敏屋里,就像两个圈总算在这里有了一点交集,但她断不会把两个人同时都叫到自己屋里来。
刘子夕细想了想,其实她和袁小玉已经十来年没见过面了,虽然高中关系还算不错,但自从各自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只听说她大学一毕业就到深圳闯荡去了,没想到时隔多年居然又在另一座城市里遇到了,而且还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并且都是单身,细想想,真像个笑话,简直有些嘲弄她们的意思。这么多年的空隙也不是白长的,它像一堵墙一样横在她们中间,使她们觉得对方都有些看不清了,再加上杜明明留给刘子夕的前车之鉴,对住在一起的女人是万不能掉以轻心的。尤其是那个陌生的梁惠敏,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高级白领,还和她们合租在这房子里,真是令人心酸。就像一个穿着旗袍、气质高雅、全身流光溢彩的女人跟着人群挤上了公交车一样令人难过。
那梁惠敏对她也不见得有多少兴趣,不冷不热,勉强打个招呼就算不错了。三个人对彼此其实都有些暗暗的警惕。于是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稀薄中带着一点风雨飘摇,似乎随时会蒸发掉。大多数时间里,三个人回家后都自觉往自己的房间里钻,就像珊瑚虫进了自己的巢穴。客厅的灯永远暗着,只有三间卧室的门缝里挤出了丝丝缕缕的光线,如围在各自门口的栅栏,到了晚上这整座屋子就像沉在海底了,如海底的珊瑚。
有一天晚上,刘子夕上卫生间的时候忽然发现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一个年轻男人,她吓得立刻就尖叫起来,以为是强盗或小偷在她们家里搭了根据地了。待两个女人都出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梁惠敏的弟弟,就在这座城市里上大学,这是周末过来找他姐姐的,那学校在郊区,晚一点就没有车了,所以就住在了她们的客厅里。原来是这样,反正那沙发平时也是空着的,由他睡去吧!
有一段时间梁惠敏出差了,屋里只剩下了刘子夕和袁小玉。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见了只互相打个招呼,就像海面上的两只船好不容易遥遥相望了,却还是擦肩而过,更添了些隔世的渺茫。刘子夕切好了一只菠萝,本想给袁小玉送过去一些的,看她这样不冷不热,便赌气回了自己屋里,一口气全把那只菠萝吃完了,带着些惩罚的意思,惩罚自己也惩罚袁小玉。
又过了两天,梁惠敏还没有回来,虽说平时并不说话,可是少了个人还是感觉到屋子里更清冷了,就像一个人突然少了件什么器官。这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刘子夕的门,她一惊,这屋里只有袁小玉了,总不会是什么别的魂魄。她开了门,果然是袁小玉,袁小玉倚着门框站在那里,像是要把自己镶嵌在那扇门里,她说:“我可以进去和你聊会儿不?”
刘子夕虽然觉得很意外,嘴上却说:“你怎么了?”
她说:“我今天心情很不好,需要和人说说话,再不找人说说话我怕自己会得抑郁症。”
刘子夕便没有再说什么,一边让她进来一边却暗想: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能想起我?当我是什么?
刘子夕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袁小玉往桌子前的椅子上一坐,正好背着灯光,刘子夕便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她周身长出的一圈毛茸茸的光晕,她整个人像一枚核一样被包在那毛茸茸的晕里了,这样使她看起来很遥远很遥远,就像是长在一棵高高的树上一样。她正不知道该说什么,袁小玉先开口了,她说:“我从深圳回来以后,我们还没怎么好好聊过呢,一直想着找个时间好好和你聊聊,一直也没心情说那些往事,根本不想提的,可是今天忽然就想和你说说话。上学的时候你就是班上的才女,那么多男生暗中注意你,怎么都到现在了你还没个男朋友?”
刘子夕听着这话心里舒坦了一点,却低着头说:“你不也没有吗?”
袁小玉停了几秒钟才说:“以前真的是一直都不想说的,因为觉得有些不堪回首。今天晚上忽然觉得很崩溃,真是不能细想。你说,我们都二十八岁了,眼看着一年年老去,还什么都没有,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也没有男朋友,你就没有恐惧感吗?我都不能细想的,一想就觉得害怕。刚到深圳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打拼,住在租来的城中村的房子里,就是那种传说中的招手楼你知道吧?在这座楼的窗口就可以和站在对面窗口里的人握住手,房间里终年不见一点阳光,阴暗潮湿得像地窖。那时候就那样我都没觉得什么,因为那时年轻,真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觉得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可是六七年时间过去了,我居然还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居然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改变。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无论你怎样生活都可以被原谅,因为你还没有开始,可是在你快三十岁的时候还是这样生活就不能被原谅了,那就说明你无能。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对自己说的,我下不了手,我对自己下不了手。今天我就是想当着你的面把这些伤疤挑开,不这样我就还会替自己遮着掩着,还会继续骗自己,还会掩耳盗铃下去。”
刘子夕想起袁小玉搬家的那天只拎着一只皮箱,那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当时觉得有些奇怪,一个女人只拎着一只皮箱搬家给人一种很凄凉寒碜的感觉,只是没好意思细问。这年头谁不是有一堆一堆的隐私,问不对地方还要得罪人,真是划不来。今天晚上看袁小玉这番情形,确实是有话要对她说的,那她就顺水推舟,不然让袁小玉觉得我都对你投怀送抱了,你还这样对我,也是伤人的心,到底也是同学一场。她便问:“你在深圳不是待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