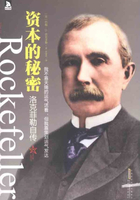我住进了这间空中楼阁,登上梯子的一瞬,我彻悟般认为这梯子是爸爸的手,是爸爸托举着我,将我一步步送向这间半空里的小屋。
爸爸说“事情须慢慢来”,难道爸爸知道我要做什么吗?可是我要做什么呢?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啊。爸爸的态度太令我困惑了,从一开始,爸爸就像是在等候我的决定,并暗示我做出这个决定。就是爸爸那句“黑鬼仿佛催促你去做一件事情”给了我启发。原本,我并未这样思考问题,是爸爸这句话给了我暗示,从而带引我步入今天这一步。不仅如此,在我下定决心后,爸爸似乎比我更加着急,加班加点工作,仿佛迫不及待。
“难道爸爸与黑鬼合谋着什么吗?黑鬼在爸爸刨木头时总是很欢乐的样子。难道爸爸要推开我吗?”住进空中楼阁的第一天,我为此苦苦挣扎了整个夜晚。
□□最初,我十分难过,想到爸爸或许在计划着抛弃我,内心即刻被一种孤独感攫获,身体便止不住颤抖起来。晚风轻拂,夜幕缀满星辰,月光透过黑黢黢的树梢,轻纱般飘浮在我的窗前,树林里的小动物们已入梦乡,偶尔发出甜美的梦呓,唯有我,置身在这安谧之外,俨然落入一个险恶的境地。
“我所能倚赖的,只是这两棵枯死的柏树了。”
“像是只身在天边,所有的人都转身而去了。”
“这难道不是我自愿的吗?”
夜渐深,大脑却越发清醒了,思绪仿若晚风,连贯而轻稳,徐徐滑过我的脑际。没有任何事物干扰我,时光纤细起来,每一缕都好像明亮了许多。我回过头审视自己的所为与所想,连同爸爸这些年里的变化,很快恍然悟出,爸爸确是有意将我推向一个方向的,他显然已经到达了那里,而后回过头来,暗暗引导着我。但爸爸似乎在他到过的那个地方没呆多久就回来了,不仅如此,回来之后的爸爸,已经带着满心酸楚,以及苍老的面容。
“这夜晚只是开始,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与今后的时光相比,都可算做不存在的。”这念头闪来,我的身体即刻停止了颤抖,血流猛然加速,片刻,脖劲间便微微沁出了汗。这念头令我激越难安,似乎从前的犹豫与烦恼因此而真相大白了。爸爸原来是很有野心的一个人,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希望生命从我这里得到续延。看得出,爸爸把我推入这个境地,是经过万般犹豫的,他细细观察我,小心试探我,或许曾经失望过,甚至还否定过自己,譬如他说我或许应该随渠三到林子外去,但是结果却是我在懵懂中留了下来,并顺从了一个冥冥中的安排。
“爸爸在梦里都会笑出声吧。”
思绪像静静燃烧的火焰,莫名中被一根铁杵拨动,霎时火星飞溅、浓烟翻滚,引来一阵喧动。我的脑袋就要炸开了,不断闯入新的念头,闪过新的思绪。
“天上的星星都往我脑壳里钻呢。”有一刻,我几乎怀疑自己的大脑被星子塞得满满当当,像一枚200瓦的灯泡那样亮得晃眼。
大脑飞转,急若掣电,我似乎到达了一种谵妄状态:
“这半空中的小屋,难道是一个卫星接收器么,无数信息飞进我的身体,丝线般绞缠在一起,而我初来乍来,双手空空,还没有解码器。”
“爸爸一定有一个解码器。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这一切呢?”我辗转不安,澄澈静寂的夜空并未给我抚慰,我越来越烦躁,从床铺上坐起,黑鬼蜷在我脚边,正安逸地睡着,此刻也被我吵醒了。
显然,黑鬼和爸爸一样,已经达到它的目的,它把我赶出原来的小屋,便是为了让我搬入这间半空中的楼阁。“现在它该是十分满足的。”
见我精神抖擞地坐在床铺中,黑鬼迟疑半刻,便小心翼翼靠近了我。它先用脸颊蹭我的膝盖,而后用温暖而粗糙的舌头舔我的手心,最终,它竟然爬进我的臂弯,温存地倚在我的怀中。更奇怪的是,黑鬼做着这些的时候,我却丝毫没有不快,恍惚中我觉着,黑鬼好似一股气流,缓缓融进了我的身体,不仅如此,我蓦地认定,一直以来,黑鬼真是逸出我身体的某个意念,之前我们不亲近,是因为我没有认出它、确认它,而今,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可谓真相大白,黑鬼也就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成为我的某个冥想、我的某个念头,或者某种潜意识。那么,黑鬼的到来,就好像人随着生命的形成、成长和湮灭,而顺次生出与泯灭的渴望。黑鬼是如约而来的。黑鬼最初与我的对立,完全是因为我背离了那些隐匿的路标,它由此便像一个幽灵般跳出我的身体,阻拦我,驱赶我,就如同爸爸在暗中引带我一样,是为了将我推回我的未来。
“现在,他们都如愿了,而我却刚刚开始。为什么必须是这样一种状况呢?渠三在林子外,恐怕比我快乐许多吧。渠三若是看到我住在半空里,一定会瞧不起我的。”
我并非无端想到渠三,一夜之间,我急剧地看透了自己的处境,就如同从前渠三所说:“你难道要与你爸爸一样,活成一副可怜相吗?”现在,我确如渠三所言,一副可怜相,茕茕居住在半空中,过着封闭而孤单的生活,这与渠三热切向往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由于自尊心的缘故,我不愿渠三看见我的这副可怜相,但也并不憧望林子外,去过一种与渠三相仿的生活,在我看来,那种热闹与喧响也依然是一种荆棘丛生的境遇,在那里,每个人也依然是独来独来,踉跄狼狈,谁也救不了谁,谁也无法替人受过。爸爸说过:“各有各的下场,谁也不会比谁更风光。”爸爸心若明镜,而渠三,他大概到死都不会明白这些的。
这一晚之后,我固执地认为爸爸掌握着一个解码器,他藏起来不拿给我看,完全是因为这个解码器会泄露出他的秘密。譬如那些丢失的椅子,为什么爸爸总是吞吞吐吐,不肯直言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没日没夜想这件事,因为过于专注,有几次,连爸爸登上梯子给我送饭的声音也听不见。
一天黄昏,爸爸坐在屋檐下乘凉,我终于忍耐不住,从窗内探出身子,提起嗓门向爸爸打听这件事。
“爸爸,那些椅子到底去了哪里?您拆了它们吗?您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
“小梅,那些椅子,林子里用不着它,你是看到的。”
“那么,您为什么不把它们拿到林子外面去呢?在外面,它们很值钱的。”
“爸爸是去过林子外的,那些椅子也跟着我去过,但许多人都不知道爱惜椅子。”
“您为什么不再等等呢?或许,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事情会有改变。”
“小梅,爸爸年岁大了,老眼昏花,脑袋也时常糊涂,有些事,你自己慢慢想吧。”爸爸说到这里,就不再理我了。
时间一天天空阔起来,很快,我习惯了我的新生活,也渐渐适应了拔地而起的视力。黑鬼变得安静与体贴,终日陪伴我,它黄澄澄的眼睛不再像从前那样凌厉地望着我,而是一种俯首认命的清澈与深远。
偶尔,呆得腻烦了,枯燥了,我也会离开我的空中楼阁,回到地上,与爸爸说些家常的话,譬如夜里的蚊子多不多?爸爸的烟丝是不是又泛潮了?或者,那只白兔子又把它的洞窟掏深了几米?但我们从不谈我在空中楼阁做了些什么,以及我心里的感受。事实上,有时候我是想主动跟爸爸说些什么的,比如:那上面虽然凉快、清静,虽然可以看到更多、更远的事物,但孤单一人,以及枯燥的寂静,常常令我既疲惫,又烦躁。更重要的是,这样长久地住在上面,我会丧失了生活的能力,会越来越笨的,饭不会做,连帮爸爸收烟叶也做不了的。而这些劳动的技能,这些杂七杂八的农活与家务事,以及日常里每一件生活器具所包涵的情感,都是生活的乐趣,更是我在空中楼阁里胡思乱想所依赖的东西。但爸爸从不给我机会。每当我将话题悄悄引过来,爸爸就用另一些话头岔开了它。所以,我猜想,爸爸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是担心我被地上的踏实与温暖重新困住,再也没有勇气回到空中楼阁。
但爸爸也并非总是坚定的。有时候,我从空中楼阁的小窗望下去,窥察爸爸的一举一动。爸爸不再刨木头,他每日早出晚归,进出林子,背影一天比一天僵硬、机械。最初的一些时刻,我和爸爸的目光相遇,彼此都会有些感动,我会情不自禁流出一些心酸的眼泪,爸爸则紧咬牙关,两颊微微颤动。后来,我们似乎都麻木了,我们谁也无法改变这样一种局面,也就只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有天半夜,我听见爸爸在他的房间里摔摔打打,似乎在与人争吵,茶杯、闹钟、凳子接连不断地砸在了门与墙壁上,听听哐哐,声响极大。
翌日一早,爸爸就在树下喊我:
“小梅,小梅,快起来,爸爸做了你爱吃的糖水鸡蛋。”
我未曾完全醒来,听到呼唤以为是在梦里,心里十分甜蜜。但守在我身边的黑鬼如同发现了不祥之物,圆睁着眼睛,尾巴像一条钢鞭似地竖起来,发出了一声凶狠的嘶叫。我一骨噜坐起来,一把搡开黑鬼,从窗口探出半个脑袋。爸爸站在院中央,太阳晒着他花白的胡须,和他焦惶的眼神,一张脸显得格外憔悴。
霎那间我明白了,眼前的一切是爸爸昨晚斗争的结果,他像我一样,时常会感到寒冷和孤独。现在,他正在向我求救,希望我用亲人之爱帮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毫不犹豫打算冲下去,但刚抬起脚步,就发现了挡在门前的黑鬼。
黑鬼嘶叫了一声,声音凄厉凶险。我头皮骤紧,恶狠狠盯着它,从前那些想置它于死地的念头又闪了出来。我抠在窗棱上的手指开始颤抖,血液涌上头顶,牙关咬出了声响。而黑鬼,它亦如从前,身体虽然稍稍后退,却毫不示弱瞪着我,脊背上的毛已经竖起,喉咙里低沉地滚动着一种可怕的声音,很显然,它已经做好与我一拼到死的准备。
黑鬼这幅架式让我不敢掉以轻心,我明白我是不能轻易取胜的,别看它只有我半个胳膊长,但我的手边没有任何工具,除了一只表,小桌上的一只墨水瓶,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使黑鬼立即毙命。
“小梅,小梅,快下来啊,吃完糖水鸡蛋我们去林子里捕鱼,你小时候不是最喜爱跟爸爸一起去么?你看,爸爸都准备好了午餐,咱们要走很远的路呢。”
黑鬼又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它的身体已如上弦之箭,微微颤动着,对准我,势在必发。
我心里突然胆怯起来,那一瞬间,我认出自己不能战胜黑鬼,就像我无法打败另一个自己。我满脸羞愧,一身冷汗,便颤悠悠回了爸爸的话:“爸爸,我胃里不舒服,吃不下去呢。您像是很疲惫的样子,去屋里休息吧。”
“小梅,你变了许多,你不要爸爸了吗?”
“爸爸,我胃里难受,爸爸,我不能……”话未说完,我关上了小窗,抱住头,身体蜷成一团。爸爸仍在树下呼唤我,每一声都如同刀尖,剜在我的心上,而我不能答应爸爸,黑鬼不会允许我这样做,我知道,没等我打开门,黑鬼就会扑上来,抓烂我的脸。这一刻,我抱紧自己的头,是在拼命遏止想掐死黑鬼的念头,因为我根本斗不过黑鬼。
这剧烈的一幕持续了半个上午,直到爸爸筋疲力尽回到了他的小屋,我才把紧捂在耳朵上的双手放下来。
接下来很长时间里,我浑身冰凉,心中注满一种彻骨的绝望,我知道爸爸再也不会呼唤我,我会像一根断了线的风筝,游荡在青溟溟的天空中,直至最终消失。想到这里,我抬起头看看黑鬼,它蹲在小屋一角,俨如一尊乌金雕塑,身体与地板形成一个尖锐的直角三角形,然而,当我端详它的眼睛,却发现与它勇士般的身影截然相反,它凝视我的目光无比哀伤、凄凉,就好像荒野中一个孤苦伶仃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