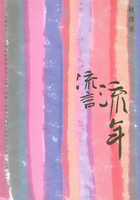月光大摇大摆,占据了大半个小屋,我的影子斜躺在地面上。为什么只有我这样不安呢?我再次躺下,想尽办法招唤睡眠,终于感到有一双手按在了眼皮上。我深深吐口气,就好像一个痛不欲生的病人,终于看见了前来拯救他的死神。
意识混乱,也就四肢沉重,我睡得不实,梦境若明若暗、或近或远,但是我还能听到那些声响,林子里的小动物们又跑动起来了,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它们并非跑在林子里,而是钻进了我的胸腔、大脑和骨头,它们忙忙碌碌、叽叽喳喳,像城市的车流与人群一样,穿梭不息;然而我看不明白,它们所忙为何?似乎一切都毫无意义,仅仅是忙碌着,让嘴和脚不要停下来。
夜像一口荒弃已久的深井,我被困在其中,只能任由这些声响在我的体内连成一片,直至它们完全成为了我。后来发生了更可笑的事情,我梦见这些声音变成了一张张长在我的心、肺、大脑、胃以及一切器官上的嘴,这些嘴不停讲述着、劝说着,甚至吼叫着我听不懂的名词、术语和字眼,它们用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语言,但是意义十分显明,那就是我违背了它们的意愿,我正处于一个危难里,而我既不自知,更不打算觉醒。整整一夜,我在这梦里游来荡去,梦醒前,突然明白这些恐怖的东西竟然都是黑鬼驱使来的。
黑鬼就在这天夜里开始抠抓墙壁的,不可思议的是,当确认是黑鬼发出的声响,我便莫名其妙说了那句话:“终于来到了啊。”说完这句话我就醒了,但是醒来我觉得这不是梦话,它显然是冲着窗外的黑鬼而来的,而且张口就蹦了出来。
关于这天晚上的事,我对爸爸只字未提,爸爸也就更不会说什么。
但是黑鬼近来变本加厉,它抠抓墙壁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时间越来越长,为了防止我把它关在仓库里,这些天它很少靠近我,白天只在院里逡巡,一近黄昏就没了踪影,但是半夜会准时出现在我的窗外。因为它的肆无忌惮,前几天,我用爸爸刨子上的刀片把它的头打破了,伤疤难看地结在左额角处,糊脏了那一块的皮毛,整张脸看上去仓惶又沉痛。黑鬼终日顶着这块伤疤在我眼前走来走去,仿佛让我铭记自己的凶残,但是这并没有加重我的罪恶感,反而更让我恶气难消。
“这畜牲疯了。它想把我赶出小屋。”我愤愤地想,身体像是就要爆炸了。回想黑鬼这些年做过的事,我恍然认出每一件都是居心叵测的,每一件都在暗中挑逗着我、指使着我,而我所有的敌意与反抗最终均化为徒劳,不仅如此,我的阻挠反而加速了事情的发展。
唯有我最清楚,我与黑鬼之间的事。
我决心做个了断,但是这件事需要避开爸爸。
我向小屋东边的仓库走去,那里有爸爸自制的老鼠夹,沉重又灵敏,附近的黄鼠狼都知道这个夹子的厉害,所以远远躲开了我们的小屋。
仓库阴暗潮湿,撂满了被拆散架的旧椅子,顺着窗缝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那个硕大的老鼠夹躺在角落里。仓库里霉气刺鼻,但为了躲开爸爸,我只能藏在这里研究老鼠夹的机关,正在这时,门外传来爸爸的话音:
“小梅,你忙些什么呢?仓库里的东西是不能轻易碰的。”
“爸爸,我闷得慌,只是随便看看,您去煮茶吧,我要喝呢。”爸爸没进来,脚步渐渐远了。
这天晚上我一直等着,脸发烫、手脚冰凉,神经一刻也没放松过。
事情像平常一样,黑鬼准时在半夜又抠抓起墙壁了。
听见声音我便拿起手电冲出屋门,老鼠夹安静地躺在我的窗下,生了锈的弹簧上结结实实夹着一条木棍,而黑鬼,它钢针般扎在一旁,黄眼睛瞪着我,莹光闪闪,像两块透明的水晶球,深幽无底。
翌日,爸爸对我说:“小梅,我把夹子收起来了。”
三天后,我下了决心,对爸爸说:“我不能在小屋里住了。”
“小梅,你近来脸色不好,是因为想太多事了。”
“爸爸,我要离开这间小屋。”
“那么你去哪里住呢?小梅,你不用理会黑鬼,爸爸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爸爸还遇见过更凶猛的猞猁呢。”我看着语重心长的爸爸,一时觉得他苍老了许多。
“猞猁后来为什么走了?”
“就是因为我不理会它。”
“爸爸,我不能像您一样不理会它,我觉得跟它斗很有意思呢。”
“小梅,你打算搬去哪里?”
“那儿。”我指了指老柏树伸开在半空中的枝桠。
“小梅,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黑鬼会仍然跟着你。”爸爸知道无法劝服我,但仍然不放弃最后的努力。
“爸爸,那会是您一生中最完美的作品,一间长在树上的小房子。您不是一直在等待一件事么?这件事您不做便无法安心,也许正是它呢。”我仿佛已经看见了那个小屋,它高踞在半空中,坚固又飘忽,卡在粗大的树干间,仿佛巨人攥在手心里的一个盒子,盒子里盛放的事物令人揣想,很难断定它们是不幸,还是光明?
“爸爸,柏树会不会活过来?”我突然觉得这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这可说不好啊,最担心的事往往最容易发生。”爸爸提着锯子走进了树林。
爸爸走了,留下我独自揣摸他的话。
关于我的荒唐之举,爸爸似乎并未感到惊讶,从话音来看,仿佛这件事早在他预料之内,不然,爸爸为什么会说“最担心的事往往最容易发生”呢?从什么时候起,爸爸开始为我担心了呢?爸爸从未对我提起,也不曾向我暗示过,不仅如此,此前,对于我每一次不寻常的举动和选择,爸爸从未表现出意外和反对,仿佛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爸爸为什么不问我?我为什么要搬去那间树上的房间?我在那个房间要做什么呢?这些话我替爸爸问了自己,但问过之后,我又觉得这些话问不问都一样,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像密码一样同时长在我和爸爸的心里,一旦说出来,就离开了密码的本义,就不是原来的真相了。
爸爸很少跟林子外的人打交道,我的记忆里,爸爸总是独自思考,并时常自言自语,好似有一个隐形人在暗中纠缠他,不断向他发问,不断给他制造麻烦。爸爸被这个隐形人折磨得越来越寡言,越来越苍老,也越来越固执,就像那两棵死去的老柏树,再也不去质问生活中的为什么,只是一副倔强的样子,站立在天空下。爸爸的心和这片林子一样深呢。我不是一次这样感慨着。想到这里,我不禁难过起来,眼泪溢湿了脸,父女连心,我虽然无法知道爸爸心里想些什么,也无法替他驱赶那个折磨他的隐形人,但却一日日清晰地感受到了爸爸心里的痛楚。我多爱爸爸啊,每逢烦恼来临,我就会因为想到了爸爸而感到一些安慰。
“爸爸也经历过了吧?他是怎样度过那些夜晚的呢?”
“林子里住着人家,但是我们的小屋距离他们很远,在我来到这个世界前,爸爸为什么会选定这个地方呢?爸爸为什么从不带我离开这里呢?”
“爸爸要在这里做什么事吧!”
奇怪的是,我从未央求过爸爸,请他带我去林子外看看。我和爸爸成了一副脾性,终日忙碌,觉着有做不完的事。但是我们谁都不曾说出自己要做的事。
这些事是无法说清的。
我从爸爸的眉间看出,没有一日他不在忙着这些事,虽然身体一天天衰老,他却仍然没有止步的迹象。爸爸为了什么呢?我猛然想起一个熟悉的梦境,我在一条昏暗的小路上疾行,而爸爸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一个叉路口,然而爸爸并不招呼我,每每用陌生人的目光看我一眼,便漠然转身而去,我急着上前追赶他,爸爸却已然没了踪影。
爸爸在忙些什么?我所能说出的,仅仅是近一年来他日日不息所做的一件事。爸爸每天刨木头,我们的小院也就每天弥漫着木花的清甜。黑鬼偶尔会很淘气,仿佛木花的香气使它快乐地发狂,它欢跳在木花堆旁,有时整个身体钻进去,杏白色的木花堆随着它的翻滚而起伏,仿佛胎儿在母体内的蠕动。木头一根根被刨得溜光笔直,或长或短,却只是一根根码在屋檐下,没有任何用处。
“爸爸,这些木头有什么用呢?你要把它们做成什么呢?”我曾经问过爸爸。这些木头虽然被整齐地码在一起,爸爸却没能把它们做成任何一件有形的木器。爸爸把它们刨光后就扔开,就好像任由它们自己想象自己未来的形态,它们想成为什么都有可能。但私下里我又这样猜想:爸爸也许什么都不会做了,他的技艺随着年岁的苍老,一并都褪化了。
“总会派上用场的。有些事情太远太模糊,爸爸现在不好对你说什么。”
“那些椅子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小梅啊,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做得好有什么用?它们都是一些派不上用场的东西。”
“那么,这些木头会派什么用场呢?”
“不知道。”沉默了很久,爸爸只说了这三个字。
“不如现在扔了它们,您每天就不用辛苦了,去捕鱼打猎,那样会安逸许多。”
“那样一来,爸爸就真得老了,连帮你、陪着你也不行了。”
“爸爸,您可以不想那么多的。”
“我知道,但想不想的,可没那么简单,就像你没有随渠三去林子外一样。”
“我是想过和他一起走的,但渠三非常着急,一刻也不愿等,我那时很犹豫。”
“小梅,爸爸当初做那些椅子时,也是十分犹豫的。”
“但是这些木头,您仍然犹豫吗?”
“这是另一件事了。你会明白的。”爸爸的眼神十分散乱,我没敢再往下问。
一个月后,我的空中小屋建成了。屋檐下那些光溜溜的木头,一根也没剩下,它们成了一间小房子,就好像一个人的思绪,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让我在惊叹之外,无端地生出一些惧意。
为了便于上下,爸爸钉了一根牢固的梯子,梯子顶端恰好正对屋门,阶面很宽,放得下我的整只脚。因为这间小屋,爸爸做得十分辛苦,仿佛沉浸在一件遥远的往事中,神色凝重而复杂。而我除了给爸爸煮饭,没能帮上一点忙。小屋稳稳卡在柏树粗壮的枝杈间,漂亮又结实,门窗、坡檐、瓦片,爸爸巨细无漏,变戏法儿一般,完成了这件与玩具近似的作品。
我从未见到爸爸这样精细过,譬如在小屋的最后一道工序上,爸爸不厌其烦熬着一种粘胶,我搞不明白它由哪些成份组成。因为比例没掌握好,爸爸失败过几次。那段时间,他眉头紧皱盯着罐子里的液体,仿佛把一生的赌注押放其中,所以,当最终熬出了令他满意的一罐胶时,爸爸脸上露出了心醉神迷的神情,像捧着一个婴儿似地,带着肺腑之喜,登上了梯子,而后细针密缕,将每一根木缝糊得透不过一丝儿风。
“小梅,你住在上面会很孤单的。”
“爸爸还是与我在一起的啊。”
“爸爸再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了,你自己要当心,事情须慢慢来,不要太逞能。”
“上面风会很大,声音也会更多吧。”
“恐怕是的。小梅,你如果想搬下来……”爸爸话只说到一半就住了口。
“爸爸,黑鬼会陪着我的,你看它,已经在上面等我了。”爸爸没说完的那半句话,也正是郁结在我心里的,但爸爸神情莫测不定,时而痛心,时而又决绝肃穆,所以我横了心,不能让自己现在就打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