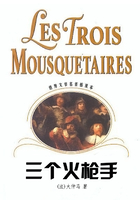半半村的由来
半半村是个什么样子呢?半个村子吊在山坡上,半个村子凹进深沟里。
吊在山坡上的全是土窑洞。土窑洞因势而建,或高或低,错错落落。这土窑洞是土木结构,以土为主,窑墙是夯土,十分宽厚,像桥墩一样支撑着窑洞。窑脊是用土积一块块碹起来的,土积是用土、黍子秸秆和成泥,用弯模子托出来的。窑仓也是夯土。窑顶用泥抹,勤快人家抹窑顶时在泥里掺些牛粪,这东西光溜、瓷实、隔雨。至于凹进沟里的那半个村子,他们就没有坡上人家洋气了。他们住的叫挨打窑,这挨打窑就是在山坡边挖个洞,整个“建筑”除门窗是木头,灶火门垒几块砖头,剩下都是泥和土。村里通往各家的路宽窄不等,这家的窑顶是另一家的窑根,担一担水不知要爬多高的坡,绕多大的弯。
你是不是要责怪半半村的祖先了,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地儿?其实半半村的祖先很聪明。他们选择栖居之处大概有两个考虑,一是寻偏僻之处便于隐身,以逃官府徭赋之苦,以避战争烽火之扰;二是找近水近柴之地,以省劳作误时之力,只求安身立命。半半村的村民说起他们村子来还很自豪,一说他们生活的自在安宁,日本鬼子都没来过;二说以前沟里有一条河,河里鱼肥虾壮,只是后来上游筑起水库,下游便剩下了河床。
扯远了,扯了这么远还没有交代半半村名字的由来。半半村土地分三等。沟湾地为一等,二阴地为二等,坡梁地为三等。半半村的祖先是靠租地为生的,租金也分为三等。二阴地收沟湾地的一半,坡梁地收二阴地的一半,故名半半村。可现在沟湾地没水了,二阴地受旱了,坡梁地就不用说了。有一位作家说,北纬三十八度,三百八十毫米降水线附近的农民,他们仰望上天的次数比其他地方多,他们收获的条件十分苛刻和严酷,他们求得温饱十分不易。半半村降水量连三百五十毫米都不到。
开头
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年秋。半半村的蹲点干部换了个硬手,在全县都很有名气。因为硬,所以才由乡武装部长提为乡党委副书记。他的名字叫李山。李山个头高,块头大,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腰圆膀阔,气宇不凡,来半半村时戴着个黑呢鸭舌帽,好不威风。后来人们都叫他山书记,我们也称他山书记好了。
这山书记来半半村蹲点是带着硬任务的——收农业税,一万三千二百元;收统筹费,四千六百元。收农业税的任务是压在乡党委、乡政府头上的。由于县里财政太穷,开工资都有困难,县政府决定:乡干部、教师的工资由乡政府解决,实行包干。也就是说,收回农业税,乡干部、教师就有了工资;反之,工资就出现了缺口。收回统筹费,乡政府的一切开销,包括炊事员、话务员、线路员、广播员、打字员、公务员、放映员、治安员等等十几大员的工资才能支付,正常的办公经费才能保障,还有这个费、那个费才能应付。县政府穷,乡政府更穷。
派山书记来半半村蹲点,这是乡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研究时山书记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尚方宝剑,他可以先斩后奏;二是要挑选一帮人马,乡党委书记全部答应了。于是山书记挑了一个副乡长、一个乡武装部长、一个乡财政助理和一个乡派出所所长,他们个个全是硬手,我们这个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干部会
山书记是骑着“红公鸡”来的。“红公鸡”是啥玩意儿?是红色的嘉陵摩托车。这嘉陵摩托车可是很贵的,一辆八百多。这个乡里共有三辆,乡党委书记一辆,乡长一辆,乡办公室一辆。山书记任务艰巨,去半半村的路又不好走,临行前,乡党委书记把乡办公室的摩托车交给了山书记。山书记骑着“红公鸡”,“红公鸡”屁股冒着黑烟,其余人马各自骑着自行车,下沟上梁,尘土飞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半半村,穿街越巷跌跌撞撞直奔支书家,到了支书家也不过半前晌儿。
支书家在山坡上吊着,阳光暖暖的,风儿柔柔的,半半村的空气十分清新。支书家三间土窑洞一堂两屋。院子里猪圈、鸡圈、羊圈,高高低低,柴堆、粪草、农具,乱七八糟。土窑洞的墙面被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道道。窑洞内倒还说得过去,窑墙刷得挺白,支书老婆每天用红土稀泥抹一次地,这种地看上去明净光亮,但只能看,不能踩。支书家炕沿是红杏木,炕上铺着苇席,苇席破烂处糊着牛皮纸,窗台是用水泥抹的,窗户下面是不大的两块玻璃,窗户上面糊着麻纸,炕上一堆长方形被子用一块床单蒙着,地下有一个柜子,红漆皮斑斑驳驳,柜顶上放了两个输完液的瓶子,瓶子里装着红水水,这就是半半村村民的“豪华”摆设。正面的墙上贴了两张露大腿、露胳膊的女人画,画上满面春风的女人,看着谁和谁笑。地上还有一个水缸、一个烧火板凳、一个暖壶。支书家没有茶叶,支书老婆用罐头瓶当杯子给他们倒上了白开水。支书老婆认得副乡长也认得武装部长,经他们介绍后认识了山书记。山书记的黑呢鸭舌帽支书老婆第一次见到,她觉得那帽子像铲铲一样,好怪好怪。
支书回来后,副乡长向支书介绍说:
“山书记刚调来,管党务,是第三把手,排在书记、乡长之后,又是后备干部,不久就是乡长的接班人。”
支书和山书记紧紧地握了握手,支书也觉得这山书记与众不同,那铲铲帽就不一般。山书记很是高兴,简单地说了一下他们的任务、目标,想上午就开个干部会。支书心事重重地说:
“行,今天村里正好有鲜羊肉,让村干部也跟上沾沾光。”
羊肉的香气和水蒸气弥漫了支书家的整个窑洞,干部们也稀稀拉拉地到了。支书住在东面的窑洞,会议在支书西面的窑洞召开,因这间窑洞空间相对大点,只有两缸腌菜占着地儿。干部会由武装部长主持,山书记主讲。山书记讲话的声音把窑顶上开裂的白土片儿震下来不少,他讲自古种地都要纳粮,他讲要求,讲时间,讲措施,讲步骤,讲了干部带头,党员带头,党员干部的亲属带头,讲了要牵羊,要瓦粮,要断电,要停水,只要能收回农业税,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粮食除去土,牲口除去狗。瓦回的粮食要全部送到粮站,谷子三角四,黍子三角六,还要扣除水分,牵来的羊,赶回的猪,只限三天赎回,三天过后统统拍卖,拍卖多少算多少。下午三点山书记还要开村民大会。
山书记叫村干部挨个表态,支书一脸尴尬,慢悠悠地说:
“羊肉烂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说。”
羊肉的香味,腌菜缸的酸味,小兰花的烟味,混杂在一起实在是熏人,山书记既想吃羊肉,又想换个环境,点头同意了。
土炕上放了一桌,乡干部在炕上,地下放了一桌,村干部在地下。桌子上是一盆羊肉、一盘酸菜、一碟辣椒、两瓶酒,那酒的名儿不好,叫“闷倒驴”。每人一个粗瓷大碗、一个酒盅和一双筷子。
谁都不说话,羊肉占着嘴哩,盆里的羊肉不一会就剩汤汤了,桌子上扔了一堆堆羊骨头,这才开始劝酒。村干部挨个敬山书记的酒,山书记碰酒之前总要说一句,坚决完成任务。
支书说:“能完,能完。”
其余村干部也都说:“能完,能完。”
村干部还想喝,山书记说:“下午开村民会,不可多喝。”
支书十分同意,再喝没酒了,一共两瓶。
山书记心中暗喜:谁说半半村工作难做?
村民会
半半村没有大队部,支书就一个戳子,学校才有个桌子。以前大队有个喇叭,后来喇叭线丢了,喇叭杆让人偷了,喇叭当废铁卖了。要召开村民会,只有干部分头叫人了。
会议地址在学校操场。学校是两排土房,穿鞋戴帽,穿鞋是说房的根基上有几层砖,戴帽是说房顶上有一层瓦。学校院墙是半人高的夯土,残败不堪,校门比较高级,是角钢和钢筋的结合体。学校的窗户有的安着玻璃,有的钉着塑料布。学校课桌有木头的,有泥胎的,学生屁股下多数都有个垫垫,有棉花的,有羊皮的。
节气已近霜降,地球好像转得快了。山书记准时赶到学校,一边琢磨他的动员讲话,一边等人。等啊等,等啊等,眼看天就要黑了,山书记没有看到一个来开会的村民。蓝色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窑洞的烟囱里冒出来,被风吹散开去,学校操场上捉迷藏玩的孩子们都回了家。一群在学校屋檐旁栖居的麻雀在学校的操场上空“叽叽叽、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说,山书记,没人啦,山书记,回家哇。山书记把支书叫到老师宿舍,摘下铲铲帽,想摔在支书的脸上,但没敢下手,于是摔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手指头指着支书道:
“喝猫尿(指酒)时本事挺大,喝完猫尿啥事儿也没了?眼皮单艳艳的,头发黄乱乱的,脑袋黑呛呛的,我看世上数你灰!什么德性?连个人也叫不来,还收粮哩,收你奶奶的个帽子!还当不当了?”
支书满脸通红,眼睛一翻一翻的,不吭气儿。
山书记又骂道:
“你放屁呀!”
支书愤愤又低低地说:
“你放哇。”
支书说完扭头走了。
武装部长把山书记叫到一边提醒道:
“你把支书撤了,这村可再找不到支书了。”
山书记脸色铁青,气不打一处来,捡回铲铲帽戴在头上,把“红公鸡”钥匙交给武装部长,他坐在“红公鸡”后面带着那一帮人窝窝囊囊颠颠簸簸连夜回乡了。
重新开头
山书记向党委书记汇报要撂挑子,半半村他是不去了。党委书记说,一口吃不了个胖子,不要着急慢慢来,要知难而进,越是困难越向前,半半村要改变战略,让乡治安队进驻吧,而半半村的蹲点干部还必须是你山书记,至于半半村的支书人选嘛,能维持就维持,维持不下去,你说咋办就咋办。
这样,我们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开头。
山书记重上半半村,队伍扩大了,增加了一个班的治安队员。这么庞大的队伍开到半半村,首先要解决吃住问题。前面说过半半村没有大队部,半半村最不缺的是光棍,光棍房不少。山书记作为总指挥和派出所所长住在了学校,其他人三三两两住在了光棍家,这是住。吃可就麻烦了,以前下乡干部挨家挨户吃派饭,现在这饭是派不出去了,山书记下令在学校起伙。于是,老师的宿舍边儿垒起了锅灶,食物自然由大队供给。山书记定的伙食标准是豆腐、山药蛋,每餐每人不少于二两肉(早餐除外),晚上每人平均二两高粱水,高粱水这是山书记的原话,比猫尿要好听得多,文明得多。早上稠粥,中午米糕,晚上加两个罐头,乡干部每两天发一盒烟,这伙食由村妇联主任负责安排。
吃住的问题解决后,自然就是工作了。工作碰到的第一件难事是算账、定政策。算账是什么意思呢?谁家国税多少、提留多少总得有个数呀,这国税就是农业税,上面有指标,有数。可提留就不统一了,一是以粮食产量提,二是以人提。今年因乡里明确规定,拿回乡里的统筹费按百分之十发奖。因而山书记决定增加提留额,每斤粮增一分,每个人增一元,再加上兑现义务工,这样半半村提留、国税、义务工都得重新核算。话好说,会计算账事情就多了,有调地的,有换地的,有的户增了口,有的户减了人,义务工男劳力十五个,女劳力折半,有够年龄的,有超年龄的,有嫁出去的,有娶进来的,有的有户口,有的还没户口。定政策是什么意思呢?光收今年的,还是连往年的也收,半半村除干部外,家家户户欠大队的钱。山书记的政策定得不错,当年的国税、提留、义务工全清,拖欠清百分之二十,每家每户今年该交多少数,算出来后贴在大街上。
会计的账一下子算不出来,这一帮人不能干坐着等数。于是山书记决定兵分两组,第一组先从干部下手;第二组碰硬,从难缠户、拖欠大户开头,你能说这政策有毛病吗?干部的头一带,难缠户、拖欠大户一交,剩下些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会主动把粮食送出来。第一组山书记带队,第二组由副乡长带队。村干部引路,赶车,乡干部下令,治安队员瓦粮、拉羊。
支书老婆
半半村数谁的官大,在外的不算,就本村而言,第一个大官是支书。山书记带着这一队人赶了两辆驴车,山书记想叫全村人看看他从支书家搬出了粮食,故意把驴车停在了支书大门外较远的一块平地上,招呼他的组员跟着他去瓦粮。
支书老婆一个人在家,山书记很有礼貌地说:
“嫂子,我们来瓦粮了。”支书老婆正在纳鞋底,她以为开玩笑哩,撇了撇嘴说:
“瓦去哇。”
支书家堂屋有两个水泥仓子,分别装着半仓谷子,半仓黍子。谷、黍上面堆着杂物,治安队员把杂物搬开,真开始往麻袋里装粮了。这装粮的声音把支书老婆惊了出来,支书老婆傻眼了,“哇”的一声哭了,随即身子像麻袋一样倒了下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治安队员吭哧吭哧地从支书家抬出五麻袋粮食来,毛驴车吱扭吱扭赶到了学校,山书记跟在毛驴车后,威风凛凛,那歪戴着的铲铲帽好像在说:
“自古种地都要纳粮,我要看看谁敢和我对抗!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是谁!”
山书记打发副乡长和支书谈了话,支书只是说:
“我不欠大队的,我的工资够国税提留了,你让会计把账算出来,做个了结,我欠大队的,我给,大队欠我的,还我,从现在起,我不干了,你找你的人哇。”
支书独自往家走,街门敞开着,家门敞开着,堂屋一片狼藉,粮仓空了,支书眼圈红了,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他喊了一声老婆的名字,大板,呜呜地哭了出来。屋内无人应声,他又喊了一句,大板,推开了东窑洞的门,窑洞内东西照旧,没有人,他趔趔趄趄奔向西窑洞,西窑洞的腌菜缸被搬倒了,腌萝卜、腌白菜撒了一地,地上白沫团团清晰可见,酸味扑鼻,哪里都没有大板的影子。
新班子上任
这半半村的支书也确实难找,党员基本上都没牙了。山书记选拔支书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够完成农业税任务。山书记早就放出了风,这几天等着有人来找他——毛遂自荐。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连个鬼也没有,别说人了。乡里的一帮干部和那些治安队员都在半半村待命,没什么事儿,只有打扑克、喝酒。支书不干了,主任后退了,会计的账迟迟算不出来,招呼这帮人的仅剩下了村妇联主任周改改。周改改是四川人,据说是被人贩子拐到半半村的。是拐来的,还是被介绍来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改改已爱上了半半村悠然自在的生活。半半村的女人管丈夫统统叫老汉,不论年纪大小。周改改的老汉在外的时间多于在村的时间,周改改老汉回村时带的东西总是人民币和大米,周改改还不时把节省下来的钱或邮给在四川的母亲,或作为回四川的路费。都说四川人个子低,周改改可不低;都说四川人不善理家,周改改的家理得有条有理;都说四川人只会吃米,周改改做饭炒菜全是把好手;都说四川人丑陋,周改改瓜子脸,眉清目秀,牙齿洁白整齐,脸上虽有几个雀斑,可那雀斑并不讨人嫌,脸儿白生生的,细皮嫩肉的。周改改也不擦油抹粉,给人一种内在的、自然的美。周改改给山书记推荐了一个人选——二拐子。
二拐子叫什么名儿,村里人并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路一颠一颠的。周改改的理由是:二拐子是大户,无人敢欺,光棍一条,村民不和他计较,如果这个二拐子给当,收税任务就能完成。周改改这几天精心伺候山书记,山书记对周改改早就有了好感。山书记和二拐子谈了一次话,二拐子答应了,但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当支书。
山书记说:“你不是党员不能当支书。”
二拐子说:“那我不干,你开会就说我是党员了。”
山书记说:“入党要有一年的预备期哩。”
二拐子说:“预备啥哩,这收粮就是打仗。”
山书记说:“那不行,宣布你为村委会主任,半半村暂不配支书,人们会把你当支书的,你就是一把手,实际上就是支书。”
二拐子说:“那行。”
第二个条件是以前的干部二拐子一个也不要。
山书记说:“要留下会计算账,交接账目误事。”
二拐子说:“收完粮我还是要换的。”
山书记说:“你完成收粮任务之后可以考虑。”
二拐子妥协了。
山书记说:“周改改这个妇联主任就不要换了,她一直管着我们的伙食,伙食管得不赖。”
二拐子说:“行。”
于是二拐子一下就被宣布为半半村村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新上来两个副主任,一个民兵连长,一个治保主任,这些人选都是二拐子提出来的,加上会计和周改改,七个人的新班子搭起来了。
意外
新班子一宣布,二拐子召开了干部会。干部会就一项内容:自古以来种地都要纳粮。明天七个干部必须把自己的和父母亲的农业税全部交来。时间限制到下午五点。粮食交齐之后,杀两只羊,犒劳大家,后天分组瓦粮,一星期完成任务。
二拐子还真有两下,你别看他走路一颠一颠的,号召力还挺大的,不到五点,学校的教室里就垛起了三十多麻袋粮食。二拐子挺高兴,山书记自然就甭说了。周改改的羊肉不到五点也炖好了,这天晚上乡干部、村干部、治安队员都放开了量,高粱水喝了一瓶又一瓶。
山书记喝多了,二拐子喝多了,周改改也喝多了。前几天,山书记和派出所所长住一个屋,派出所所长换了新班子后推说所里家里都有点事回去了。这样,山书记一个人住在了学校里。山书记正准备睡觉,周改改跑进来让山书记给她做主,理由是喝醉了的二拐子调戏她,说今晚要到周改改家去过夜。
周改改羞涩涩地说:“家我是不敢回了,除非山书记和我去做伴。”
山书记迷迷糊糊地说:“走,我把你送回去。”
这一送送出了麻烦。一男一女,一公一母。一个老汉经常在外,一个老婆眼下不在。一个已露出了话儿,一个正想寻个法儿。这会儿,一个被酒精烧出了激情,一个被高粱水麻痹了神经。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就发生了。天有不测风云,山书记和周改改万万没有料到,周改改的老汉这天夜里回到了半半村。周改改老汉的敲门声、吆喝声把周改改和山书记从睡梦中惊醒。这周改改和山书记都慌了神儿,都没了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周改改也没有想到,老汉还拿了个手电筒。这手电筒反倒帮了山书记的忙。山书记借着手电筒的光,跳上墙头跑了。周改改老汉自然认不得山书记,山书记的铲铲帽却丢在了周改改家。
这件事发生在前半夜,前半夜漆黑一片。因此,月亮不知道,星星不知道,只有三个人知道。山书记不敢说,周改改不敢说,周改改的老汉一大早离开了半半村。
另一件事儿发生在后半夜,后半夜星淡月明。一大早这件事儿就传遍了全村,学校库房放的三十多麻袋粮食全部被盗了。
破案
半半村没有电话。
山书记让武装部长骑上“红公鸡”回乡里报案。
这武装部长平时很稳当,这回呢,独自骑着“红公鸡”快进乡政府时,碰在了一棵被秋风吹干了的老榆树上。还好,劲儿不大,“红公鸡”哑巴了,武装部长的头碰烂了,幸运,只缝了六针,并没有伤着脑子。头缝合后,他才托人报了案。
武装部长是公费医疗,医药费不掏自己的腰包。乡政府在卫生院有本账,先记上再说。医药费也不多,一百二十六元。只是后来乡干部调侃武装部长说,想周改改想得走了神儿,便和榆树亲了个嘴儿。
接到报案后,派出所所长带着派出所的干警来到了半半村,第二天,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帮人也来到了半半村。照相、走访、调查、取证,侦察来分析去,得出的结论是:
不是本村人偷的,就是外村人偷的,不能排除本村人勾结外村人偷的;被盗的粮食不是藏在本村,就是转移到了外村,不能排除一部分藏在本村,一部分转移到了外村;转移的方向嘛,可能朝东走,也可能朝西走,但既不能排除朝南走,也不能排除朝北走;偷粮食的贼也许能抓到,也许抓不到,这个案子也许能破了,也许破不了。
破了三天案,连个怀疑对象都没找到,因为全村人几乎都知道学校的库房有粮食。破了三天案,吃了三天饭,还说半半村招待得不周。公安局的人前脚走,派出所的人后脚也走了。派出所所长临走对一颠一颠的二拐子说:
“破不了,案子在。”
结尾之一
我们的故事该结尾了,我们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一个结尾。
山书记的脑袋耷拉了下来,虽然铲铲帽又回到了他的头上。这三件意外事,究竟哪件给他的打击更大些呢?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我们的山书记从来就是个不服输的主儿。一不做,二不休,自古种地都要纳粮。在他的指挥下,一是学校停了课,让学生动员家长交粮,完成任务的才能来上学;二是瓦粮队疯狂作乱,撬窗子、砸锁子,但已没有多少粮食可瓦了,人们的粮食、猪、羊,能转移的全部转移了。零零散散地瓦了一个星期,几乎家家户户过了一遍,粮食也瓦了不少,一算账,共瓦回粮食5192斤。伙房吃了690斤,卖到粮站4502斤,扣除水分1,45斤,剩余4457斤。其中谷子2816斤,每斤0.34元,计957.44元。黍子1641斤,每斤0.36元,计590.76元,两项合计1548.2元。这1548.2元由乡里结算,村里拿不走钱。半半村的开销呢?二拐子也得算一算,酒钱、烟钱、肉钱、豆腐钱共花了5129元,还不算车工钱。瓦粮的车工、送粮的车工,用义务工是结算不了的。二拐子问会计半半村以前还有多少饥荒。会计说,账上的两万多,没上账的可能也两万多。这些天,要账的人陆续地登上了二拐子的门,二拐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时候的二拐子才知道了当支书的难,一是得罪人,二是尽要钱。二拐子原来认为当支书后好娶个媳妇,可眼下把全村人得罪遍了,有一个说媒的,全村人破亲,还娶什么呀?尤其是不让学生上课,让全村人骂翻了,说二拐子的心比毒蛇还毒,他断子绝孙不说,还怕别人的孩子学习好。二拐子一颠一颠地和山书记说,我是不当了,不当了。
结尾之二
山书记想撤出半半村,周改改告诉他说,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老汉提出了离婚,她要嫁给山书记。山书记总算还有一下,说服周改改嫁给二拐子。并说要给周改改买一辆新“红公鸡”,还答应让周改改任村计生站站长,干上一段,再把她弄到乡计生站去,到了乡计生站就能挣工资了。这不是天上掉下个馅饼吗?山书记说去了乡里,和她继续做“地下夫妻”,如果这事情泄露出去,可什么也办不成了。周改改美极了,她有了一步登天的感觉。说服了周改改,山书记又去说服二拐子。山书记对二拐子说,你无论如何不能辞职,你把这个支书当下去,周改改就会嫁给你。二拐子说,真的?只要周改改嫁给我,当王八也行,别说当支书了。
结尾之三
山书记一行人离开了半半村,半半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学校又传出了呜呜哇哇的读书声,人们转移出去的东西慢慢地又转移了回来。但还有两件事必须交待一下。人们发现半半村少了两个人,一个是本村的羊倌,一个是原支书老婆大板。有的人说,大板跟着羊倌去了内蒙古,也有的人说,羊倌跟着大板回了四川。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据说半半村从此以后,小孩哭得哄不住,妈妈只要说,哦哦,不能哭,哦哦,不能哭,再哭铲铲帽就来了。那孩子马上就不哭了。半半村两个小孩对骂,一个说,你妈和铲铲帽过上了,一个说,铲铲帽是你爹。老汉与老婆嬉戏,老汉说,你看上铲铲帽了,老婆说,是呀,铲铲帽刚从咱家出去。